1.
质疑运营机构“为了方便之名”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
作者:特蕾莎 M·佩顿 西奥多·克莱普尔
译者:郑淑红
版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1月
序言作者:霍华德·A·施密特(曾任奥巴马政府网络安全特别助理)
全球的数据量正在迅速增长,而速度可能达到了每18个月翻一番。计算机科学公司(CSC)发表的最新一份研究报告声称,2020年的数据产生量将会达到2009年时的45倍。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如今“大数据”这个原本深奥的科技词汇正日益在居家和办公场所变得更为主流。
我们采集和利用日益增长的数据源的方式,将对我们的职业和私人生活产生影响。大数据给全球的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了大海捞针的能力,即通过分析和整理海量的数据宝库来发现人类分析师个体可能会错过的隐藏模式和相关性。
然而如今,大多数机构还没有真正明白如何设计大数据的应用和分析方法,所以在采集海量数据时只是抱着“万一用得着”的心态,甚至有些公司在收集数据时并没有考虑过数据安全性以及隐私的影响。
由于企业和政府部门收集所有数据并从中获益,于是捕捉数据本身就成了目的。
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数据来满足无止境的欲望,然而我们还从未公开探讨哪些个人信息可以被收集以及如何被利用。
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通过法律解决私人数据的使用问题。美国有一些这样的法律,但是即使早在互联网走进公众生活之前,美国国会也没有通过一项更加广泛的法律来限制各类私人数据的收集或者使用。信息收集和挖掘技术已经远远超出政府的能力范围,以致难以深思熟虑地通过一项兼顾商业和隐私保护的法律。正因为如此,商业公司不知道它不可以做什么,而民众也没有得到保护。
放眼全球,太多的民众暴露个人身份信息于盗贼面前。如果我们不处理安全和隐私问题,这些难以置信的好处看起来就没那么显著。实现这一点的最佳途径是更好地了解并且取得适当的平衡。
2.
质疑政府机构“为了安全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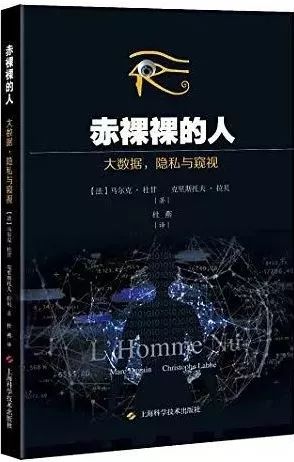
《赤裸裸的人:大数据,隐私与窥视》
作者:马尔克·杜甘 克里斯托夫·拉贝
译者:杜燕
版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7月
序言作者:朱扬勇(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在舒适便利和个人隐私之间进行选择、寻找平衡。问题是我们似乎完全没有准备好,没有足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来帮助我们寻找这种平衡。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个人隐私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侵害,我们不知道个人隐私被侵害到何种程度,也许我们早已经变成一个“赤裸裸的人”,却毫无知觉。
爱德华·斯诺登关于海量监视程序有一个说法:这个程序从来就不是针对恐怖主义,而是为了商业监听、社会控制、外交操纵。这是一个权利的问题。本书作者马尔克·杜甘认同和分享了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间谍活动的世界中,人的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正在逐渐消失。
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采用的方法,是对所有人的资料进行收集,根据可疑性对数据进行提炼分析。显而易见,今后间谍监视活动主要通过这样的科技手段得以实现。马尔克·杜甘批评这样太过于依赖高科技而忽略了线人的情报,而线人的情报却是十分基础和有效的。
由于全民监视已经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似乎成了一个比以往更安全的地方,而实际上,世界的安全性却不容乐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哲学学者格雷瓜尔·沙马龙曾经说过:“2013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局主管宣称通信程序已经挫败了‘几十起恐怖主义活动’;随后,在10月,他修正了自己之前的言论,把挫败的涉及美国领土的恐怖活动数量降到了13起。而最终,他承认美国通过电话通信元数据收集程序,成功抑制的恐怖主义威胁活动只有1起(也许是2起)。”
如何发展技术、如何保护隐私、如何界定权益……
不同于人类历史上前几次的技术变革,我们没有时间慢慢适应大数据的变革。
3.
拒绝“宿命论”,不要绝望

《无处安放的互联网隐私》
作者:茱莉亚·霍维兹 杰拉米·斯科
译者:苗淼
出版社: 阅想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人们很容易产生“隐私已死,何必执着”之类的想法。比如,经常会有人认为:
“对隐私的任何期待都是不合理的。”“你还想怎样?是你自己发布到网上的。”“嘿,这是免费的。你要是不喜欢,那就别用。”
我们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我们并没有理会这些宿命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地描述问题;我们认真对待托马斯·爱迪生的名言:“人用手创造了什么,就应该用头脑控制什么。”
这是一种对待隐私争论的新方法,它认为隐私是值得保护的,而且应该研究出台有意义的应对政策。
我们通过追踪创建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lectronic Privacy Information Center,EPIC)开始收集相关文章。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主旨任务在于引起公众对新兴的隐私和自由问题的关注。在刚开始的 20年里,我们取得了成功,也经历了一些挫折。电子隐私信息中心将迎来其周年纪念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评估已完成的工作和未来的改善空间。
我且举我们中的几个例子:
达尼埃尔·席特伦(Danielle Citron)是一位研究性别问题的法学教授。她在讨论人们越来越担心的“色情复仇”时结合了一些隐私文化因素。她的建议很明确:“法律需要再次修正,以打击网络技术对性隐私的破坏性侵犯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史蒂文·阿福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是政务公开的倡导者,他在文章中讲述了隐私在确保可问责性中的关键作用。“透明度本身并不能命令或推断特定的隐私或国家安全讨论应该达成什么结果。但公开政府行动的基本事实,才能使隐私讨论成为可能。” 公开是对隐私的更大保护。
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于公众对隐私权未来的讨论质量。他警告说:“隐私会被恐惧打败,因为恐惧发生在我们的大脑中更原始的部分。隐私也会被便捷打败,因为便捷是真实而直接的,而缺乏隐私产生的危害则是更为抽象和长期的。”但他也仍对理性讨论抱有希望。“我们需要现在考虑这些问题,决定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而不是不假思索地便让这些变化在我们身上发生。”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