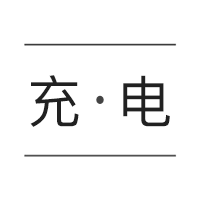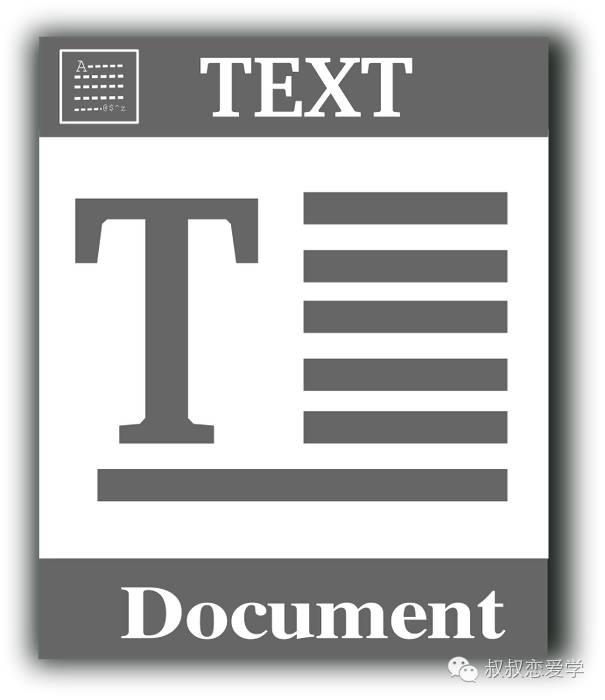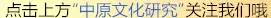
编者按:林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古文字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商周考古、东北考古与古文字学,代表作有《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
本期将节录林沄先生《我的学术道路》一文中有关其研究生阶段的回忆内容,
以仰山斗,励之后学
。
 林沄先生 近照
林沄先生 近照
我原想考东北考古的研究生,但那一年北大和考古所都不招这个方向的研究生,其时吉林大学的于省吾教授有意在北大招甲骨文金文专业的研究生。我本来对此有兴趣,又想到东北还可兼搞东北考古,所以就突击备考,居然录取,因此就成了于先生的学生。
跟于先生学习时,他也非常强调做学问一定要占有全部资料。在他的指导和督促下,我用大概两年时间看完了全部在吉大能看到的先秦古文字原始性资料。他还强调要通晓本领域内前人研究的成果,才能站得高,更上一层楼。这在三年时间中实在难以做到,只能尽力而为。他的治学方法,上承乾嘉考据学派,注重全面排比资料,孤证不立,无征不信;而在考释古文字时,力主“以形为主”,也就是立足于实际字形的历史演变,找不不识之字和已识之字的确实联系。在我看来,这和考古学上的类型学排队有相似之处。在史学方法上,他主张重视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认为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还强调得不够,应该把地下证据看得比传世文献更重才对。他还主张研究古代史的问题要综合使用文字记载,考古实物和民族学现象,多方求证。这些都是我得益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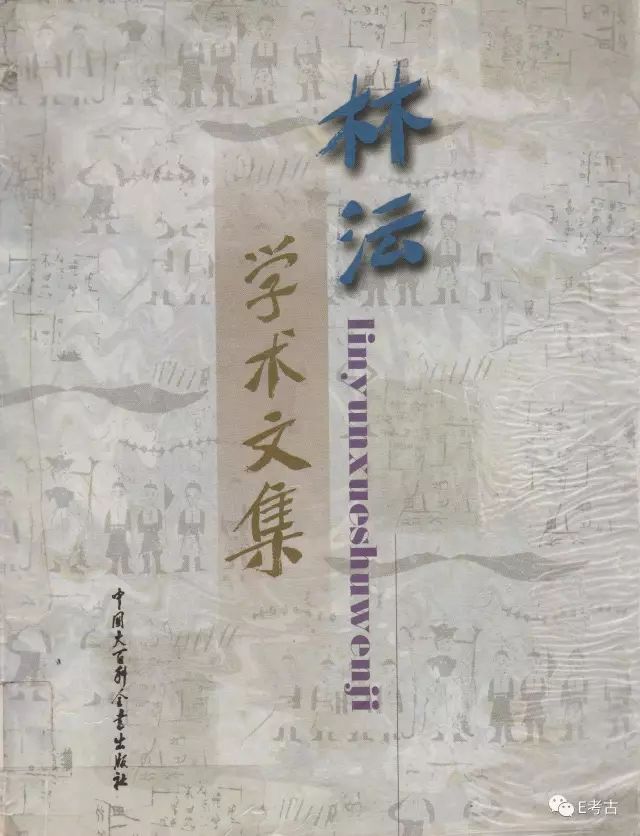
《林沄学术文集》书影
我在1962年年底写的第一篇古文字习作《豊豐辨》,就是既用字形嬗变的方法来论证豊、豐两字虽在汉代已形体相混,但实有不同起源;又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实物等多方面证据来对这两字的造字本意作新的解释。结论得到于老的首肯。1963年春在自学古音韵学时,写了一篇越王者旨於赐戈铭中的名字即文献中的“鼫与”的短文,经于老帮助修改,被《考古》杂志刊用。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论文。在论定这个越王名时.也兼用了青铜器类型学年代序列方面的证据。
在跟于老学习的三年中,以及后来回到吉林大学当于老的助手的好多年中,于老每写一篇新的古文字考释文章,几乎都要让我先看,讨论一番,反复修改。后来出版他的《甲骨文字释林》,是我清写全书的。在长期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深感古文字释读的基本依据,是客观字形的仔细确认和在掌握全面字形资料基础上作纵向、横向的历史比较。这个观点,我在《古文字研究简论》这本小册子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发挥。当然,在那本书里我着力要论证字形和辞例这两个客观依据中字形为什么更重要,因而对辞例的作用并未能全面讨论和估价,是有一定片面性的。
不过,我虽然跟于老学的是古文字,我自己的目的还是想用地下出土文献研究商周史。我觉得郭沫若把铜器铭文编成断代的、分国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使之成为系统化的史料,比单纯去考释文字意义更大。但他的《卜辞通纂》写得早,资料未经分期,从中只能把全部甲骨文记载当作一个时代平面的东西看待,无法了解商代后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以我在看甲骨文资料时,大约用半年多的时间,把较完整的辞条分期、分类抄录了一遍,订成十册,想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在分期抄录中,我感到旧有的董作宾五期划分的标准,有不少不精确之处,特别是他分的“文武丁卜辞”,内涵复杂,性质和年代都已引起争论。因此我转而专门对这批卜辞下了工夫,一方面,对过去有的研究者已经识别出来的“非王卜辞”,分类全部摹录了一遍,通过研究卜辞出土坑位、共存的它类卜辞,确定它们是武丁时代之物;而对其内容的全面分析,则确定了它们是不同的父系家族的首脑(均自称为“子”)所卜。这一研究成果,到1979年才有机会正式发表,后来朱凤瀚在《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正是用这批材料对商代家族的内部形态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而且,1991年在安阳花园庄又发现了一坑新的“子卜辞”,完全证实了我对这类卜辞性质的判断。另一方面,我对所谓“阜组卜辞”也进行了全盘摹录和详细研究,通过考古学上的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论证了这种卜辞实际是早于董作宾所定的第一期卜辞的时代最早的王卜辞,也是武丁之物。这项研究成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其中主要论点到1984年才在我的另一篇论文中正式发表。
从这些研究中我认识到,要把甲骨文资料变成研究商史的科学的史料,必须首先真正解决卜辞的性质分类和断代问题,即使是单研究文字,不解决分类和年代相对早晚的问题,许多字的实际发展历史也要造成误解,不能正确释读。后来我在甲骨断代方面又做过一些工作,提出应该把甲骨按客观特征分组和按出土层位及祭祀对象称谓断代这两件事分开,而且主张以字体书风的特定组合关系作为分组的唯一标准。赞同我这种观点的黄天树在《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一书中,对这方面又作了更细致的研究,但还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很希望有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能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科学的分类和断代基础上,产生一部类似《两周金文辞大系》那样的《殷墟卜辞大系》,这将使商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甲骨断代研究之外,我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只有很少是识读文字的,大都是以古文字资料研究先秦史的。我发表的论文中第一篇有较大影响的是1965年《考古》第6期上的《说王》,那就是从古“王”字象钺形出发,讨论中国古代王权起源于军事统率权(后来在别的论文中,我又进一步把王的原始意义推衍为军事性方国联盟的盟主)。在这方面研究中,于老对我是很支持的。他常说,王国维在古文字学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但他更有影响的是利用古文字资料写出像《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这样的史学史上有地位的名著,并鼓励我也要向这个方向发展。我看于老的著作,觉得他写的《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一文,就是他的《殷周制度论》。在中国史家几乎异口同声说商代是奴隶社会的50年代,他却主要以卜辞为主,论证商代是军事民主制社会。虽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已经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认定殷墟大量用人祭祀的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他却根据卜辞记载论证被杀的应是当作牲口而新抓来的俘虏。而且他分明不是郭老所斥为“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而是认真读过马、恩原著和《古代社会》的。我从而更深切地感到,商周的历史并非已是真相大白,只需讨论划归哪个社会,而是多方面的真相首先有待探明。我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时,根据整理的甲骨文资料,写了一篇《商代方国军事联盟》,文中不同意于老说商代还是部落联盟的观点,但接受了联盟主要是军事性的论点,并进而和周代仍保持的诸侯制联系起来,解释了诸侯制的实质。于老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加以鼓励。在研究生期间,我又做过商代军事制度的研究和父权家族的研究,都是从实有史料探求历史真相的尝试。
研究生毕业后,我一度被分配到辽宁复县的农村中教中学。在农村的最后两年,用原来做的资料又开始这方面的研究。1973年调回吉大任教,长期担任商周考古课程,结合备课,一直断断续续做些新的研究。其中较重要的成果,是在原有的方国联盟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方国内部的“都鄙群”这一基本结构和以“都鄙群”为基本结构的国家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变化。其主要论点在1986年于美国召开的“中国古代社会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研讨会”上宣讲。论文后在吉大学报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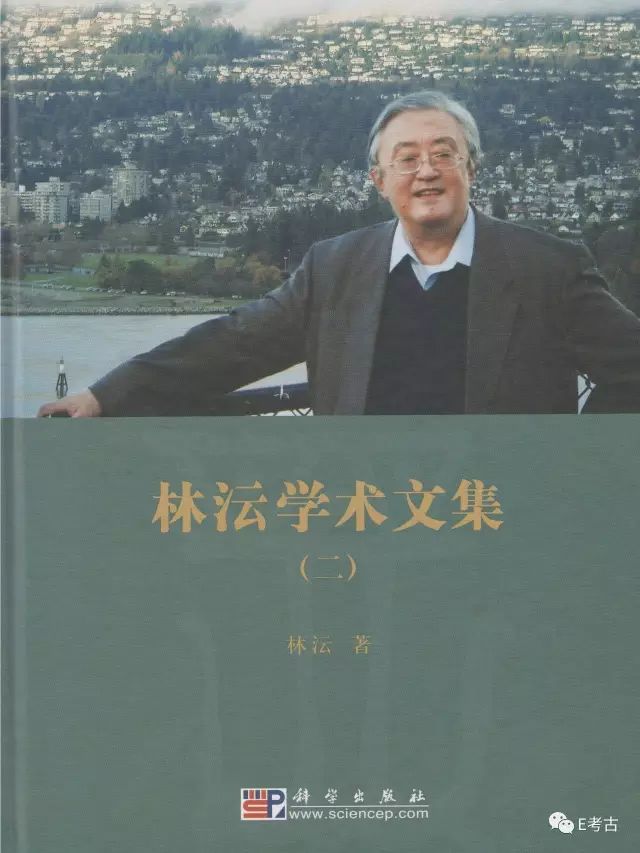
《林沄学术文集(二)》书影
通过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我现在认为,疑古派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强有力地批判了古代文献的真实可靠性,从而破除了长期统治中国人头脑的旧的三代圣王至治史观。但由于对大批传世文献的否定,三代的历史也几乎成为真空了,因而考古资料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我一度在课堂上也强调考古资料在研究古史上比文献更重要。但后来也越来越认识到考古资料在研究古史方面有种种局限性。古代人们的活动并非都留下遗存,而留下的遗存又大部分不能保存至今,保存至今的又并未都被发现和认识。因而,从现已被认识的遗存去恢复古代历史情景,必然是“管窥蠢测”。而且,遗存是“哑”的历史见证,它们反映什么历史真相,是由研究它们的今人代它们说的。不同的代言者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从遗存所恢复的历史的真实性和清晰性自然就会受到影响。文献作为史料自然也有种种局限性,但它涉及很多不留下遗存的古人的活动。而且它本身就是古人语言的记录,是古人在“说”。我们只要能弄清传世文献究竟是何时的何人在“说”,即使是全伪的古书,也不失其史料价值。只要是人在说,就有主观性,并不一定真实而全面地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但由此而可知该时的某人或某些人的看法、想法,也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实际。当然,传世文献在长期传抄翻刻后,作者本来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存在许多疑问,不少地方也要文献学家来做代言人,这也要影响它们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和清晰性。
我国过去号称“历史悠久”,主要是因为有相当多的先秦文献相沿不绝地流传至今。在疑古派对大量先秦古籍的可靠性发动全面攻击,而现代考古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几乎成为空白的夏、商、西周历史,一度成为供史家驰骋想象力的原野,并用外国史中的或民族学上的范例来填补空白。但随着考古发现、研究的飞速发展,地下出土文献释读的不断进步,我们越来越看出那样干是背离中国古史真相的。而且,对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需要更冷静的估价。于老主张地下资料比传世文献重要,多次对我说,传世文献中夏初铸九鼎的事他不信,因为二里头文化还发掘出很小很薄的铜器。但后来二里头遗址本身在冶铸作坊中就发现了较大型铜器的铸范,后来又发现了铜鼎、铜斝,和镶嵌绿松石的铜器,该遗址也由多数人认为是商汤之都,而变为多数人认为是夏都。如于老仍在世,也会认为夏初铸九鼎并非不可能,再如顾頡刚认为《禹贡》成书必晚至战国,其中一个根据是战国以前不可能贡铁。但现在西周考古中已屡见铁器,新疆地区发现的铁器年代可能更早,这条理由就不能成立了。特别是地下出土的文献,一再像殷墟卜辞证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确有所本一样,证实过去受人怀疑的传世文献确有历史真实性。因而,在驰骋想象力恢复古史图景时,凡遇与己见不合的典籍记载,就斥古籍为虚妄,这种办法肯定是越来越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