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的一个深夜,李美玲再一次刷开几个电报(Telegram)群,迎面弹出的,是数条女性裸体视频以及“开盒”的女性个人信息——年龄、学校、住址和联系方式。
群聊的名称颇为露骨——“奴隶房”“偷拍房”“非法录音房”,还有按职业划分的房间——“记者羞辱房”“女兵羞辱房”和“教师羞辱房”。一些群友正肆意点评、侮辱新的“战利品”。
在这些“羞辱房”里,李美玲伪装成一名极右翼厌女的韩国男性。她模仿男性口吻发言,句末加上“-노”——这是韩国极右翼论坛ilbe嘲讽已故韩国总统卢武铉的黑话。
“羞辱房”外,李美玲是韩国女权组织“猫”(CAT)的一员,该组织创立于2024年8月底。两个月前,涉及12名受害者的首尔大学“深层伪造”案(deepfake,以下简称“深伪”)发生后,“猫”等数十个韩国在线女权组织将一桩桩“深伪”案通过多语种翻译扩散至全球。
“深伪”亦可理解为AI换脸,此类案件均是嫌疑人在未经受害者知情或同意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真实人脸与虚假身体,生产出大量色情片,在电报等匿名社群中流传、售卖。一些嫌疑人会主动将色情照片发给受害者,嘲讽、骚扰被换脸的受害者。
韩国警方公布的数百起“深伪”案里,嫌疑人遍及学校、军队,并有大量未成年人参与,其中最高群组人数约22万。许多受害者是嫌疑人的同学、女友,以及女性亲属。
外界谴责,这是韩国N号房2.0版。新一轮的韩国数字化性剥削下,二三十岁的韩国女性再次站出来抗争,她们用Z世代的网络结社方式,自下而上地为女性争取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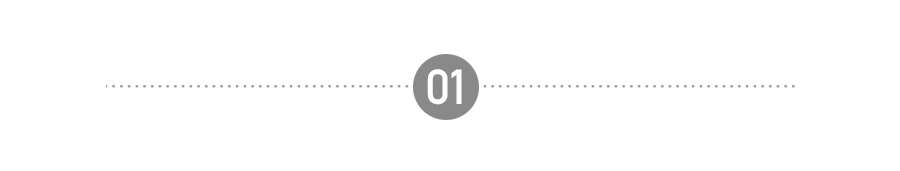
卧底一间“羞辱房”
前两年,韩国“非法摄像头”(Molka)泛滥时,李美玲就开始观察电报群了。她的推特账号吸引了大量女性粉丝,每隔几十分钟,李美玲就会转发一条女性权益相关的韩语或英语推文。
她的头像是一张“比着大拇指与食指手势(Megalia)”的韩国男性,形容韩男生殖器短小。当然,这是李美玲加入女性组织“猫”的志愿工作之一。
进入“羞辱房”前,新人需提供一张女性的照片和信息。5秒左右,“合成大师”就贴出了一张“深伪”色情图。群友还可以对胸部大小提要求。
“我用AI做了张假的女性照片,就混进去了。”李美玲回忆。她每天都在线,大多数时间潜水,偶尔冒两句厌女言论,寻找“群内认同”。
作为管理者的群主和掌握AI换脸技术的“合成大师”人气最高。李美玲也会跟他们聊几句,以收集更多“深伪”证据。
“如果我身边的男性进了群,他们会用我的名字建一个‘张尼扬羞辱房’,在里面发布与我有关的‘深伪’照片和羞辱内容。”李美玲的团队成员之一张尼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女生的照片、信息是被身边的男友、男同事或男家属泄露的。
在那间22万群友的巨型“羞辱房”中,群主设定了一套盈利模式。
据《韩民族日报》报道,新人只有两次合成免费照片的机会,之后每合成一张照片收费1颗钻石。群友可以通过加密货币购买钻石,每颗钻石售价0.49美元,每10颗为单位起充,量大从优。为了扩大群聊人数,邀请新好友入群也可获得钻石。

▲《韩民族日报》记者潜入的22万人的巨型电报“羞辱房”。文字由软件Papago翻译 图/顾月冰
有利可图的拉新机制,让群成员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李美玲卧底的众多群聊里,最大规模超5000人。“在一些群里,我看到过未成年女孩的‘合成’照片,性剥削者抓住了女生的弱点,称她为‘奴隶’。而在女兵羞辱房里,很多视频甚至是十多年前偷拍的。”李美玲有些气愤,回复记者时加了“感叹号”。
所有人都成了大型羞辱房的合谋。没人质疑、没人反对,每一张照片都会引来乌合之众的狂欢。
“羞辱房内,获取色情内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拿钱买,二是彼此分享。”李美玲发来一个“哭泣”的表情,她知道,在群里很难为女性出头。“谁质疑群聊内容,ta就会被踢出去。”她只能默默搜集非法资料,提交给警察。她不敢轻易联系受害的女性,怕受害者走极端。
这些年来,因非法性剥削引发精神问题、结束生命的女性不在少数。五年前N号房事件中,每一个女性的自杀都会让电报群的韩男迎来一次小高潮。
李美玲知道,这些人都是极其普通的韩男,“很多人还是未成年,就已经这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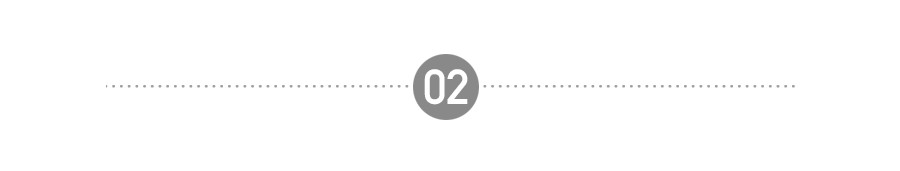
抓住那群“制造色情片”的男人
李美玲的卧底方式是跟揭露N号房的“追踪团火花”学的。李美玲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几条“追踪团火花”的报道链接。
“追踪团火花”是由两位女性成立的,她们曾通过体检表追踪到N号房关键人物“兔子”,又向警方提供了博士房创始人赵主彬的信息。自此以后,“追踪团火花”的媒体采访邀约就没停过,南方周末记者的约访信息,她们隔了一个星期才回复。
“追踪团火花”的元恩地用了快两年,才配合警方将首尔大学“深伪”案的主犯朴某(40岁)逮捕归案。
首尔大学深伪案是本轮被曝光的一系列“深伪”案中最恶劣的一起。韩国警方统计,在2021年7月到2024年4月间,首尔大学“深伪”案主犯朴某(40岁)、视频制作者姜某(31岁)等5人在电报群聊天室中制作、传播61名女性的合成视频,包含12名首尔大学校友。
经查实,视频内容多达两千余条,且含有未成年人视频。
2021年夏天,躲在网线之下的朴某,向首尔大学毕业生Ruma发送了数十条色情照片、视频——Ruma的脸和不明裸体合成在一起,配文不堪入目:“荡妇”“在学校出卖身体”。
那些照片的原素材是Ruma在KakaoTalk上的旧照。警局调查人员建议Ruma尽可能写下嫌疑人及其相关信息,可Ruma仅接触过那一个电报账号。几周后,账号被注销了,一切像是沉入海底。

▲2024年8月28日下午,韩国首尔,数码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内,韩国女性人权振兴院设置了深伪犯罪受害预防和对受害者紧急援助方案的看板 图/视觉中国
直到2022年的一天,收到Ruma邮件的元恩地站了出来。此时,Ruma与其他被换脸的首尔大学女生相识,她们缩小了调查目标。其中一位受害女生获得了一条电报群的分享链接,元恩地伪装成为一名“喜欢看色情片、有着漂亮妻子的30岁男性”进入了主犯朴某(40岁)的群聊。
“他不停给我发合成照片,问我喜欢哪个女性?”元恩地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朴某也不停询问“我妻子的日常和照片”。朴某反侦查意识极强,时常回避个人信息问题。元恩地每次跟他谈论“漂亮妻子”后,总是生理性反胃,要缓一阵子。
事情在2024年年初出现了转机,朴某突然提议想要“妻子的内衣”。两人约定将内衣放在首尔大学地铁站附近。4月的一天,一名黑衣男子被首尔警方逮捕。
警方随后将朴某等五人一并逮捕。“他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人。”Ruma对这位相差数届的学长朴某毫无印象。庭审和判决听证会时,朴某显得焦虑,双手不断捂住脸,会自言自语或哭泣。
2024年10月30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一审判决,主犯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共犯姜某(31岁)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而在8月28日,首尔法院一审宣布,五人团伙中另一位朴某(28岁)只被判处了5年监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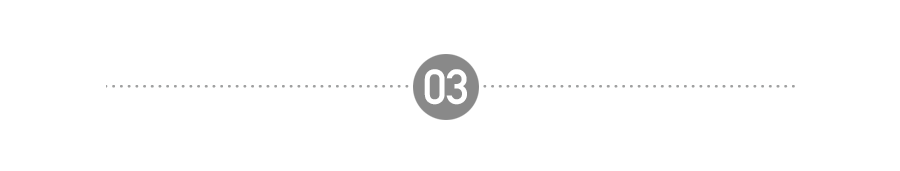
“请支持我的请愿书”
“五年太短了,所有深伪制造者至少判10年!”尤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是Ruma的朋友。
本轮“深伪”案早期,推特大号Queens Archive就汇集了多起受害女性的个人经历,三名男程序员通过爬虫抓取设计一款标注学校的“深伪”地图,以此提醒其他女性注意身边的“性剥削”。
这些民间志愿行为给警方调查和女性自保提供了便利。但很快上述账号被删除,地图制作者被公司提醒。
接棒的是由年轻女性尤里、李美玲等组成的小型女权网络组织。她们对法院的判决力度不满、厌倦了社会的不公正,决定在互联网上将韩国新一轮性剥削事件推广到全球。
9月初,尤里创立了“女性工作小队”(Woman Task Force Team),在推特等社媒上招募组员。“我只允许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加入。”尤里说,她会检查应聘者的身份证和手写痕迹。
“女性工作小队”约有四十多人,组员间不过问彼此的真实身份,主要用匿名社交软件Discord线上联系,昵称称呼。
尤里称,这是一场面向全球的标签运动(Hashtag Movement)。她们主要做的是宣传推广工作——将“韩国女性”相关新闻、政策和性剥削案件译成英中日俄等语言,通过推特、Instagram、VK、微博等平台,以海报形式发送至全球。
“平均每个人工作2小时,积极地组员会自愿工作更多。”30岁出头的尹佩斯说,小组创立的初衷是为了改善韩国互联网的厌女氛围。
尹佩斯和李美玲同属于女性保护组织“猫”,成员约25名。她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现负责“猫”账号的韩中英翻译工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4小时语音采访后,她还主动整理了中英文版本的几起“韩国厌女事件”。
多位女性采访对象对韩国社会的性剥削感到恐惧和不安。她们采访时会提到一系列数字性剥削事件。例如,1999年成立的色情网站Soranet。该网站鼓励用户偷拍身边女性的私生活,常年活跃用户约100万。该网站服务器在荷兰,直到2016年才被关停。
还有近两年来无孔不入的“非法摄像头”。“很多韩国浴室里也有隐秘摄像头,它会边拍边上传,很难抓到偷拍者。”尹佩斯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五张非法摄像头图片,厕所、酒店浴室的墙壁上有着大小不一的圆洞,有些被堵住了。

▲韩国首尔永登浦区议会3楼女厕所墙上的洞 图/受访者供图
被偷拍、偷录、物化,“女性”是所有性剥削事件中被凝视的主体。
2024年8月底、9月初,韩国的“深伪”案件登顶多个社媒平台的热搜。“效果还算是成功。”尤里有些欣慰,她和小伙伴想做的还更多。
除了线上宣推外,“女性工作小队”个别组员前往首尔惠化站参加抗议集会。9月21日,超过6000名女性身穿黑色衣服、戴着黑色口罩,站在六年前N号房的抗议现场,她们敦促政府严惩“深层伪造性犯罪”。队伍近350米。
经过几轮女性组织的抗议与请愿,韩国政府推进了“深伪”相关的法案。
9月26日,韩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称,购买、储存或观看深层伪造的照片、视频者,将面临罚款或坐牢。
10月10日,韩国国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处罚性暴力犯罪的特例法》修正案,规定持有、购入、保存或收看“深伪”色情影像者,可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罚金。
这远远不够,网络暗处仍在生产着色情照片和视频,韩国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剥削依旧猖狂。
尤里和组员们草拟了两份请愿书,一份名为《关于加强“深伪”性剥削法律惩罚力度》,另一份名为《关停Porn Korean非法色情网站》。
“我的国会请愿书只要30天内超过5万人同意,韩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就必须对其调查、处理。”尤里语气坚定,她不希望更多未成年男性被互联网的厌女incel(记者注:incel原指欧美社会中的非自愿单身者,他们不受女性青睐,在互联网上抱团取暖,后发展出一系列仇女话语体系,甚至公开杀害女性)情绪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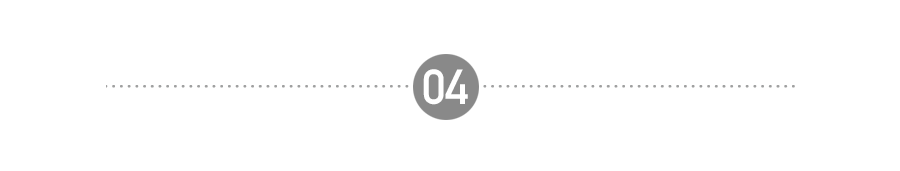
“我在韩国做女人很不安”
厌女文化充斥着韩国互联网。“我经常听到一些网友说:‘女性就像干明太鱼,每三天打一次才好吃。’”尤里是善于打游戏的女孩,她曾考虑过成为《守望先锋》的职业电竞选手。可不论她游戏水平多纯熟、账号等级多高,一旦她连麦说话,总会受到男玩家的讥讽。
在李美玲模仿的厌女网站ilbe上,韩国男性给女性起了歧视性外号:“泡菜女”是约会中让男人付钱的女性,“豆酱女”是爱买奢侈品、过度消费的女性。论坛里常提到“女性应该谦逊,不应该在男性面前发言”。
“被歧视、被性骚扰似乎是韩国女性的常态。”尹佩斯曾经在一家韩国大企业工作,她被安排的具体任务是早上8点到公司煮咖啡、给老板打扫桌子。
“我向上级表达过,想尝试市场营销的工作,可没得到任何反馈。或许是我无法参与男性员工与老板们的饭后酒局。”尹佩斯后来选择离职,和女性同伴成立了一家同类商业模式的小公司,薪水高过从前。
囿于家庭、学校、职场上的不公平对待,韩国女性开始在互联网上反击。
2015年,韩国女性成立Megalia网站。当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暴发,一些男性在MERS Gallery版面上不实指控两名韩女,称其出国游将病毒带回韩国。
Megalia将“MERS Gallery”与女性主义讽刺小说书名《伊加利亚的女儿们》(Egalias döttrar)结合在一起,用“比着大拇指与食指手势”图片嘲讽男性。
该手势在各大公司广告、游戏宣发上被男性抵制。“不要给外国记者发这个手势(Megalia)。”尤里特意提到,这两月里她的后台收到了一条匿名男性留言。
此后,韩国社会又出现了Womad等女权主义网站。韩国社会陆续掀起“我也是”“逃离束身衣”等女性主义觉醒运动。2017年,女性主义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畅销过万,并被改编成电影。
这让韩国男性的“厌女”情绪逐渐放大。2016年,江南地铁站厕所内,一名男性无故杀害了一名女性。
一场场“性别战争”让“女权主义”成了贬义词,公开谈论“女权主义”会遭到韩国社会的“取消文化”,甚至遭到男权的袭击。
在美国东部读博的张尼扬,在韩国生活时爱穿裤子。“他们常说,你为什么穿得跟男孩一样?”张尼扬提到,韩国男性对于女性的外貌是否有女性特质更加敏感,“一些男士认为短发女全是女权主义者”。
2021年冬奥会期间,一些韩国极端男性集体攻击短发女运动冠军安山,称她是“剪短发的仇男主义者”,扬言要撤回其奖牌。2023年11月,韩国东南部晋州市曾出现一起二十多岁的男顾客袭击便利店短发女店员的恶性事件。“既然你留着短发,那你肯定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大男子主义者,我认为女权就该受到攻击。”警方记录中,该男子说。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女权组织成员里,没有人愿意主动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像是李美玲总是深夜回消息,每次聊天框的输入条总是亮了又灭、欲言又止。她多次提到,她很怕被一些韩国男权者盯上。
在N号房事件中,嫌疑人团伙曾根据公开报道,定位到一些卧底电报群的女记者,对其人肉、网暴,甚至用记者真名建了“羞辱房”。韩国警方曾要求电报公司协助调查,但被忽视。
“我在韩国做女人很不安。”尤里作为起草国会请愿书的女性组织创始人,她依旧不敢在工作场合大谈“女权议题”,“因为在公司谈论女权,很可能被开除。”
尤里没敢跟年迈的父亲坦白自己争取女性权益的努力,“他要是知道我在做这些事,他会生气的,觉得我被洗脑了。在老一辈眼中,女性是弱者,就应该谦逊。”

▲2021年8月10日,韩国仁川市,警察厅和女性保护部门成员在当地一号线地铁的公共女厕内检查拆除秘密摄像头 图/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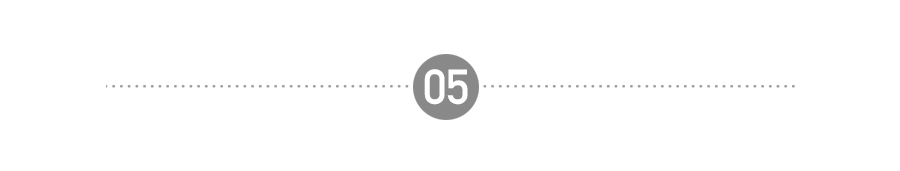
“社会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
三年前,尹佩斯搬到了美国生活,逃离了压抑的韩国。“长辈重男轻女,他们试图控制女孩的言行举止,但并不会限制男孩。”尹佩斯知道,这是韩国社会典型的父权制文化。
做自由职业后,尹佩斯有固定的客源。但她只能跟韩国客户假装客源不多,“因为男性不喜欢女人挣得多”。
直到2005年以前,韩国家庭法中依旧保有户主制(호주제),即户籍系统中只有男性能登记为家主,须有长子继承,遗产也通过男性传承。该制度导致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地位上从属于男性。万一离婚,子女也得归属男方。
韩国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就业率的提高,使韩国年轻男性的“厌女”情绪开始增长。
韩国记者千官聿所著的《二十多岁的男人》一书中,年轻男性视同龄女性为威胁,而自己是女权的受害者。他们认为“社会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女性还在持续受到优待,这破坏了唯才是用的精英主义”。
一些男性甚至认为,韩国男性义务兵役制会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近两年的优势。
可据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韩国性别平等指数为0.68,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05位。
“韩国青少年普遍厌女。”Aha首尔青少年性文化中心调查39名实施“深伪”性剥削青少年后发现,这些青少年谈到犯罪动机时,22%的人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更多的是出于好奇(22%)、一时冲动(21%)等。
“他们抱怨社会不公正,说‘我被抓是因为我运气不好’。”Aha首尔青少年性文化中心主任咸庆镇(音)说,将女性性化和仇女,已经成为韩国青少年的主要问题。
韩国是遭受深伪色情内容生产最严重的国家。
2023年美国专注于身份盗窃保护的初创公司Security Hero报告统计,韩国女歌手和演员形象占全球深伪作品生产的53%。
截至2024年9月18日,韩国已接到八百多起与深伪相关性犯罪报警,警方已经逮捕387人,其中八成是青少年。过去三年的警方调查中,六成受害者是未成年人。在8月底被曝出的一间850人的“女兵羞辱房”中,很多女兵的照片只能在军队内网找到。
每当韩国发生性剥削色情事件后,社会更多要求女性先自我审查。
“大多数女孩担心被换脸,删除了社媒的个人头像。有段时间,我的ins动态里总是出现‘绝不要上传面部照片’的建议。”尤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然还有男性傲慢地说,“别担心,你太丑了不会成为受害者。”
“深伪的图像,太过逼真了,其危害已经不是图片本身真假的问题。高度的‘以假乱真’已达到对女性的严重伤害,社会舆论在对受害女性道德审判时,‘真假’问题反倒显得并不重要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深伪”内容难以在网上根除,一些女性宁愿自己整容。
从N号房之后,韩国女性的抗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韩国国会立法。
2020年5月韩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N号房防止法,如《性犯罪处罚特例法(修正案)》新增了持有、购买、储存和观看非法性剥削视频,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罚款的规定等;《刑法修正案》中,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权年龄从13周岁提高到16周岁……
尽管如此,韩国最高检察院表示,2021年被捕的17495名网络性犯罪者中,只有28%被起诉。
“政府总是对男性性犯罪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十年,至少判十年。与政府合作很重要,即便很难落实为法律条文,我也不希望女性失声,不希望对女性的性剥削被忽视。”尤里说,作为普通的韩国公民,她只能通过请愿,推动韩国国会调查。
“‘深伪’等AI换脸案件可能涉及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陈冉提到,在中国刑法第363条中,考虑到涉案淫秽物品的数量、次数等情节标准以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最高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截至2024年10月30日,尤里的请愿书已得到5.3万国民的支持。

▲2018年8月4日,韩国首尔,妇女街头集会抗议偷拍女性行为,参会人数超过4万人 图/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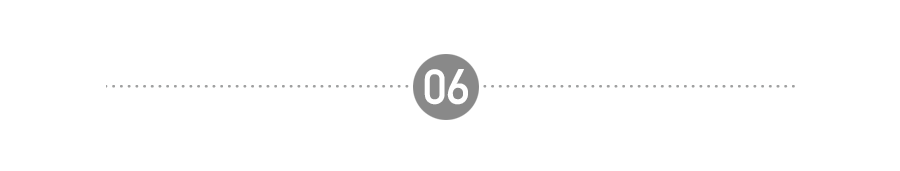
谁输了性别战争
近年来,“性别战争”逐渐成为政客攫取选票的资本。文在寅就职时宣称,他将成为“一位女性主义总统”,可在2018年“我也是”运动中,其党内政客安熙正因多次性侵女秘书一事,文在寅丢失了女性选民的好感。
在2022年韩国大选期间,尹锡悦竟放话称,韩国“不存在结构性性别歧视”,将废除防止性别暴力的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韩媒舆论哗然,称其为了拉拢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带头挑动性别对立。
政客的性别牌在韩国负增长的生育率上,并无益处。
“猫”和“女性工作小组”组员的简介中普遍写着“4B”或“6B”“4T”,4B是指“不恋爱、不发生性关系、不婚、不育”。这是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口号。6B则多了两个“不购买厌女产品、单身女性互助”,而4T是指“脱束身衣、脱宗教、脱御宅文化、脱偶像”。
“一个人挺好的。”22岁的尤里说,2023年她曾经有过一段不算愉快的亲密关系,让她太窒息了。尤里家住在首尔周边的城市,是一名销售,平时挣得钱比前男友还多,她不需要依赖别人。
尹佩斯大三时就开始犹豫是否要走入婚姻,她担心婚后的母职惩罚和繁琐的家务。“我现在三十多岁了,感谢父母给我的自由,他们没怎么催我。”尹佩斯笑了笑,可能也因为她是女孩,父母不想管。
父权制下的传统婚恋观平等地压迫着每一位男女。
尹佩斯有位38岁的男上司,频繁被其母亲催婚。“赶紧找个女人结婚生娃!生下来我会照顾,你什么都不用管。”尹佩斯回忆的时候,忍不住笑了。她还提到,38岁的男老板对一位离异带娃的女性有好感,但他的老板思虑片刻说:“可是她带了一个儿子,我没有冠姓权了。”
历届政府的人口政策都未能扭转结婚和生育率下滑的趋势。“如果女性的不满得不到承认,社会是无法结束生育罢工的。”文在寅政府女性家族部部长郑铉栢批评,现任政府似乎在主动破坏性别平等。
能不能让女性生活在公平、安全又健康的社会?“厌女文化、社会制度,以及韩国男性的优越感,除非这些都消失,我才会结婚。”张尼扬感激母亲尊重她的任何选择。
本轮“深伪”案件曝光后,韩国政府与Telegram东亚分公司商定清理关停了一批“羞辱房”。类似于Deepbrain AI等韩国初创公司也在跟韩国国家警察厅合作,开发了一款深度伪造检测系统——只需几分钟便能对口型同步、换脸进行检测。
网线之下,电报上的“羞辱房”仍然存在。
2024年10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电报搜索“羞辱房”时,仍能发现最多超过2000人的群聊仍在运行。
“请发来你想羞辱的女孩照片、姓名,和简单的羞辱文字……”当南方周末记者进入某个“羞辱房”群聊时,群主设置机器人弹出一条消息。
群里的多数账号显示,“已注销”。
• 参考书籍:《N号房追踪记》【韩】“追踪团火花”著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李美玲、张尼扬、Ruma、尤里、尹佩斯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