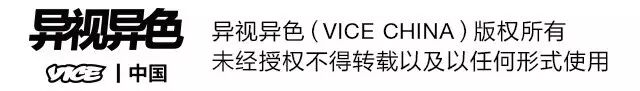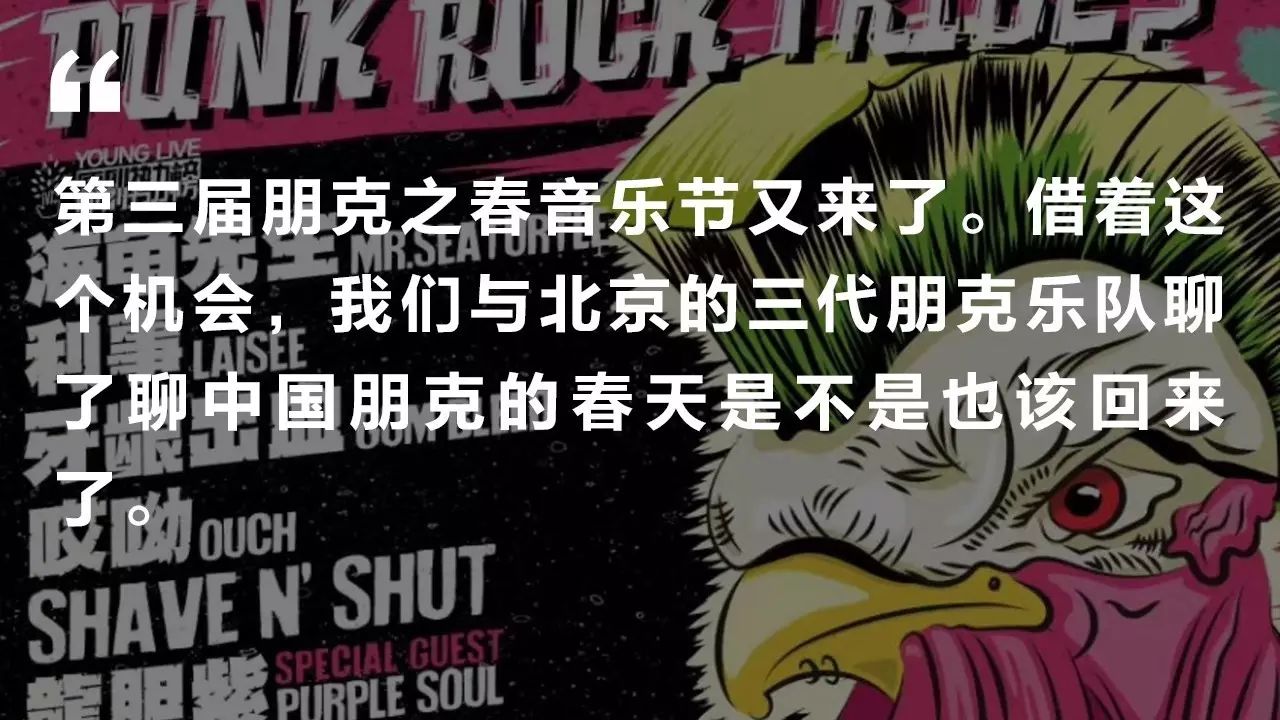
“朋克” 这词吧,非要下定义挺难的。往窄了说,可以指一种音乐类别和这一类别的音乐人;往宽了说,所有刺儿头、混蛋和不服气的家伙都是朋克。往实了说,可以是已走过近五十年的内蕴丰富的历史文化;往虚了说,“操,我就不” 和 “操,我偏要”,就是朋克。
但无论怎么看,位于五道营胡同的 School 酒吧都可以说是北京最朋克的现场酒吧。
三十多年前开始玩摇滚,长年活跃在北京地下音乐现场的老炮儿王迪,熟悉北京几乎所有现在和曾经热闹过的演出场地。有一回,王迪在 School 门口看到店员一箱箱地往外拎空酒瓶,吃了一惊 —— School 居然有消费。要知道,几乎所有做不下去的地下现场酒吧,都死于无消费,即使现在经营着的其他 Livehouse,也难破 “场地无消费,火了旁边的羊肉串和小卖部瓶啤” 这一铁律。“School太奇怪了!”
在 School,演出的乐队和看演出的人都喝酒。有时演出还没开始,就有人跑门口吐。大部分时候人们不会在演出一结束就作鸟兽散,真酒局这会儿才刚开始。
朋克演出格外多,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朋克与酒从不分家。除此之外,School 老板刘耗和刘非,都是嗜酒朋克。刘耗是朋克乐队 Joyside 和赌鬼的贝斯手,刘非是朋克乐队人体蜈蚣主唱。如果你一进门,就看到酒吧老板和一圈哥们儿正玩命煞,怎么好意思不喝一个,只要喝了一杯,你就别想走。刘非说了:“我们是用命在干这事儿啊!”
如果顺着北京朋克发展历史往前捋,第一拨无疑是 “无聊军队”,刘耗所在的 Joyside 这一时期可以算是第二拨,再往后常常在 School 演出的年轻乐队,便是新的一拨。

王旭(左)和王迪(本文图片摄影均由小猴提供)
1997年左右,北京语言大学西面遍布脏串摊、发廊、小店铺,巷子深处,一家名叫嚎叫俱乐部的酒吧开业。那年王迪34,他走进嚎叫,发现一帮不到二十岁孩子的朋克演出,音乐粗糙却有力。他们完全不同于老一辈的摇滚乐队,显得直接、冲,年轻得无所顾忌。王迪从那时起开始和他们混在一起。
这些乐队是69、反光镜、脑浊、A-jerks 等一帮年轻朋克。两年后,王迪为这些掀起北京第一波朋克浪潮的乐队集结录制了专辑《无聊军队》。
王迪记得,2000左右,他到远在北五环的清河找这帮孩子玩。四周一片荒凉,遍地荒草,走了10分钟才看到一家马兰拉面,一人吃一碗拉面,特高兴。他们不工作,天天厮混在一起死磕乐队 —— 至于找一工作上班嘛,挺丢脸的。
“家在北京,朋友在北京,饿死挺难的,怎么都能活。”

刘耗
在他们之后,刘耗、边远、辛爽组成的 Joyside 乐队也住到了清河。
他和另一个乐队一块租房。六个人,一个月房租900块。起床就轮流排练,排到晚上就喝酒。每天晚上都有朋友来,兜里揣着三十多块钱,买一大堆啤酒,大家凑一块儿就着馅饼喝。那段时间乐队出歌特别多。到录第一张专辑时,他们一共排出三十多首歌,收录了17首,还有许多都忘了。
到2004、2005年,北京的朋克乐队多达三四十支,朋克网站、论坛如 “朋克俱乐部” 和 “朋克地带” 上聚集了一大帮朋克音乐爱好者。迷笛音乐节固定安排朋克舞台,还有许多 DIY 的地下杂志。2005年,刘耗帮蜜三刀的雷骏筹办第二届朋克音乐节。20块钱一张门票,一共卖出2000张。
王旭那会儿是 Skinhead 乐队 Life for drinking 主唱。他记得那两天,恨不得整个新街口都是让他一见就兴奋的皮衣、马丁靴、Mohawk 和光头。朋克们五六人一撮儿来,五六人一撮儿走,约在距离演出地一两公里的地方见面,一堆一堆地走,制造气势。

刘非
2009年,Joyside 解散。五六年间,在 D22 一场一场的 Joyside 演出和一顿顿大酒里,一帮年轻人聚集起来,因为酷爱最便宜的金酒,便自称为 “年轻帮” —— Gang of Gin。这一年许宸大四了,进入了年轻帮喝得 “没有明天” 的生活。
刘非和许宸都在其中。
刘非第一次看 Joyside 演出时就被震慑了,从没见过拎着整瓶金酒就上台的乐队。这个乐队几乎从没好好完成过演出,有一回,鼓手关铮打到一半就跑外面吐了几分钟。
后来刘耗在鼓楼东大街开了家古着店。下午五点,所有人自动聚齐,店门口支个桌子,开始吃饭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扫大街的都扫了两圈。
喝到了2010年,刘耗和刘非琢磨,既然都这么爱喝,干脆开一酒吧,于是有了 School。

许宸
那年许宸大学毕业,按照家里安排做电路工程,先到太原,后去了武汉。他的工作就是个包工头,每天盯着工人布线,跟甲方和经理三方扯皮,陪人洗脚、斗地主。
他一个月只休息一周,每到那周,他就回到北京,直奔 School,和一帮朋友聚到一起喝得昏天黑地,把6000块钱工资造个精光。工作单位有个比他大十岁的项目经理,自己带施工队各地奔波接活。许宸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三十年的模样,感到十分恐慌。工作了两年,他就辞职回了北京。
民谣开始走进主流视野。地下音乐场景的风向偏向后摇,又转向嘻哈。大型的音乐节越办越多,却已经没有一个再设立朋克舞台。2011年之后,王旭已经很难再看到那种让他兴奋的朋克范儿特正的场面,现在的演出,台上台下的穿着打扮,都合理而不 “夸张”。
2011年,许宸创办了朋克厂牌 D.O.G,带乐队、出唱片、办演出。扎进自己喜欢的领域也要付出代价。有时他做音乐节统筹,一天能接上一百个电话,几天下来,一天现场都没看过,累得庆功宴都去不动,差点儿把喜欢的事给做成不喜欢了。
2014年,他办了第一届朋克之春音乐节,那是北京已格外少见的朋克盛况,一连四天,但赔了几万块钱。第二届,时间缩短到两天。今年的第三届,也不知能否收支平衡。现在,D.O.G 带着十二支年轻乐队。许宸的日常工作,就是催着他们录音、写歌、拍宣传照、巡演。

年轻的朋克乐队已经很不一样了。王旭觉得:“北京朋克队伍里,老队员都比较 ‘片儿汤’(北京话,形容人没正事,净干些没用的),后来的,越来越规矩”。但整个时代都变了,新队员如果还 “片儿汤”,就好像装的。
2015年,王旭和朋友们组建新的 Skinhead 乐队 SHAVE'N'SHUT。他2010年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儿子,自己有一家家具店,卖丹麦1950年代的设计师家具。SHAVE'N'SHUT 绝大多数成员都结了婚,做乐队最重要的就是哥们儿在一块儿玩玩。王旭花一半时间陪家人,另一半,和哥们儿呆着,非常有谱儿。
Free Sex Shop 是年轻乐队中特别的一支,成员全是女孩儿。她们几乎都在刘耗的服装店做过导购,原本就是很亲近的朋友。几个姑娘每个人都会点乐器皮毛,有天开玩笑就说,正好组个乐队。第一次排练刘耗去了,看她们基础差得一塌糊涂,“1,2,3,4” 起来所有人各弹各的。过了一段时间,乐队排了三首翻唱,刘耗突然给她们安排了一次演出。她们硬着头皮集中排了五六首,完成了第一次演出。演完之后,大家认真起来,决定把乐队做下去。

崔洁
乐队里每个人都上班,工作挺努力。主唱崔洁是学服装设计的,在独立设计师品牌工作,每天坐班,即使前天喝得烂醉,第二天也一身酒气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之余坚持乐队非常累,但崔洁说:“朋克是不知疲倦的。”她们一周排练两三次,在同龄乐队中,算多的。前些年还好,这两年,大家的工作都步入正轨,协调时间简直太难,“你的生活里还有很多事,不会除了工作就没事干了。” 而乐队只是其中一件,“虽然是最重要也最好玩的。”
年轻乐队选择一种更有保障的生活,对自己负责,自己养活自己,也养乐队。现在,Free Sex Shop 可以靠乐队挣些钱 —— 够抵排练费。崔洁不打算把乐队当职业全职做,“如果把喜欢的事当工作,你为了挣钱肯定不得不做很多不喜欢的事儿,没法那么纯粹。”
再接下来,乐队还有可能面临乐队成员结婚生子的情况。“无论谁做出什么选择都没什么,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崔洁说,“但我一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许宸接了茬:“想结婚的就结婚去,想单身的就单身去,反正都会后悔。”

几乎没有乐队住在一块儿的,大部分人有工作,生活规律。玩乐队好像变成一项坚持的爱好,不再有 “死磕” 一说。年轻人好像活得理智也认真多了,不再选择那种 “玩儿” 起来的生活。
王迪说,时代变了,这么丰富的时代,哪儿哪儿都是你看得见的诱惑,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也会有别的这样那样的追求。好玩的东西太多了,不像过去,信息那么闭塞,搞乐队就是唯一的最好玩的东西。
许宸笑了:“是啊,天天玩手机!”

王紫璐在 school 酒吧二楼 摄影:杨毅东
The Diders 乐队是这几年间冒出来新朋克乐队中出挑的一支。主唱王紫璐可以说是朋克 “老队员” 风范仅有的继承人之一。这是个常常抢麦,天天喝花的家伙。
王紫璐初中毕业后便离开学校混街头。他第一次去 School 就因为亲了别人的女朋友被人狠揍了一顿,那场架弄坏了刘非租来的音响设备。为了赔上一千块钱,他到 D22当酒保打工挣钱。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后来,他拉人组了三人乐队 The Diders。2012年是他们的第一场演出,王紫璐在台上光了屁股。
The Diders 曾经是全北京演得最凶的乐队,常常到 School 任意加塞。过去一年,他们的演出少了很多。另两位成员比王紫璐大几岁,有家庭和孩子,很多时候,大家确实各有各的事。他们几乎成了 “演出前才排练” 的乐队。
王紫璐觉得这没什么,尊重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乐队才能走下去。他自己很快也打算结婚生子,“该有的总得有吧。” 不过,结婚住哪儿,怎么养孩子,还是到时再说吧。
第三届朋克之春音乐节将于2017年4月22日下午3点在糖果 LIVE 开始,你可以 在这里 购买预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