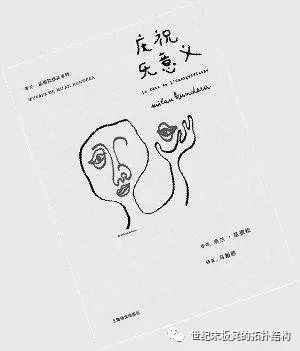
(Click here to read Part I )
/ 斯大林,加里宁和他的格勒/
对于鹧鸪的故事,后来的人们看出这是个玩笑。而布尔什维克们,对斯大林的谎言感到厌恶,但除了赫鲁晓夫,他们沉默,像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一样。赫鲁晓夫在盥洗室里吼叫,“他撒谎!”许多年后,他将取代斯大林,打碎他的每一座雕像,“他撒谎!”斯大林在墙壁另一面仰天大笑。
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欧拉七桥问题的柯尼斯堡,康德度过一生的柯尼斯堡,后来变成了加里宁格勒。加里宁,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老人,他的名字留给了这个城市。斯大林讲他的往事,尿急的加里宁没有勇气去厕所,直到扭曲的脸松弛下来,他又一次输掉了他的个人斗争。斯大林微笑看着他,这样的斗争是他暴躁一生的温情时刻——一个可怜人为他受苦——在他将个人意志投影到人们身上时——Ding an sich——这是康德的思想,加里宁正为自己的战斗焦头烂额,而对多年后的光荣一无所知。
阿兰满含温情地讲道:
为了不弄脏自己的内衣而受苦……当上了清洁卫生的殉徒……击退在生、在涨、在前进、在威胁、在进攻、在憋死人的一泡尿……还有哪一种英雄主义更为通俗、更为人道呢?我才瞧不起我们那些名字给马路冠名的大人物。他们出名是来自他们的野心、他 们的虚荣、他们的谎言、他们的残酷。唯有加里宁其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 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对他人造成过痛苦。
于是,加里宁格勒的命名是多么合理,斯大林再次嘲讽了政治的严肃性,他曾造成的更广泛的痛苦塑造了他僵硬的面具,而这一种微小的个人的痛苦却唤醒了一种感情,在个人的感情下,康德什么都不算,这是加里宁格勒的光荣。朋友们存活下来的世纪里,察里津改成了斯大林格勒,后来改为伏尔加格勒;圣彼得堡改成彼得格勒,再改成列宁格勒,最后改回圣彼得堡;柯尼斯堡改成加里宁格勒……但是,加里宁格勒留下来了,永远留下来了,不会再改了。
/ 庆祝无意义 /
庆祝,本是一个不可解释的谎言造就的鸡尾酒会。达德洛的生与死同时庆祝的美妙念头,熄灭于医生的诊断,死亡的回忆好像滞留在心中,不吐不快,他轻描淡写,说出癌症的谎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谎,这没什么道理可言,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除了满足一种存在主义的要素罢了,但是他确是找到了自己的好心情。
酒会上,大家似乎都在寻找一种实在的,有意义的好心情,终于无功而返。凯列班在自造的语言中迷失,面对自我的情感,没有想有所改变;拉蒙的那喀索斯幻想无法博得人缘——即使他对玩笑有精彩的表述;夏尔看到一根小羽毛在天花板下落下又升起,想到惦念的天使,与陪伴的母亲;阿兰靠在墙边,想象一个被抛弃,后又不得不重生的自己出生前的故事,并等待卡列班来打碎那瓶雅马邑;达德洛和卡格里克用口才吸引女性,前者的高深莫测比无用更差,而毫无趣味的话语摆脱提防,是无意义解放了某个她。那天,斯大林和同志们看到,一位天使,落了下来。
在卢森堡公园,朋友们想到了隐喻与一致性。拉蒙爱公园的人们胜过爱夏加尔的变质象征,“到处都存在一致性,但是在这座公园里有较多的一致性。这样你可以保持你的个别性幻觉”。啊,个别性是一种幻觉,阿兰愿作这个结论的捍卫者。所有的肚脐都是相似的,不同于大腿、乳房、臀部,不可能去识别你爱的人。爱情的光荣在于唯一性,而肚脐号召去重复,这是这个千禧年的象征,当然,所有时尚都会过时的。
这时,面对一个猎人、一个撒尿的人、与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无穷的好心情迎头赶上。朋友们动了真情,庆祝生与死,庆祝生活的反复、隐喻、和无意义。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