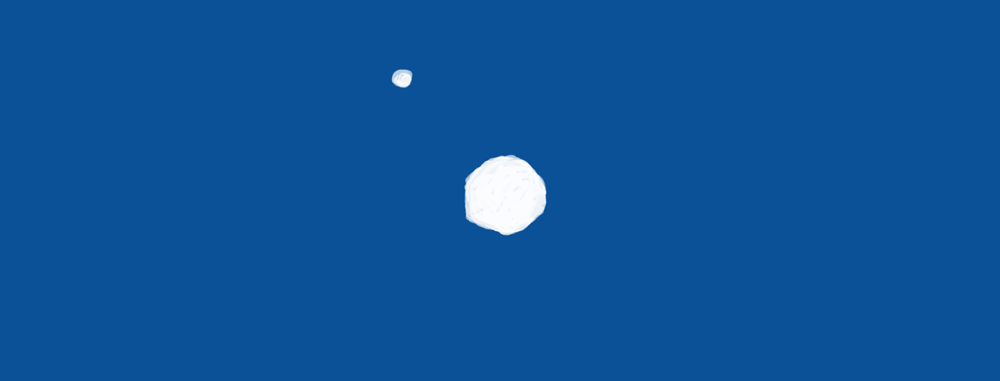
“
如果大家细读《聊斋志异》就会发现,全书近五百篇作品,
能够吓到人的其实超不过两三篇。
”
“
客观来说,孙悟空形象中确实有
哈奴曼
的影子,这是无可回避的。
”
科举考试对士人的意味
“
不是他们平步青云、光耀门庭的现实依靠,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泯灭希望的无尽折磨
。
”
“
《红楼梦》不仅写出了
不同身份人物
的人生困境,也写出了人在
不同年龄段的各种苦恼
,这些困境和苦恼不是说解决就能解决的,有不少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也许这就是
人类的宿命
。
”
*作者:苗怀明 主编
*上册:《世说新语》、唐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
下册:《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侠义小说
*定价:88.00
中国古典小说
是透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绝佳窗口
中国小说普遍具备
“世代累积”的创作特征
,决定了在小说里沉淀了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内涵,此外它也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
审美趣味和现实关照
。
心怀天下的
大义
与
精致的利己主义
并存;英雄
快意恩仇
的行事,却又有无尽的寂寞
枷锁
;
自由、规则
的相容与相斥;读书人的
傲骨
与现实
窘境
的相互交替;黑暗时代的
畅谈
与无声中的
反抗
交相辉映;这一切复杂的情感与现实尽在古典小说中流淌,无声无息,令人百味杂陈。
孙悟空的“国籍”问题
一度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围绕其原型来源,形成两种主流见解——
外来说与本土说
。前者主张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后者则认为中国神话传说中固有猿猴形象(如无支祁、白猿精等),不必从国外“舶来”神猴。比较而言,前者的影响力与接受度都胜过后者。
客观来说,孙悟空形象中确实有
哈奴曼
的影子,这是无可回避的。求法故事本来就与印度有密切关系,而自唐五代以迄宋元,《罗摩衍那》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也是历史实际。不过,说
孙悟空是“舶来品”
又是片面的。故事的生产与传播者毕竟是中国人,本土知识是构造故事的基本材料,而孙悟空形象中也确实有本土神话传说人物的影子(不止神猴,还有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权的刑天等)。比如,元明时期的孙悟空还不是“超我”式的英雄,带有很强的“妖”性,尤其《西游记》杂剧中的孙行者,满口秽语,贪淫谑浪,简直像个市井流氓。这部分基因当然不是来自哈奴曼的,而是来自白猿精等妖猴。
所以,对于孙悟空“国籍”问题,我们今天一般采取折中态度,这不是“和稀泥”,而是尊重历史实际。
然而,光解决“国籍”问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外来猴与本土猴是如何结合的,这就要注意边疆地区(尤其多民族地区)的作用。
按印度神猴的故事传入中国,主要通过三条路径:
一是北方丝绸之路,二是南方丝绸之路(即川滇缅印通道),三是海上丝绸之路。陆路来的大圣,无论走西北,还是由西南,都要经过
当地“猴祖记忆”的
过滤。
藏缅语民族的祖源记忆中普遍存在着以猴为始祖或图腾的神话传说与历史遗迹,它“几乎覆盖了藏缅语所包括的各个语支的民族”。王小盾将相关神话传说分为四类:猴祖创造人类,婚配育人,物种进化,灵猴。总体来看,这些神猴带有“英雄”色彩,是“善相”的。从陆路传来的哈奴曼,要进入中原地区,必须经过这重“猴祖记忆”的过滤;外国的“英雄猴”要与中国本土多民族的“英雄猴”相结合,最终形成自觉帮助取经人达成愿望的“猴行者”形象。
海陆传来的哈奴曼略晚(在宋元时期),在福建地区登陆。这里也流行猴王崇拜。与西北、西南的猴祖不同,福建一带的猴王多表现出“恶相”,令民众畏惧。这些猴王能作祟,善祸福人,当地百姓需要虔诚供奉他们。《夷坚志》甲志卷六就记载福州永福县能仁寺有猴王作祟,波及“福泉南剑兴化四郡界”,“祠者益众,祭血未尝一日干也”。
这些猴王被当地人尊称作“通天大圣”或“齐天大圣”。这与瑜伽教有密切关系。瑜伽教源于佛教密宗,北宋时已在福建流行,南宋以后,该教派的法师以云游形式活跃于乡土社会,作为提供禳灾、超度等仪式服务的专家。瑜伽教中有不少“大圣”,如猪头大圣、象山大圣等。猴形的通天大圣、齐天大圣,应该也是瑜伽教信仰与当地原始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在元明杂剧(如《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类形象,他们身上带着妖性,有凶顽的气质,当然也有反抗的精神。
海上来的哈奴曼需要与这些“大圣”相结合,形成带有“叛逆”色彩的猴王形象。这是很重要的:“善相”的猴王是虔诚的、恭顺的,如果没有“恶相”的猴王作为补充,也就没有“大闹天宫”的精彩单元,后来小说中的孙悟空也就不能具备弥足珍贵的反抗精神。
更重要的是,“善/恶”两面便于更好地塑造人物,尤其是表现人物气质、性格的蜕变。读者们会发现,以
“真假美猴王”
为分界,孙悟空的气质、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六耳猕猴被佛祖打回原形后,悟空表现得更虔诚、笃定、恭顺。对此,网上一度流传一种“阴谋论”解读,认为被诛灭的是真猴王,留下的是假猴王。其实,六耳猕猴就是悟空,是其“恶”的一面;六耳猕猴之死,代表悟空的妖性被涤净,凶顽、叛逆的劣根被剪除,更进一步说,是实现了“求放心”的宗旨。
这当然是与小说主题相关的,但也是一种高级的人物塑造。我们常说,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静止”的,即气质、性格不随情节发展而变化。这固然是事实,但许多经典文学形象的气质、性格是变化的,孙悟空就是一例。这倒多亏了他的“混血”来历。
节选《西游记》:现实与幻想
苗怀明,1968年生,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古典小说领域最活跃的知名学者之一。“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gudaixiaoshuo123)创办人及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在《文学遗产》《文献》《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等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风起红楼》等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