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点感想,不站队。记得大学时候一个教授说,他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个翻译,知识人似乎更好一些。说人是分子有种战斗的意思,有责任压力优越感在,说成是人了,就显得平和许多。
我觉得这两天大家闹翻的这期节目本身已经非常成功了,用马东的话说就是带来了价值观的争论。而且要感谢老许,在这个节目剪辑的时候,也留下了自己各种尴尬大笑和坚持己见的瞬间。在这一点上,他是很坦白的,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固执或者自信,一种坦荡。谁过多去解构这些动机也没有意义。
其实我觉得
95%
和
5%
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必要去锱铢必较对号入座,把自己和假想的对方阵营对立起来。虽然朋友圈大部分人都是文化人各路精英,这两个所谓阵营是有模糊的,是有人游走之间,也有人分裂撕裂的,很多圈子是重合的,当然有些人也渐行渐远。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些人和他们价值观的矛盾,组成了我们的世界和生活,这个时代。
纠结阵营对立本身就把自己套住了,去表态深刻解构这期节目。当然了如果深刻解构带来了思维乐趣也罢了,但事实上很多人只是为了解构而解构,说了很多其实语义不明,逻辑混乱的话,吊了一些书袋。
马东谈到说自己八年留学生活带来的不是知识积累,是看世界视角的改变(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点还比较有同感。我觉得我所获得的更多也是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开放和反思并存的,比较平和、不带目的性的心态。
我学的东西是冷门甚至是精英知识分子趣味的历史,看了很多和绝大多数人、所有各界精英前男友、甚至在文化土豆都无法交流推荐分享的书(但当然了我们有各种别的精神交流,比如看《奇葩说》和各种剧)。我学的历史研究的课题,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都不是有用的干货,学这些给我带来直接益处,是开心。至于对我之后从事的各种事只能说是潜移默化和间接帮助。所以执著于找到百分百可以交流的伴侣是不可能的,这点我很多年前就平常心了。
学冷门文科优越感不是没有,但只会在需要的地方慎用。比如有些朋友现在碰到热点问题非常及时抖机灵的说法,我看到还会不适,我现在也懒得去指出。一来因为忙,二来我觉得思维方式和视角严谨程度,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解释清楚的。
读历史对做餐厅的
PR
和创意有帮助?能帮助我半年和同事们一起把它做到纽约时报年度十佳么?非常难讲,但是受的一些训练时可以的,比如写作的水准,阅读的训练,比如搜集资料的能力,甚至包括思维方式,比如那种沧海一粟的感觉,会帮我避免很多争当人上人的虚荣狭隘。或者说是一种底气,我并不觉得在这个时代,选择回国很长一段有什么可以惋惜的,思路是灵活的,本事够,在哪里都可以做各种各样让我自己觉得开心有意义的事。
那时候因为当助教,要接触许多九零后。要让他们爱听和真的
engage
进去难学的历史课,就必须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和看世界。我把这当作一种平衡。我挺享受每个星期讲讨论课的时段,以及之前的备课时间,觉得思维是活跃的,说得功利一点,上课的交流是有营养的。
只要你愿意主动去交流,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定义和设置,心态是开放的,那么被很多人看作是浪费时间的教学过程就是放松和愉悦的。
今天看完他们的对谈,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跟本科生教美国历史就好比《奇葩说》,是大众传播的作用,一个鲜活的话语平台,我们助教传播的是历史通史的知识和话题,我们也经常让学生辩论,因此激起他们学习某个知识点的兴趣。我们教本科讨论班,是不能用自己研究生讨论班的要求和风格的,这里的边界和分寸是我们经常反思的东西。学生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历史研究者,他们对知识的把我就是常识和通识的,虽然我觉得我们当年对学生美国历史的要求,其实相当高了。所以这么看来,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年轻人,也有更多责任,甚至有比老许更多的挣扎和痛苦,都是可能的。我正因为想避免这种痛苦,更倾向于去把读历史书当成开心的事,才决定不走这条路。一种有多种选择的自洽或者是怂。
所以我一直相信,评论和批评是有边界的,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如果是要在启发民智和传播知识的角度,就要学会转变思路,用开放平和的心态看待新事物,而不是一来就说这个事物不是什么,这个作品没说什么,是尴尬的,这个节目讨论的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观的碰撞也是一种传播方式,所以就有了这个对谈,启发了人们反思和思考。
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有时候经常会将自己的身份代入进各种评论中,虽然评论是存在即合理的。最近有约稿让我写《二十二》的影评,编辑给我参考一篇做口述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的影评,影评大致观点说导演没有通过性别视角挖掘这些老人在历史反思中的agency的作用,是一部点到为止取巧尴尬的作品。我当时看了就很反感,导演是拍了纪录片还原humanity给老人,拍片子给大众看,为什么非要去挖掘她们的 agency 才算是完美深刻的作品,这是研究者学者身份代入太深。
不过,每个时代都各有各的精彩和荒诞,就好像每段人生也是如此,有的人注定相遇,也注定分开,都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我学历史的感想。我觉得马东和许知远都是很可爱的人,正因为他们非常自我的存在,才让这个时代有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知识分子对时代表示出批判反思和惋惜也是正常的,没有人可以要求他们必须入世,也没有人可以成为时代的代表,它甚至比美国的 Roaring 20s, 更像是 Roaring 20s。放开心态,多看多想,尽情尽兴,去学习去表达,享受这个时代。You only live o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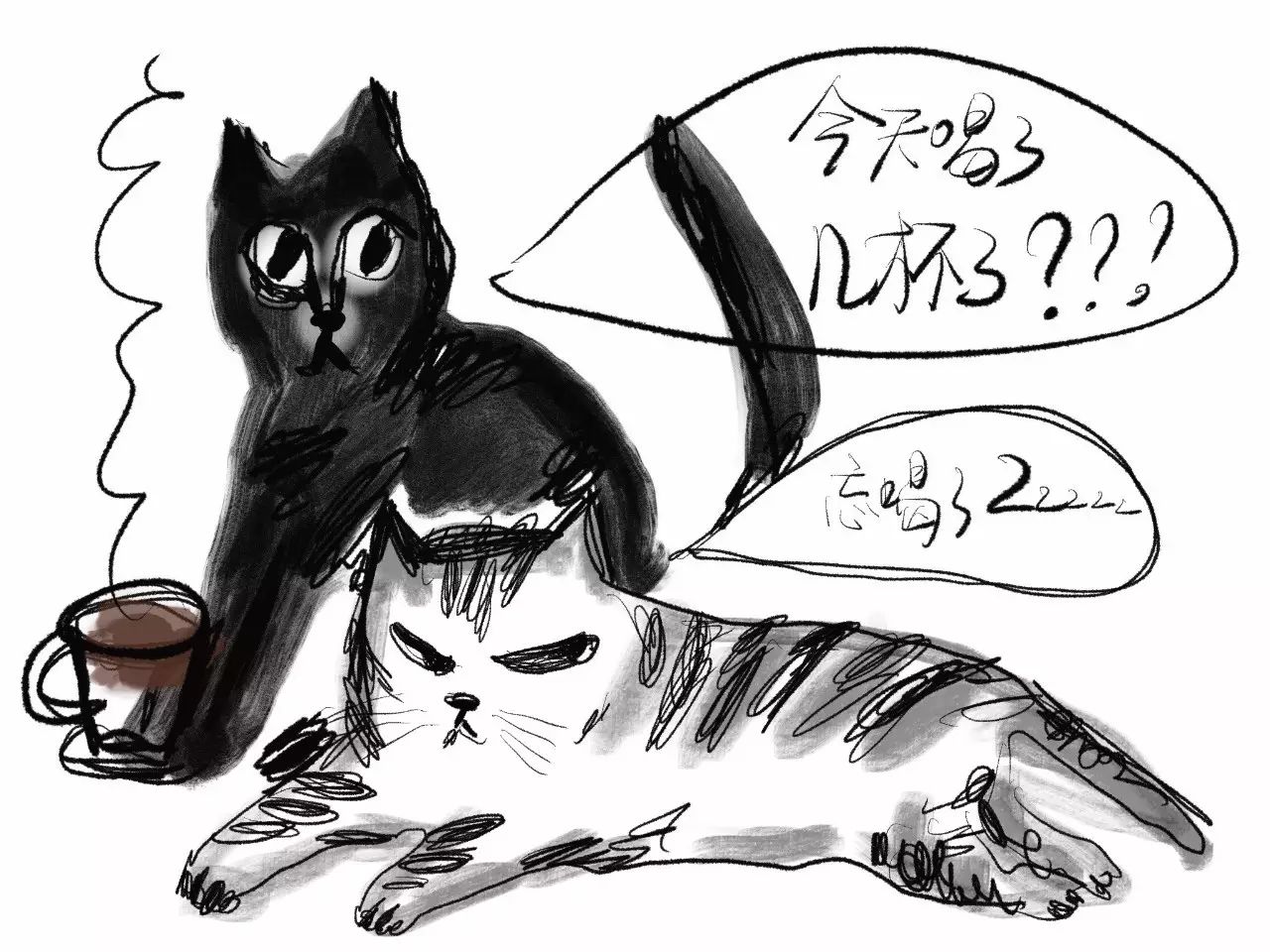
昨天画的纯属用来做题图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