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作者投稿 作者 | 靳 帅
编辑:学妹(ID:xuemei700) ,媒体转载请联系学妹要授权

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敦煌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的同学朋友都是这里的人。而我也是一口当地方言。可我并不是敦煌人。在填各种信息表格的时候,籍贯一栏上清清楚楚的写着我是“甘肃平凉”,或者是“甘肃静宁”。这是一个盛产苹果的地方。我的祖辈就生活在那里。

大学里的好多同学问我“你是哪里人?”可我渐渐发现,自己的籍贯认同日趋模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父母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外出流浪,漂泊在外,乡音未改鬓毛衰,却仍是这里的“外地人”。而我以髫龄之年背井离乡,在此地读完小学、中学。读大学时对外宣称的籍贯仍是我从未生活过的故乡。故乡啊,我也再不可能重归于你。今年回乡烧纸。我和爷爷从沟壑中的小路上散步回来。他望着不远处故乡苍黄土老的院落对我说:“现在看来,你们兄妹三个是不会回来了。你爸爸也不会回来了。可惜我和你祖母在这古院里白守了一场。”是啊,我们在外地读书生活,或将在另一个外地成家立业。故乡,就这样被我们抛弃了。
约摸三岁的时候父母带着我离开故乡,坐着大巴车穿过乌鞘岭,经过河西四郡到敦煌。车子穿过武威繁华的霓虹灯火时,父亲对我说“金张掖,银武威,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那时虽懂得这民谣的意思,却未有多么深刻的领悟。只是觉得河西比河东的故乡要富裕很多。
或许是因为富裕,我们在当地都要被贴上“外地人”的标签。他们对于外地人不种地而经商十分鄙夷。他们认为外地人贫穷却又精诈。如果有本地人嫁给了外地人那就是“下嫁 ”。我作为一个“外地人”的孩子,在接受教育的时候,是需要看表现而享受各种政策的。直到高考那一年,对于那些成绩较差的外地生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尽管都拥有相同的省籍。

在敦煌的十几年里,我们几经搬迁,最后一直生活在敦煌西郊的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座古塔。 据传,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大将军吕光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东归传经。当行至这里时,鸠摩罗什所乘的白马病亡。当地佛教信徒遂葬白马于城下,修塔以纪念,取名“白马塔”。后来几经重修。最后一次重建是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3年-1844年)。小时候,我常常去瞻仰这座被农田房舍所掩锁的古塔,周遭空旷寂静。笔直的新疆杨一排排的伫立在四周,夏天的时候,风吹动苍翠的树叶飒飒作响。冬天的时候,干枯的树干直插蔚蓝无洗的天空。它陪伴我走过了热闹的小学,欢乐的初中以及匆忙的高中。如今,它和我又目睹着这个村庄是如何一步步像费孝通所言的那样被废墟与高楼慢慢地“蛀蚀”。
小学的时候,村子里上学的孩子很多。因为是城郊,还有许多像我一样“外地人”的孩子转学到这里。每天放学,都是排队回家。有时候学校还会清扫村子周围的垃圾。更多的记忆是每年秋季的集体拾棉花。那个时候棉花的经济效益很高。许多棉农种植的棉花到秋天靠几人之力无法及时拾完,学校就组织我们摘棉花,为此往往要停课一周多。学生的课桌也因长期不上课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沙。棉花有一种死敌,那就是棉铃虫。村委会也会鼓励我们抓棉铃虫,好像一毛钱一个。那时课后无事,我们把抓来的棉铃虫拿来玩,抓住它的尾巴,它会不停的摇头,我们都叫“摇头脑”。
也正是这个时候,从河东农村涌来大量棉工到这儿,或是到更西的新疆来拾棉花,以满足棉农的需求。在我们上学的乡村公路上,这个时候也常常可以看到带斗的拖拉机满载着瓷实的棉花哒哒哒地远去。直到高中,在上学的必经路口,还是聚满了拾棉工和招收拾棉工的棉农。年年如此,竟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人才市场。每每深秋十月的清晨,天上的月亮清亮,人们聚集在这里,讨价还价,乐此不疲。这个候在我的眼中,小村依然是十分繁盛的。

近几年在外读书,唯有寒暑假才返回家中。不经意间,小村的支柱产业棉花种植因经济效益低下,年年亏损,已经被抛弃,逐渐被葡萄所替代。前一段时间和一位卖水果的叔叔聊天,他是本地人。他说今年农村的葡萄已经是第三年没有收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的是因为摘收前的一场雨,有的是卖给批发商之后,批发商批发不出去,导致批发商欠债难还。不得已农民们都到市上去闹了。也有改为种植果树和蔬菜的。但是还未等到成果,村子大半已经被房地产商征收。自上高中之后,小城逐渐在蔓延拓展,城郊周围的村庄渐被蚕食。征收之后的土地闲置数年,荒草遍野。早已不是满目丰实的景象了。村里小学的孩子也越来也少。十几年前的排队放学的情景也早已不见了。失去土地的农民除了补偿所得的楼房和款项外,他们也失去了赖土地为生的工作,职业。
被强迫由农民变为市民之后,他们何以为生?这是对于他们来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房地产商并未给他们予以一份工作。早在土地未征收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农民放弃了种地,改为开饭馆,跑出租等。事实上,这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种地已满足不了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寒假和小学同学聊天,他说,地早都不种了。现在谁还种地?这个时候,他们不再鄙夷经商做生意了。我的同学,他们的父母当了半辈子农民,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在失去土地步入市民生活后,他们更多地是依赖他们即将成家的子女。子女在哪儿,他们就生活在哪儿。我的同学们和我一样,当然并不会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即使是初中毕业,也会选择在城市中找一份工作。姨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敦煌扎根的。如今已是彻头彻尾的本地人。他的家在离市里有十几公里的农场里。十几亩好地多年来他早都不种了。而是在保险公司上班。他的儿子在新疆工作后,他准备离开这里,到儿子身边去。闲谈时我问他种地收入怎么样?他说种地一年就挣了六千块钱,还不如我在儿子那儿找个看大门的,一个月至少两千块钱呢。
土地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这些被农民抛弃的大片的荒地怎么办?连靠种地过上比较富足生活的河东都是如此,那我的故乡河东农村是什么样子?
二十年间我们只回过两三回故乡。那时我还很小。那时兰州的天还是长久看不见太阳的阴沉。市内还有电车划过。我们在村口的小路上,路过一旁的人家,他们放下手中的活,远远地驻足观望我们,嘴里念叨着,“这是趸趸子一家子么”。父亲随记微笑着与之寒暄而去。那种亲切的乡情是永远忘不掉的。大山深处的故乡依然十分热闹。

记忆最深刻的是碾麦与放牛了。河东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深处,是我并不熟悉的家乡。故乡院子前的麦场边有一棵很大的杏树,是祖母生前所栽。树身能遮挡出一大片绿荫来。每年收麦碾场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们常会在那儿休息,扇着草帽,喝茶吃瓜;小孩子也叽叽喳喳的跑来跑去,嘴里鼓着新摘的桑葚。故乡六月,麦浪滚滚,似黄云极目,谷糜高粱,似翠浪平铺。大人们割麦扎捆,我们最爱放牛了。暑假的农村,孩子们大都无所事事,我们吆喝着自家的牲口到山沟里,到收割完的麦地里放牛,等到晌午炊烟四起,或是日落西山,大风鼓鼓的时候才尽兴而返。而这已是记忆中十几年前的事了。
长大之后,便再也想不起故乡的模样。直到上大学之后,才时常回去看看孤单的爷爷奶奶。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去年冬天,奶奶病危,父母回乡,我也去探望。在故乡的不多日子里,故乡的种种图景,让我感触颇深。路过的人家,他们也会远远地站在青苔干黄的院墙上看着你,直到走近之后会关切地问你一句,“你是谁家的娃娃?,你要走谁家去呢?”这种因地缘与血缘而自然融流而来的温情地问候会消释久别之后怯怯的心情。奶奶病逝后,周遭的邻里乡亲们都来帮忙。丧事上一系列繁缛的礼俗让我再一次对乡土中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
离开家乡数十年,村里常年被山雨吹破的路已被拓宽铺平,听说明年要硬化。有的乡亲们是富了,可仍然赶不上村外日新月异的世界。“近世人心趋末富,其权加本富之上”。许多乡亲富了,但并不是靠着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依然是在外打工,漂泊亦或是在本乡做生意。我和母亲沿着小时候放牛的山路上漫步。黄土高原上,大片的梯田杂草丛生,一看便知已是荒芜数年,无人打理。夜晚的时候,繁星满天,寂静的村子让人感到恐惧。远处的大山静静地伏卧在那里,唯有几声犬吠和几家灯火才让人感到踏实。就是在白天,炊烟稀少,人声罕闻,依旧寂静。乡亲们说村子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剩下的就是一些老人和妇女。这些抛弃土地的人,无论是考学还是打工,他们有一种浓重的共识那就是在农村,注定是没有前途的。他们不愿意待在农村,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伴随着青壮年们逃离农村的,是教育的空虚。现在村子里没有小学,乡里没有初中,他们都集中去了镇上,县城里。长途奔波去上学,或者很小就学会独立住校。一旦他们考上学,他们又是新一代的农村的背叛者。

在逃离农村之后,农村剩下了一个空壳,这在甘肃的东部,平凉,庆阳,白银,这些被群山包裹着的农村里,尤为突出。在这些地方,比起河西敦煌,是连城市都不愿入侵的地方。它们失去了青壮年,也就失去了再造乡村的血液。我不知道,一旦父辈们老去,这些空虚的农村将走向何处?这种主动逃离土地与被动地城市入侵成为了我所亲历与目睹的农村现状。我相信这不是个例,而是整个甘肃,乃至西北农村的缩影。
不光是他们,这些年轻的一代认为呆在农村没有发展前途,一些名流也是如此。这似乎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共识。俞敏洪在中央电视台青年公开课《开讲啦》谈到,自己当农民在家种地是没有出路和出息的。从江苏宿迁农村走出来的刘强东也不例外。我初中的老师曾对我们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世世代代都是穷人。”没有一个老师不鼓励我们考出农村。难道在农村种地真的没有前途吗?或许在大部分地区是,种地无法获的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水平。而孩子的教育与老人的医疗却成为了背负在父辈身上的大山。
近几年,农村空虚与衰败的现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成为时代病痛的神经。稍有刺激,便会做出剧烈的反映。去年春节一则“上海女因江西男友家的饭而逃离农村”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社会、媒体、网络的种种表达、渲染、评论之后才发现是一则假新闻。实质上,一则假新闻之所以能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民众内心对于上海与内省、城市与农村、恋爱与婚姻等在在巨大悬差的间接发泄。在这之前,《一位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亦爆红网络。在引起许多人对于农村现状共鸣的同时,许多人也指责春节“返乡体”、博士“返乡手记”的盛行是知识分子爱唱衰农村。其实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春节返乡体”会在这个时候泛滥网络?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会唱衰农村?是其特有的习性造成的还是这个时候的乡村真的出现问题了?

他们在还没有彻底读懂赵旭东2008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成为问题的乡村与乡村研究成为问题》一文,就借来批评那些唱衰者:“他们或许是有过在乡村生活的经验,或许是访问过几户农民,或许是仅仅在乡下随便待几天,甚至还没弄清楚一些信息报告人在乡村里的身份及其口头报告的可信度,就匆匆赶回城市自己的家中,开始撰写有关中国乡村问题及其出路的调查报告了” !其实无论是各类“返乡体”还是“返乡手记”他们的关怀与初衷并未有何差错。它们之所以能集体泛涌是知识人对于这个时代病痛的细微观察与渐进反思。正如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派关注农村一样,是因为乡村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是时代不同,病症殊异罢了。而我与那些唱衰者所目睹的乡村图景亦是大同小异。
赵旭东认为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社会医生的理念,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的农村是有问题的。因此他们在不断地寻求改造农村的方式。最终他们归结为是农民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其实,在晚清以降,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传统城乡之间人才、教育等资源的循环流动终止。过去致仕还乡的乡绅不再回归农村。山西大学的刘毓庆就认为“乡绅消失后,乡村便不可避免的衰落。”农村道统断绝。土豪劣绅随之出现。(罗志田、关晓红等学者已做了深刻的讨论。)由此论之,民国时期的乡村怎能没有问题?那些乡村建设派又怎能是先入为主?
当然,这只是一己之见,赵文是相当有深度和思想的。赵旭东在追溯“晏阳初模式”产生源头后,讨论了作为行动主义者的乡村建设派、作为西方理论引用者却不顾实际的学院派以及当代乡村研究中回访范式的问题与责任。进而他追问道:“那么作为一位以冷静的客观描述为己任的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在面对受到伤害的农民或者受到污染的乡村时,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反应呢?干涉还是不干涉,这是摆在中国乡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学术伦理问题。”赵旭东在其文中亦有回答。他说我们应该“积极的参与观察和独立的理性思考,加上历史的过程视角和负责任的事件描述,并努力建构一个大家认可的基本的学术伦理规范;这些也许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无法避开的策略性选择及未来的努力方向。”我们个体的命运就像时代洪流溅起的泡沫,微不足道。但我们有责任在观察与记录乡村的同时,反思乡村的历史与当下,身体力行地去回馈乡村。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本次征文依然采用开放性选题,即“我的故乡:与费孝通先生对话”,你可以写在外学习工作的点点滴滴,人情冷暖,也可以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家长里短,还可以写环境的变化、交通的变迁,总之要以一个外出学子、游子返乡的角度去反观都市生活与故乡农村的变化,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那些在你头脑中挣扎的意象都可以在笔端倾诉。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可查看详情
·
·
·
END
l 后台回复关键词查看相应文章 l
论文排版 红黑榜 未来简史 没有抱负博士生 教师挖角之争 梦想 开题报告 页码设置 毕业论文 论文写作 科研必备 阅读技巧 英文科研写作 国家社科基金
据说学霸们都关注了这个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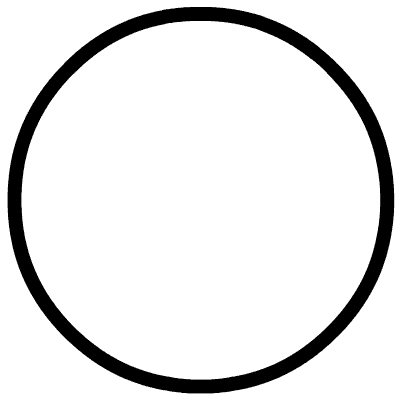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免费使用国家社科基金大数据查询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