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目前是解决执行难中红利最大的时期,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交不出合格的答卷,执行者就会成为“失信人”。
文 |
程余
来源 | 稻花蛙声微信公众号
在信息过剩的年代,“十年漂泊无人问,一夜成名天下知”实在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找个不远不近的朋友,借上千把块钱,无论对方怎么软磨硬泡只回一句:你去法院告我。等判决书下来,绝不要主动履行。这样,你很快会出现在网站上,火车站或商圈的户外大屏上,手机彩铃上,来电提醒上,以及各种限制名单上。你发现,自己从未如此广为人知。
于是,在一个老赖的无码照片与明星艳照以同样速度传播的时代,你也可以点上一支烟,在云雾中幽幽感叹:梦想如此廉价。
2016年3月,官方正式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平心而论,通过区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加上执转破和终本等一连串出清机制,这个目标的实现,也许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天马行空。
司法强制执行,从没有像今天一样挺着胸收获尖叫、鲜花与掌声,这是他们应得的。但更大的考验,或者说无从回避的命运,也许就在眼前。

经济学的一对核心概念,是平衡与失衡。经济学家们画了各种图表,盯着密密麻麻的曲线交叉点左观右瞧,相信能从这一个像素里看出决定人类命运的秘密。
强制执行的命运一角,也确实可以从曲线图里揭示。
让我们设想一幅曲线图。横轴是执行力度,纵轴是舆论效果。那么在一定范围内,这张图呈现为一条先是近乎垂直上扬,又逐渐收于平缓的曲线。
在一开始,这张图回答了为什么要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执行力度低,舆论效果自然也会“投桃报李”。如果不下力气解决执行难,舆论效果就只能低位徘徊。这样一种变相的互相伤害,当然不适合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期,是曲线逐渐上升的时段。执行力度不断加码,舆论效果也给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回应。不用怀疑,这可能是我们能够经历的最好时期;不要忘记,这是一条收缓的曲线,好时光不会永远持续。

一种新的事物,总是被误解,常常被反对。当人们对它习以为常时,新事物就取得了成功,但此时它也只能等待着被下一个新事物取代。
当执行力度上升、执行手段翻新,社会欢呼雀跃。但要不了多少时间,喜新厌旧的舆论也便会失去敏感——你是否意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只不过提出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却已恍如隔世。
执行力度—效果这条曲线,在理论上最终会到达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曲线的切线是与横轴平行的。换句话说,强制执行手段的增长,已经无法再拉动舆论效果,这是增长的极限。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从这个平衡点往后,曲线的后半段恐怕是一条抛物线。执行力度的进一步增长反而会引起舆论效果的下降。
这并不难理解。在执行领域,当有效执行已经看上去顺理成章,舆论最终会找到新的眼球增长点:执行名义有没有瑕疵?被执行人为什么拒不清偿?执行行为是否合法妥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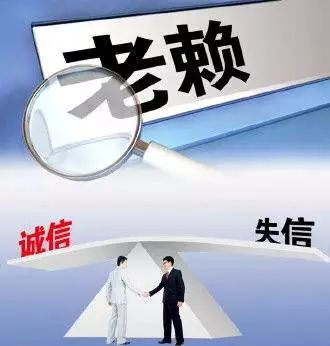
在这个阶段,神兵天降、果敢坚毅的执行法官形象,并不比一个深陷传销骗局而身无分文,为维持生计漂泊打工,急着坐火车赶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却发现无法买票的“失信被执行人”更有吸引力。
当执行者遭遇“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大帽子,你怕不怕?
但司法强制执行没有选择。毫无疑问,目前是解决执行难中红利最大的时期,如果不抓住这个机遇,交不出合格的答卷,执行者就会成为“失信人”。
曲线在纵向上遭遇断崖式下跌的后果,没有人能够承担。
无论是做事还是坐视,司法强制执行都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历史上常见的一景:当浴血奋战者提着崩了口的战刀踉跄着上前,命运正从王座上施施然起身。
要战胜必然的命运,司法强制执行的前路上,至少要跨过三重门。
第一重是执行方式。
曲线平缓时,最容易发生悲剧。一方面,可选又可靠的新执行手段越来越少,执行者不得不向新领域进行探索,而不熟悉就会带来不安全;而另一方面,舆论对于传统执行手段越来越麻木,这又迫使执行者走向新的领域。执行手段如何摆脱跑马圈地、先到先得的恶劣生态,又能否在重重压力之下成功跨越雷区?

第二重是执行者。
越来越多样的执行手段,意味着越来越高昂的沟通和维护成本。一个案子执行完毕,被执行人是否及时移出名单,是否及时通知有关合作者下架此前发布的信息?随着执行手段不断开疆拓土,有效的维护能否跟进,能否摆脱重建设,轻维护的困局,又能否尽量不授人以柄?
第三重来自审时度势。
当曲线逐渐走向平衡点,社会舆论对强制执行的关注点逐渐转移,执行者能否找到新的发力点?比如,在社会对执行权力扩张表示忧虑的前夜,执行者能否通过传递强化执行异议、执行监督的信号,提前抚平舆论的躁动与不安?
能够改变与不能改变的,都是命运。面对貌似必然的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接受无法改变的平静,改变所能改变的勇气,以及辨别这两者区别的智慧。
事实上,这才是面对横在强制执行前途上的命运时,我们需要打开的三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