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杨澄宇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最近的消息是葛宇路收到意大利米兰一所美术学院的留学邀请。
愿他不像云朵一般,被岩石所殴打。
不知道葛宇路被拆的时候,葛宇路有没有难过?
他的肉身有没有些许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的疼痛?
葛宇路拆了,我们在昨晚也旋即将这篇文章删除。
路杆还在,桅杆不倒。
亲爱的读者,再见我们时,你们已然迎着新的晨曦。
2017年8月6日,上海,5时14分日出。
本文约 1800 字,阅读约需 6 分钟。
“看呐,那条路是用我的名字来命名的!”
路人甲跳了出来。
你一定不理他。他有病。
路人甲的名字叫
葛宇路
。
大致搜寻沪上以人名命名的马路,会发现这些名字的前宿主要么是
红色(革命)
的:逸仙路、黄兴路、靖宇东路、靖宇南路、靖宇中路、晋元路、志丹路、子长路、自忠路。
要么是
无色(科学或文化)
的:毕昇路、祖冲之路、光启路、蔡伦路、张衡路、鲁班路、华佗路、行知路等等。
对于鲁迅我一直是犹疑的,按照他在《死魂灵》里的意头,他自己或许更愿意是
黑色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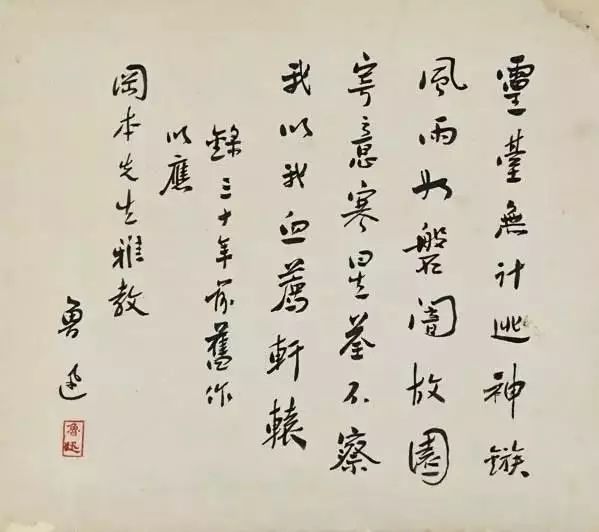
▲ 鲁迅手稿《自题小像》
“无色”的路里也包括外国人的名字:居里、爱迪生、法拉第、达尔文、伽利略、哈雷。这和其他大部分以科学家命名的路一样,可能都要归功于张江高科。
是的,我一直以为
道路是有颜色的
。
甜爱路大概是粉色的。
世纪大道是
银色
的,直通通的银色从硕大的日晷射出。
南京西路是
玫瑰金
的。
人民路是
炸鸡色
的。
衡山路大概是
酒红色
的。

▲
地铁1号线衡山路站的月台
或许它还有我们
专属
的颜色。
比如我在南京的天津路上拉过姑娘的手,那么它的色彩就是那
炫目
的女孩,她的名字就是那条路的名字。“天津桥头残月前”,桥与路重合;残月也被填满。
但这是只属于我们的颜色与名字,没法要求所有人承认。
所以,你觉得那个宣称自己命名道路的人有病。他不是已故的名人。
可是你忽视了一点,他曾被
认同过
,被某些地图软件公司
承认过
。我们现在认路,不就靠这些 app 吗?
纸质版的地图恐怕存在于姜育恒的歌词里和桂冠女诗人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诗歌里:
国家的颜色分配好了还是可以选择?
——最能表示水域特征的色彩是什么。
地理学并无偏爱,北方和西方离得一样近
地图的着色应比历史学家更为精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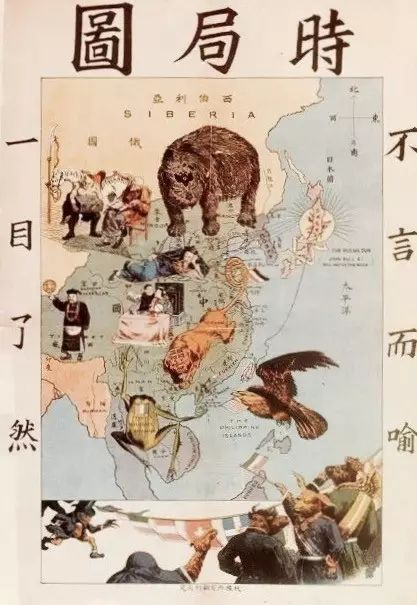
▲ 《时局图》:地图从来不是那么客观的,它不仅有颜色,还有浓厚的政治性。
但是,被
国家承认
才算呢!好了,这就是症结所在,葛宇路说这是行为艺术,原因也与此相关。
艺术在哪?
因为他让我们意识到了“命名”不是一件
随便
的事情。
当葛宇路认真地去给马路起一个“随便”的名字时,问题就显现了。因为无论有多认真,这个名字都只会是“随便”。
命名,是一件
神圣
的事情。
名字,本身就
超越
了符号存在。
《西游记》里银角大王颠来倒去喊“孙悟空、孙空悟”,就能把大圣弄得死去活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墙头的美女蛇的呼唤,肯定让小男孩又怕又痒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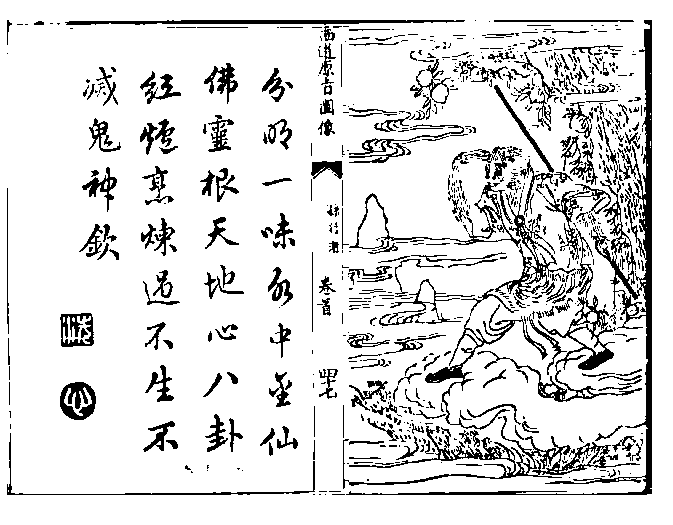
▲ 《西游原旨图像》
如何命名?
海子说:“给远山起一个温暖的名字。”
只有用
文学
,除此之外都超越边界。
因为首先,你得确定她是个
无主之物
。
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都是国家,岂能冠以自己的姓名?另外,道路因其公共性,是群众的,怎么可能用某一个群众的名字来命名?
“谁给你命名的权力?”
但人们有命名的
渴望
。命名即
占有
。
我们同样有对大地的渴望。地母是温柔的。“大地蜇睡着,太阳宿醉未醒”,人类想要在她的身体上建筑,并起一个私密的名字。这欲望也可向上,去做一个数星星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承认葛宇路的诞生有些许
叛逆
的因子在,这或也是他自认为是一种行为艺术的原因。对于这世界有那么丁点儿的反抗或占有。这是对权力机构的
质疑
、对公共边界的
试探
。
“凭什么我不能命名?”

▲ 拆除葛宇路
如果大家都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个名字,那么,它是不是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权力机构将会水到渠成地接受吗?道路的本质是什么?现代社会的道路不是鸡犬相闻、阡陌交通,而是本雅明的拱廊街,人们甚至可以做一个遛龟的人,但抱歉,
没有命名的权力
。
这权利我们已经
让渡
了出去。
这类行为一个更缓和的形式,是用骑行或跑步轨迹在地图 app 上画画。
那也是一种命名,不过是
即刻
的、
私人
的、
安全
的
。它又是一种
健康
、
减肥
的运动,而这又被种种商业模式所加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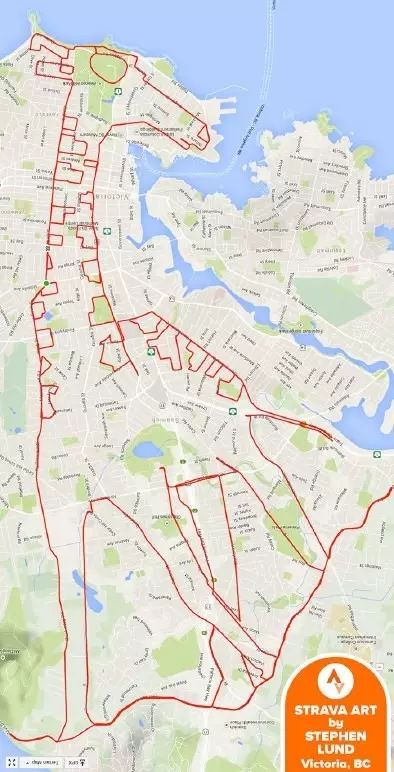
▲
Stephen Lund,长颈鹿(95.5KM,3小时30分)
行为艺术家则尝试过
更极端
的形式。
1999年3月,何云昌在云南梁河完成了《与水对话》的作品。他用吊车将自己倒吊起来,放到河中央,在胳膊上刺了两刀,血不停地往河里流。整个过程持续了90分钟。他让自己分割江河,成为江河的一部分,
成为江河
。
这超越了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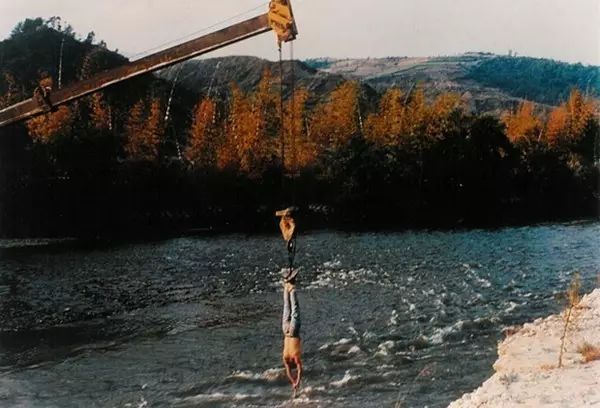
▲
何云昌《与水对话》,1999年
淅川人周梦蝶却说:
真难以置信当初是怎样走过来的
不敢回顾,甚至
不敢笑也不敢哭
——生怕自己会成为江河,成为
风雨夜无可奈何的抚今追昔。
好吧,我们得承认,有胆儿的行为艺术家们比诗人要决然得多。
我们最怕
麻烦
别人。
我们最怕
麻烦
不到别人。
哪怕是一条无名之路,命名的便利最终还是指向媒体的狂欢,打扰了世界的清净。
就是这么残酷,道路的诞生是为了
方便
别人,但它
没有
自己命名的能力,哪怕再简单的名字。
同样,大家也没有。
话说回来,还是诗人方法多,对于无法或不愿起名的诗作,大可叫《
无题
》。
这是一条短短的
永远走不完
的道路。

▲
Bob Dylan, Liverpool, England, 1966 by Barry Feinstein
文中图像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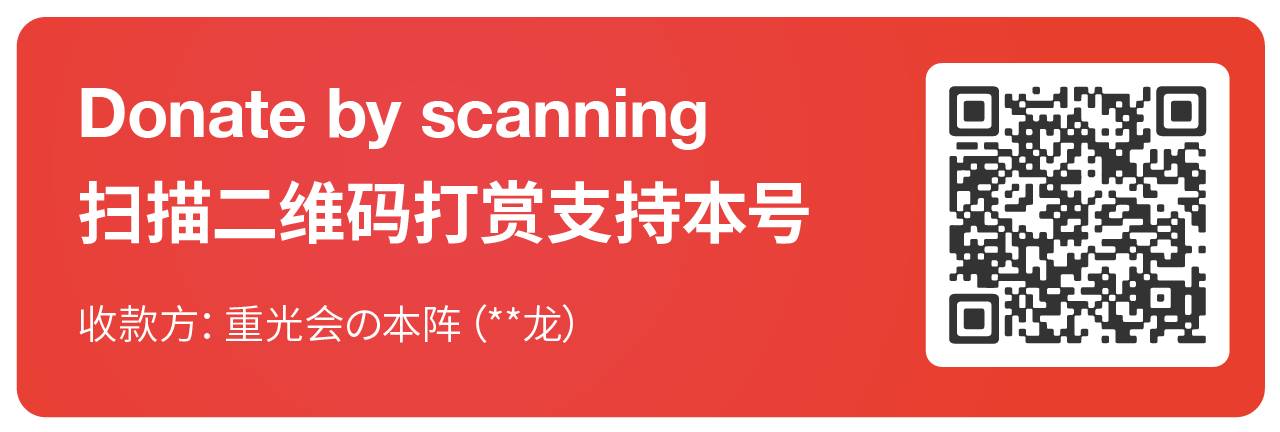

◉
主编
杨澄宇
顾问
傅元峰
编辑
王梓诚、孙欣祺
视觉
应宁
监制
朱绩崧
联系我们
[email protec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