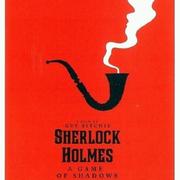正文
说起G市,我对它印象极差。我呆了三年。前三年混进网络公司朝九晚五地上班,每天对着电脑敲敲打打,像没有生命的机械人。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厌倦了那种生活,就像厌倦了要用我的右手解决生理问题。于是我辞职了,老板爽快地批准。
我不急着找工作,先回到家的避风港,成了失业青年。
爸妈知道我没了工作,脸色变成了猪红色。他们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到处托人介绍工作给我。不久后,他们找了关系送我进工地当施工学徒。
他们高兴了好几天。看见他们狡黠的笑容,我清楚地知道笑容背后的含义。
三天后,我告别了爸妈,独身到了工地。工地位于G市郊区。偏僻到连一只鸟都厌恶飞到这里。
我进了工地。走马观花地到处看。工地面积大得如无边际的大海,一眼望去,有十幢楼,每幢有30层。楼设计像男人的阴茎。看着一根根像晨勃一样的阴茎拔地而起,觉得滑稽。
突然有个人挡在我的面前问我找谁,我说找老总,他说他就是。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脸上堆满了油光的笑容叫我进办公室。他大腹便便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企鹅。
翌日的早上,我六点就起床坐在办公室等吩咐,等了一个小时,老总慢吞吞走进办公室,然后给我一顶红色的安全帽,安排我跟着一个师傅放线。
师傅年龄在40岁左右,不到一米六的个子,留着络腮胡子,像艺术家。“走,放线去。”他对着我说。
跟着他几天了,发现他的脾气暴躁,时常操着具有方言味道的普通话骂人,我也未能幸免。
他会说我:“你会不会放线?我弹线的时候,你要按稳,别松开,有没有力气的?你这点力气怎样操女人?”还有很多不堪入耳的粗口。每当我想骂回去,就想起老妈苦口婆心的劝告:“阿狸啊,到了工地要听话,你是去学手艺的,不管别人怎样说你,你都要忍,拿了工资记得请你的师傅吃饭。”云云之类的话。
为了宣泄我的愤怒,我私底下叫他崔逼逼。当然,他姓崔。
这是夏天。南方的夏天。
我们像是干枯的荆棘,站在天面宛如听到噼噼啪啪被烧着的声音。
崔逼逼也会骂天气。边干活边骂:“妈的,鬼天气这么热,干个毛线。”
又是燥热的下午,我跟着崔逼逼上天面放线。十几个人挤在人货梯,就像包子的馅挤压在一起。而旁边的人货梯显得萧条。这台人货梯有个年轻的少妇。她30岁左右,微胖,大胸部,白皙的皮肤。脸上涂抹了一层层的粉底,看起来像是被入殓师化了妆,身上喷着廉价的香水。男人们心照不宣地挤上这台人货梯,目的就是为了看她穿着的低胸装露出深不见底的乳沟。
大热天散发出来的汗臭味被挤碎了,取而代之的是躁动不安的味道。
很多人因此搭过了楼层。
崔逼逼也想看她的胸部。可他比较装。他会偷偷瞄一眼,或者假装转头看上两眼,生怕别人看到他猥琐的样子。巧的是,被我看到了。当时我准备也一览春光景色,无奈狼多肉少,我挤不进去。恰巧看到他懊恼的表情和咽口水,我在心里窃笑。
上到了顶层,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出了人货梯。
崔逼逼突然说下26层放线。我在心里骂了无数句粗口。
下到了26层。地面铺满灰尘、铁管、方木、零食塑料袋,烟头。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我找了个地方把工具放在地上,然后看到一个用过的避孕套。它饱含风霜地躺在地上。想必有些岁月了。我捡起来看,随即往窗外扔了出去。
崔逼逼还在抽烟。我带上胶手套,拧开墨水瓶,拿起墨斗,把墨水倒在墨斗,加点水在墨线上,再倒出来。这是我每天的工作,无趣繁琐。崔逼逼叫我到把要放线的地方扫干净。我嗯了一声,拿起扫把扫地。这时崔逼逼开始骂街了。这也是他每天的工作。
“和你说了多少次,要扫梁底下的地方,你是不是有健忘症?”
我一声不吭。
“你愣着干嘛?还不去扫,需要我动手吗?”
我哦了一声。如垂死前的呜咽。然后走到梁底下扫地。
扫好了地,我们开始放线。崔逼逼拿着卷尺和红色铅笔从控制线开始放线。我屁颠屁颠地跟着他蹲下又站起来,如此反复。忙了两个小时,崔逼逼说休息一下。我如释重负。他放下工具,从陈旧的牛仔裤掏出烟,熟练地点烟,随后吸上一两口,乐开了花。我趁此机会,从崔逼逼的挎包拿出放线图,恭恭敬敬地问他怎样看图纸。他假装没听见,我就提高了音量,他一脸的嫌弃:“你才来多少天?扫地都不会,还学看图纸,你干嘛休息啊,墨斗要加墨了,赶紧去加。”我支支吾吾,像被人掐住喉咙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不再问他问题,机械般地扫地,拉线。他偶尔会和我说话,我像木偶一样沉默不语,时不时点头表示我在听。他无非是在吹嘘自己年少轻狂的杂事,睡过多少女人,身家有几千万。我没有拆穿他,唯有在心里对他嗤之以鼻,这牛皮吹得出神入化,对得起他的姓。
到了下班的时间工人们蜂拥而上挤在人货梯,汗味精力旺盛,在鼻孔流窜。不过谁也没有在意,只要能看到“机婆”的胸,这点味道算什么?我们在背后叫开机的是“机婆。”
下到一楼,看到一辆警车停在办公室门口。我们像鱼群一拥而上围在警察前面,警察把两男一女带走了。我问旁边的共有是怎么一回事,他笑了笑说,砌砖有个小子偷看粉墙佬的老婆洗澡被发现了,刚才他们还打了起来,粉墙佬报了警。你说了,到外面叫个小姐或者看个三级片自己解决不好,非要去偷看别人洗澡,偷看又不能干有毛用,不过粉墙佬老婆的那对胸真他妈大。我呵呵笑,没有回答他。然后大家纷纷散去。这件事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无独有偶。又过了几天。一名30岁上下的女人哭哭啼啼到工地找叫阿南的电工。她和阿南说她老公坐牢回来了,昨晚还大吵一架,然后她就跑出来了。阿南听了脸色大变,像熟透的猪肝。阿南把她赶走,她不依,大骂阿南没良心,说去年睡她的时候又不是这个样子。阿南怕闹大事情,把她拉进了宿舍。
在别人的口中,我知道了他们的事情。那女去年是在这个工地做杂工,就和阿南搞上了。他们还告诉我,说他们不去开房,晚上在宿舍的木板房干那事,呻吟喘气的声音一览无余。住在他们隔壁房间的人一整夜都没睡好。声音耐人寻味,他们的生殖器像升旗杆似的杵在半空中,有的人实在忍耐不住,蹑手蹑脚地贴在木板上聆听久违的声音,脱开裤子手淫。
说到这,他们诡异地笑了,笑声散发出一阵骚味。看得出来他们沉浸在快乐的回忆当中。
阿南的房间传来激烈的吵架声,像是地震。那女破门而出,阿南一路追打她,被几个工友拉开,她跑远了,哭声逐渐消失了。老板知道后,炒掉阿南了,给我们开会说不要传出去。这是后话。
我的生活依旧不堪。每天还是跟着崔逼逼到楼层放线。他还是骂我,但眉宇间多了挥之不去的担忧。我心想他是担忧自己和阿南的下场一样。我只好每天祈祷他东窗事发。
有天晚上,我百无聊赖,接着去逛街。宽敞的柏油路两旁种着芒果树,还有如雕像的路灯木纳地杵在地上扎根至死,散发着油尽灯枯的光。不远处霓虹灯在闪烁,像眼睛进了沙子。车来来往往,简直是在竞赛。有丝丝风出来,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和没来过一样。
我走进一间大排档,坐在嘈杂的人群,隐约听到摊贩在吆喝:“外贸衣服,便宜大甩卖,来看看啊。”我顺眼望去,他用大喇叭说:“赶紧过来挑,挑慢就没了,没有袋子装的啊,直接给钱就可以了,送给亲戚朋友人家也会说是高档货,现在只卖25……”我听不下去了,就开始点菜。我点了一碟水煮花生米,一盘凉拌猪耳,一碟炒米粉和三支啤酒。
他们先把啤酒送上来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回想起这几个月来的学徒生活。
当中的辛酸苦辣,没人理解。大家忙于赚钱,谁也没有空去关心其他人。
想到这里,菜已经上齐了。我从回忆晃过神。
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如果自己有本事也不至于在这里当学徒。这一晚,我心情复杂。
突然,有几滴眼泪掉在盛满啤酒的啤酒杯,波澜不断地扩大,像一朵残败的棣棠。我拿起酒杯仰头大喝,觉得味道特别苦。酒里仿佛参杂了黄连。
东西吃得差不多了,映在眼内的影像是杯盘狼藉。我付完账就回工地。二十分钟后,我靠在宿舍落败的墙上沉默地哭泣。我怀念的,想要的,没人知道。在这个城市找不到我想要的,美好的愿望隐没退去,散得无影无踪。青春在辛辣的生活中昏睡。
翌日。我昏昏沉沉地去上班。然而我听到了关于我的谣言。有人说我昨晚勾搭开人货梯的少妇,说我们昨晚去开房。总之有诸多不堪入耳的谣言,越说越离谱。我以为我是清白的,就不畏惧众说纷纭的谣言。在吃饭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我如坐针毡,饭还没吃完就起身离开,一刻也呆不了。我受不了他们的中伤。
回到了宿舍,我闷头就睡,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告诉同宿舍的工友说我是被清白的。看到他们的假笑,就知道说什么都是徒劳的。工地是谣言的聚集地。工人是勤劳的生产工,专产谣言是非。他们的嘴巴是屎壳郎的娱乐场所。我愈想愈气,恨不得拿玻璃胶封住他们恶毒的嘴巴,让他们终生只会手语。现在我只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一切。
煎熬地度过了一天。我反锁关上门,关掉了手机,安心地睡觉。醒来时已是中午的下班时间。奇怪的是,崔逼逼没有催我上班,或许他叫了我,我却没有听到,管他呢。我欲想去吃饭,出门刚好碰到崔逼逼用那像被火烤过的眼睛瞪我。看到他去芝麻大的眼睛,我差点笑了出来。他问我为什么不上班,我没搭理他,径直走向饭堂。他的脸挂不住了,一把把我推倒。我被他一推,倒在堆满钢管的地上,我连忙爬起来,用力把他推倒在地。于是我们厮打起来,直到被其他人把我们拉开,我们才停了下来。他的眼角被血染红了,像蜿蜒的沟壑的水在蔓延。当然我也没有比他好多少。鼻血把我的胡须涂满了红色。他简单地包扎了眼角。我用纸巾塞住了鼻孔,纸巾很快地换了一种颜色。我气不过,再次冲上去把他推倒。他没敢还手,爬起来拨通了电话。从他日落西山的声音得知,他是给老板打了电话。和老板说了我的罪行。
这次我没有理他。我饭也不吃了就回宿舍。怎样睡也睡不着。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醒了过来,那企鹅一样的老总找到我,黑着脸说我被炒鱿鱼了,赶紧收拾东西滚蛋。我问他,我工资呢。他怒不可遏地说,你还想要工资,不是给你爸妈面子,我就报警了。明天给我赶紧滚。
于是我又回到原点,成了连爸妈都嫌弃的失业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