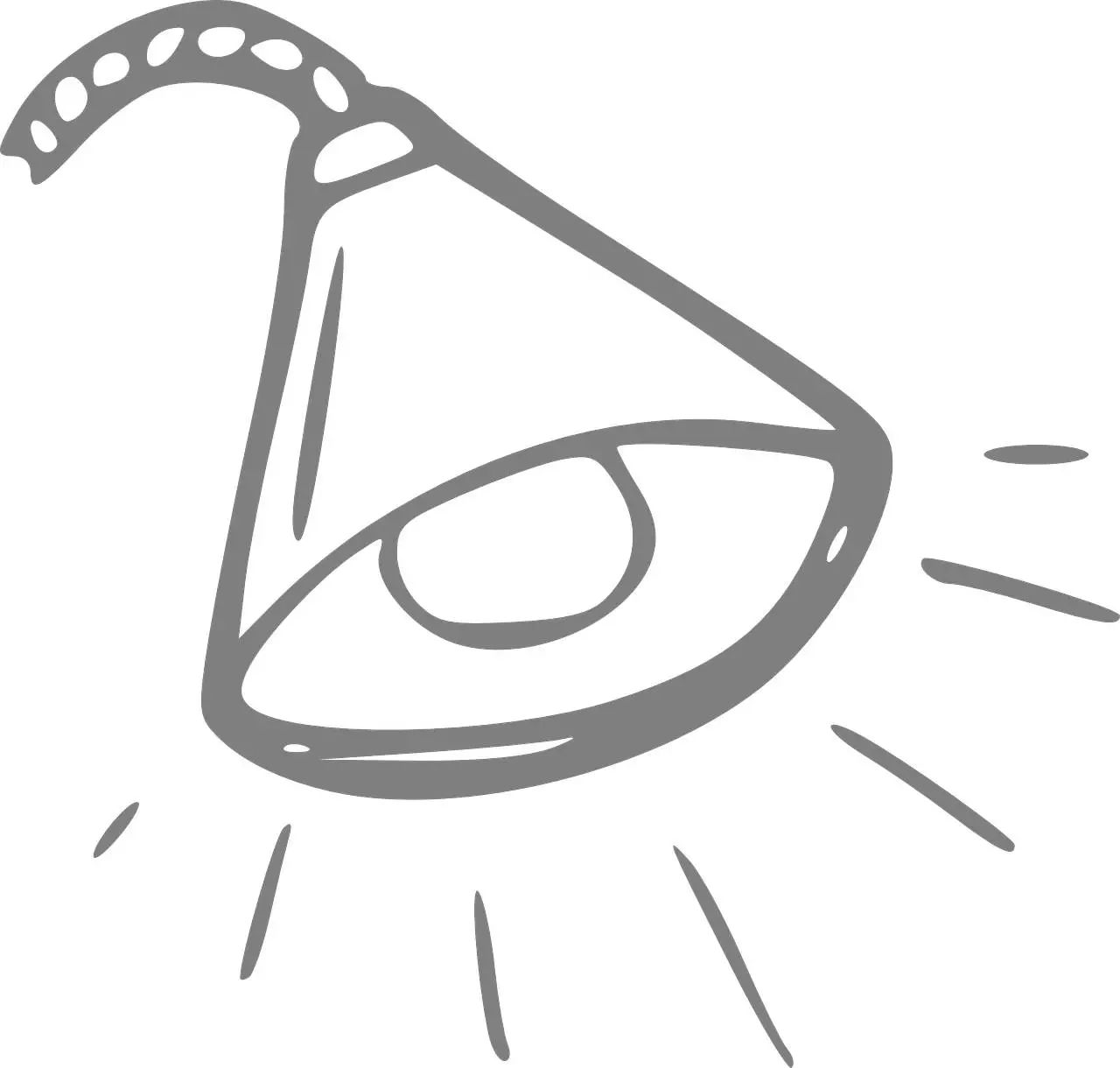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不相衔接,或是经济的条件变更,或是对外关系改观,整个国家社会逼着从基层再造,当中必有一番变乱,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是出于这样的要求。
——《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
老友建议梧桐码一篇狗日的繁荣,意思是说,
就像一个人,咆哮了四十年之后,落得一身的虚华和人文的尽失,由此心灰意冷,几经曲折,步入断舍离的澄明之境,并最终发现,一切都是故事,原来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只是,我们还是从萧条说起吧。
海曼·明斯基(
Hyman Minsky
)认为,为投资进行融资是系统不稳定的来源,而融资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对冲性融资,即债务人的现金流可以覆盖利息和本金;投机性融资,即债务人的现金流只能覆盖利息;旁氏融资,即债务人的现金流什么也覆盖不了,只能靠出售资产或续借新钱履行支付承诺。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信贷的扩张,这是一个长程的信贷扩张时期,融资的基本趋势是从对冲性融资向投机性融资、旁氏融资的方向发展,显然,投机性融资和旁氏融资有赖于信贷环境的宽松和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涨。
然而,一旦这个环境发生变化,融资链条即会断裂,而资产价格螺旋加速下降效应将引起雪崩式的金融动荡。
这个时刻,我们称之为明斯基时刻(
Minsky Moment
)。
用一种具有画面感的表达就是,灰犀牛横冲直撞的时刻,我们已经看到股票资产的崩塌,正在看着债券资产的崩塌,并很可能会看到房地产的价格崩塌。
资产泡沫是一种自然的“庞氏骗局”,只要不断地有傻子(接盘侠)加入进来,人们就会不断赚钱,但是,傻子总是有限的,到了最后自然全盘崩溃。
譬如,当房地产价格膨胀的时候,人们会认为所有与住房有关的东西都是安全的,而当房地产价格泡沫刺穿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所有与住房有关的东西都是不安全的,甚或开始持有负资产,即房屋的价值还不够偿还抵押贷款。这是另一种型态的“挤兑”。
稳定最终是不稳定的,因为稳定会引起资产价格膨胀以及信用过量,我们经历了一个长程的稳定,并将迎来不稳定。
一次次地微调,一次次地成功抑制住,结果是一次算总账。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依靠房地产加杠杆的方式,直接将居民储蓄率拉下马来,苦了百姓,我们可是扯着嗓子喊了很多年的“扩大内需”。
整个系统,就像一头驴,眼前不是胡萝卜,而是一个死结。
药方只有一个,那就是系统的自我革命,但是,显然这似乎得要等到整个系统崩塌之后。
中国的大历史似乎就是这么一个宿命,儒家的故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宿命往往是不到一败涂地,不会反思和修正。而这也就像是一个人,壮怀激烈,气吞万里山河,到了最后连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无敌,由此,失去了自我的进化力和迭代力,以及反脆弱性,看上去是一块钢化玻璃,然而本质还是一块玻璃。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到高峰,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就算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距离,而与苏联亲近。
而到了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在1970s,似乎人类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这就是40-50年前的事情,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讲述无常,而社会主义是一个故事,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故事,自由主义是一个故事,资本主义是一个故事,到最后,一切都是故事。
修昔底德陷阱,既然是陷阱,往往意味着愈落愈深,直至陷阱之底。中美贸易战之贸易战还只是相上的,本质是一场对抗,类似于cold war的对抗,是两个故事的深刻较量,而在目前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上,吸收了社会主义优秀元素的自由资本主义至今仍或是最完善的故事。
回到萧条,由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庞大,以及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加之庞大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反脆弱性,因此,就像一个人一样,系统崩塌的速度不会那么快,这个过程不会一夜之间,而更可能像是在放电影,一个慢镜头。
而至于崩溃之后,是否会重生,似乎也没有那么简单,到了最后,一切都得回到人本身。
我们走在历史的进程之中,我们也在刻画着历史,我们就是历史本身。
过去的四十年是人口红利、互联网红利、全球化红利、政策红利等等的红利共振,是一个各种因缘和合的现象。而现如今,这些红利消逝殆尽。需要思考的是,究竟有没有可能走出混沌,若是没有可能,那我们这些微尘众究竟应该如何安住自己,走过这一次生命的轮回?
有朋友说,可以劫富济贫,然而,劫富济贫虽然显得公平正义,但那只会更加强化人们的不安全感,整个生态系统会变得更加怠惰,从而无法走出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