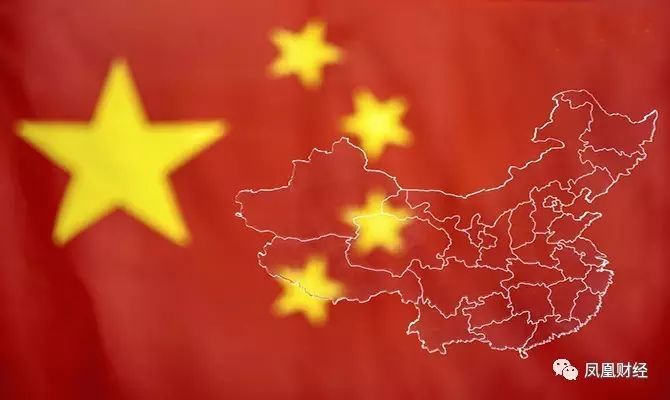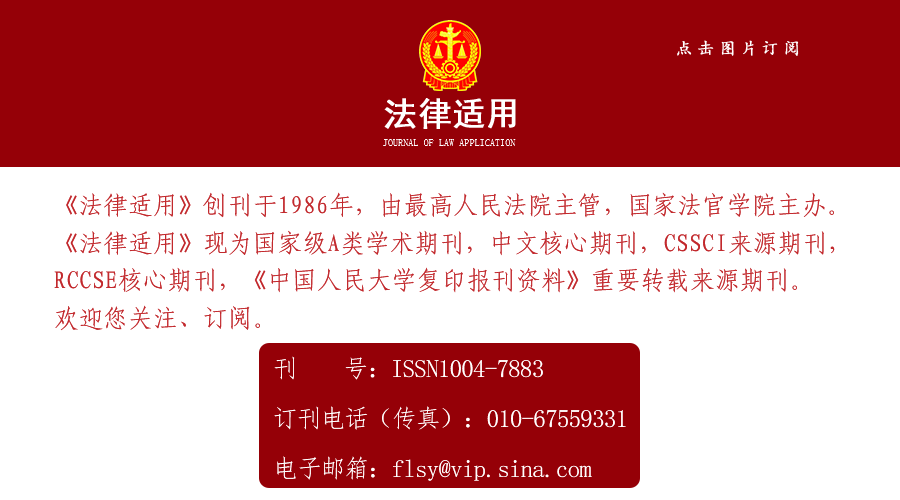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适用》微信公众号在刊发纸质期刊文章外,特开设“实践法学笔谈”栏目,为务实管用的实践法学研究成果提供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
,敬请关注!

谢蕾
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和解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制度。但在行政非诉执行中,由于理念偏差、规范缺失、理论约束、风险考量等因素,执行和解制度存在一定的适用障碍。但笔者认为,行政非诉执行中可以适用执行和解制度,理由如下:
(一)柔性执法理念之融入
现代行政法理念认为,行政权的行使应善意、宽容及合理,应从单方行政转为协商、民主行政。而执行和解制度在行政非诉执行中适用,不仅能通过尊重行政相对人,照顾其实际情况,吸收其合理要求,弱化行政相对人的对抗性,更能通过和解过程中的沟通交流,来弥补部分行政相对人因未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缺失的陈述权、申辩权,增加其对行政行为的接受度。因此,在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适用执行和解制度,是对现代柔性执法理念的契合与回应,有利于建立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彼此配合、信赖、支持的和谐行政关系。
(二)行政执行协议的体系解释
《行政强制法》第42条以“执行协议”的形式,规定了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样态。虽然该条规定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这一章,但从体系解释角度出发,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同属于行政强制执行,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应协调一致,在内容上应相互补充。在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中允许达成执行协议的情况下,若否定行政非诉执行中执行和解制度的适用空间,会造成不同程序中的行政相对人“权利差异”,对行政非诉执行中的行政相对人显失公平。
(三)比例原则对执行方式的选择限制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手段要符合行政目的且造成的侵害性最小,如果有多重同样能达成目的之方法时,应选择对相对人损害最少者。执行和解制度,在设置合适的条件下,能以缓和的方式,让行政相对人自动履行,同样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且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较低,符合比例原则。
(四)行政非诉执行中多方主体的现实需求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执行和解制度让被执行人自动履行,能省却大量程序环节,节约司法资源。对行政机关来说,行政机关通过与行政相对人持续地沟通,能充分宣扬行政政策、价值、理念,行政相对人在长期履行过程中,会对行政决定产生“肌肉记忆”。因此,执行和解更有利于行政行为教育、预防目标实现。对于市场主体来说,能通过执行和解,以时间换空间,缓解执行带来的资金、经营压力,更有可能实现“涅槃重生”。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适用执行和解,除“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这一基本条件外,还应根据行政非诉执行程序的特性,围绕着最大可能实现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的目标,设置合适的条件。
(一)被执行人不具备一次性履行能力,但需具备基本履约能力
所谓一次性履行能力,主要指被执行人有充足的金钱形式的财产能够全额履行义务,比如足额的银行存款。在被执行人有一次性履行能力情况下,不应适用执行和解制度,而应将被执行人金钱形式的财产执行完毕后,再允许进入执行和解程序。否则,不仅会侵害公共利益,更有可能助长行政相对人以执行和解逃避执行的不良风气。
同时,被执行人仍需具备履行和解协议的基础能力。若被执行人已属“执行不能”,即使达成执行和解,也只是“空中楼阁”。因此,在被执行人提出执行和解申请后,行政机关可与执行法院共同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履行能力、经营状况等情况进行考察,评估被执行人所提和解方案的可履行性及风险。若被执行人已不具备履行基础,不应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
(二)被执行人应当提供有效的执行担保
行政非诉执行的执行和解,应要求被执行人提供切实有效的执行担保以保障履行。对于被执行人有固定资产的,可以通过“活封”的方式控制财产。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可以对被执行人开展法治和行政教育,释明不履行和解协议及违反行政法规的后果,为和解协议顺利、完全履行设置多重“保险”。
(一)和解范围原则上与《行政强制法》第42条保持一致
在行政非诉执行过程中,行政机关系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履行职责,而非享有权利,故其仅能在行政裁量权范围内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而该行政裁量权如何确定?笔者认为,仍应与《行政强制法》第42条保持一致,即仅能就履行期限达成分阶段履行协议;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
与此同时,如果被执行人确实无力履行行政决定,即被执行人属于“执行不能”的状态,采用替代性方式有助于实现对公共利益保护的,也应当允许。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情形,当被执行人无力支付因污染环境的行政罚款时,可以通过种植复绿等“以劳代偿”的方式履行义务,弥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保护。当然,此种方式也是一种有益探索,具体细节还需多方论证优化。
(二)执行和解的次数应予以限制
民事执行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主义使得理论上执行和解可以反复达成。即使被执行人因故未能履行和解协议,在恢复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可以再次达成和解协议。而在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从维护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角度出发,若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和解协议,法院恢复执行后,行政机关不应再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
(三)救济路径限于恢复执行原行政决定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赋予和解协议可诉性并由当事人选择救济路径。但对于行政非诉执行的和解协议,若赋予行政机关可诉性,不仅严重降低行政效率,在未厘清此种诉讼性质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出现法律依据不足、理论争议不断、实践操作混乱的局面。而且,在行政非诉执行和解协议范围受限制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另行起诉并不具有现实利益。
(四)和解协议受法院审查和监督
不同于民事执行程序应限制执行法官对当事人和解的参与度,行政非诉执行中,执行法官应适当参与到双方的和解过程中,以体现执行权对行政权的支持和监督。这种适当参与主要体现在执行法院审查和监督两方面。一方面,执行法院要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审查范围主要为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和风险性等。比如,执行法院发现和解协议明显不具有可执行性,被执行人不履行的风险极大,应当告知行政机关并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在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法院还需承担更多的监督义务。若法院发现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未履行和解协议,应当建议行政机关及时恢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