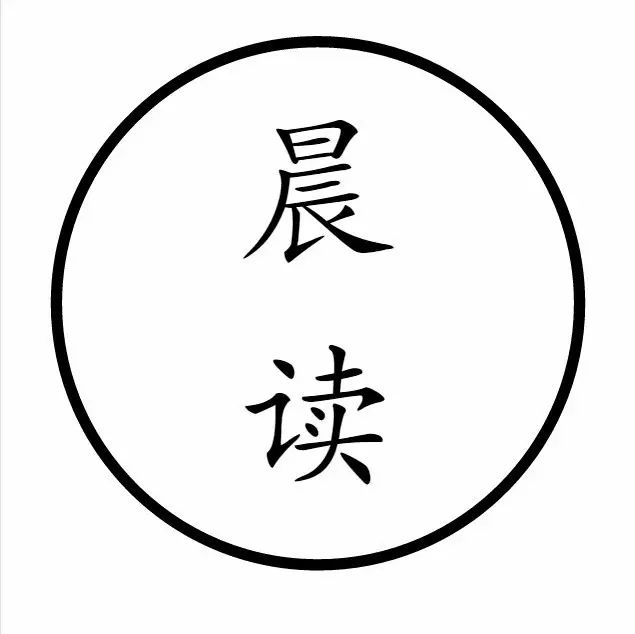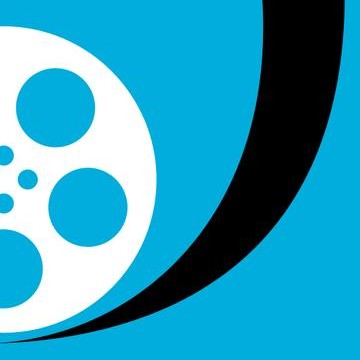穆赫兰道
大卫·林奇,一个让人兴奋又害怕的名字。对影迷来说,他的电影就像一场怪梦,看后既让人心惊胆战、龇牙咧嘴,但又忍不住再点一下播放键。影界甚至以“林奇主义”来总结大卫·林奇鬼魅的超现实风格,足见其风格之怪异与突兀。
近年以来,林奇执导的《穆赫兰道》(2001)一直高居新世纪最佳影片榜单前列,与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难分伯仲。影片本身神秘和暧昧的特质吸引了太多影迷和学者对其进行解读,而对于这部电影到底要表达什么,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称其故弄玄虚者有之,看完大呼过瘾者亦有之,大卫·林奇从不对这些解读和评判做出过多评价,在他看来,任何附加的信息都会使影片本身遭到漠视和亵玩。故此,我们“必须保卫影片本身”,让它“独立自存”。

事实上,《穆赫兰道》也的确是一个完全足以独立自存的自洽体系。在影片中,大卫·林奇故意模糊了梦境和现实的界限,反转了形式与内容的必然吻合(比如将梦境描绘得殊为真实,现实则如梦境一般破碎难解),以此制造出了一种认知困境。

就《穆赫兰道》以及林奇类似的“错乱”影片而言,这种认知困境通常来源于主角的意识的分裂和错乱,所以关于到底谁是真实的人,谁是出现在主人公意识或梦境中的幻象(《妖夜慌踪》里出现了一组男女主角,《穆赫兰道》里出现了一组女主角,《内陆帝国》里光是女主角一个人就有四五个“分身”),我们总是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搞清楚,甚至根本搞不清楚。
不过,正是通过故意的错乱,大卫·林奇探讨并揭示了真实与虚幻之间关系——恰如“寂静俱乐部”里动情假唱却让人感慨涕零的女歌手所喻示的那样——当我们呼唤真实之时,虚假和复制总是相伴而生;而比之转瞬即逝的的美好幻梦,生活中到底充斥着不少无望和残酷。

这里所说的“残酷”恐怕并非修辞,而是一种确定的事物——对大卫·林奇而言,就是好莱坞。从1977年至今,林奇一共创作了十一部长片,其中至少四部都在剧情中明显指涉好莱坞(包括电影产业和特定的影片),尤其是在后期的影片之中,大卫·林奇基本就是把故事设置在此地,甚至直接设置在梦发生的地方,也就是片场。
比如在《穆赫兰道》中,女主角就是前往好莱坞寻求个人发展(让人联想到不久前大热的《爱乐之城》,抑或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根本就是《穆赫兰道》的反面?),未料梦想破灭,最终自杀身亡;片名“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本身就是好莱坞的一条路,是“电影世界与非电影世界的分界”(《大卫林奇的奇异世界》,“梦工厂”),一场追杀和车祸在此地发生。此外,《妖夜慌踪》和《穆赫兰道》中同时出现了非常相似的男性反派角色,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控制好莱坞产业的黑帮老大(一个细节让人难忘:《妖夜慌踪》里的色情片大佬洛伦在盘山道上发怒时,林奇突然改用长焦,将标志性的好莱坞标牌和洛伦并置)……

妖夜慌踪
凡此种种,无疑都是林奇关于权力和控制的反讽:好莱坞控制了一切,梦想、金钱、思想,电影制作的权力,甚至是演员的心理状态,全都在这个体系之中扭曲、变形以至失控;而从个人经历上说,大卫·林奇也的确曾在控制权问题上深受其害,尤其是在其早期作品《沙丘》的制作过程中,林奇本人失去了电影的定剪权,最终使得《沙丘》成为了林奇艺术生涯最低点。
也因此,林奇为《穆赫兰道》选择了法国的制片公司,彻底脱离了这种束缚,其本人对影片的权力史无前例地得到了增强。事实证明,脱缰的林奇的确在影片中将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至少让他的作品离初心更近了一步。

无论如何,《穆赫兰道》的确成为了影史上的一条重要分水岭:它展现了另一种电影文本的可能,拓宽了人们对电影内容的认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大概在《穆赫兰道》之前,影迷获取观影快感的主要源泉是“看懂”,而在它之后,天平开始倾斜,看懂好像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形式的迷离和内容的暧昧让人莫名陷入林奇式漩涡,让你既想远离、又想靠近,既有梳理和解读情节的欲望,又深感理性的局限和潜意识的觉醒——而这种矛盾在大卫·林奇的电影中可谓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