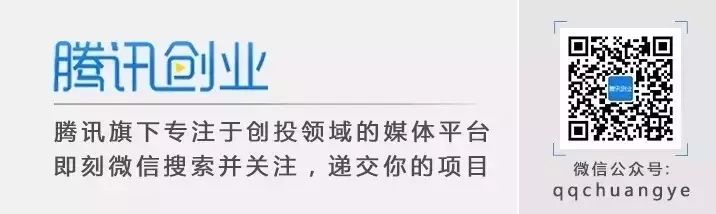拜马云。 视觉中国供图
只有在青年商会这样的角落,还遗留着这些故事的后续——风光地开始,亏完本金还欠了外债的创业者“灰溜溜地”回了大城市。
有人总结,外出打工不是一条出路,却是一条活路。
80后杨子明回乡以前,在温州负责一家文具厂的产品开发和销售工作。农民工出身的他年薪已经到了6位数。可家乡一系列返乡创业的政策让这个年轻人动心。4年前,他辞职带上全部积蓄和家人回到家乡。
他想开一家属于家乡的文具厂。这个个头不高的湖北男人把全部积蓄砸了进去,购置设备,在乡间租下工厂,把房子拿去抵押,再依照政策向政府借款,就能撑过一开始的周转期。
出乎他的意料,银行的贷款批不下来,政府的申请也卡住了,没有借给他救命钱。
创业第一个月,他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差点搭上十多年打拼的全部积蓄。
遣散了全部工人、只留下一个亲人看门,杨子明奔赴浙江,带着订单找到不同的工厂,请求对方生产。
整整半年,他一直待在浙江,刚怀孕的妻子在老家天天跑银行申请贷款。老家的人冷嘲热讽,“工厂突然关门肯定是犯事儿了”。还有人嘀咕,要离这家人远远的,更不能借钱。
“雪中送炭根本不会出现,大家都只愿意锦上添花。”扛过那段困难期的杨子明,如今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三四十个员工,他苦笑着回忆,后来自己日子好过了,借钱的人多了,政府也给了不少支持,银行的贷款更是顺畅。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说,自己刚回来就遇到财政困难,换做谁都不敢贸然借钱。
只是,“在最难的时候真的孤立无援。”那时,他甚至借了高利贷,没日没夜地干,就怕还不上钱。
这种孤立无援于张成而言也不陌生。最初他投资什么产业都赔,妻子和丈母娘发火了,她们希望张成把积蓄存进银行,安安心心找个工作上班度日。听到他还要创业,妻子和他分居了,丈母娘留下一句狠话,“你再这样下去,你俩就离婚。”
“这里不是深圳,你不行的。”“你不要创业了,都失败那么多次了。”张成很清晰地记得这两句“最常听到的话”。
他不服,想要再试一次。
可更多的返乡创业者,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再尝试。
曾有一位返乡创业者想要提升本地人的饮水质量,带来了净水器项目。一开始项目势头良好,围着一圈又一圈儿“朋友”,后来,这个项目遭遇困难,这个年轻人迅速被孤立,“都怕他来借钱”。
这个年轻人孤独离开家乡后,张成给他打电话,想邀请对方来自己的公司上班。电话那头,年轻人沉默了许久,随后苦笑道,“老家这个地方啊,太太太太难搞了。”
电话那头的张成沉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开口劝说了。
他想不通,“很多返乡青年失败了,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带动他们?”他语气急促地说,“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这个年轻的青年商会会长不止一次地说,要是有一个机构能对失败的创业者给点反应就好了,“就给一点点支持、一点点鼓励、一点点温暖,不要躲着他们,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张成觉得,濒临“死亡”的企业也许只需要一笔周转资金,也许只需要一个续命的客户,甚至只需要一个宽松点的舆论环境。
可惜,很多创业者的离去都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远离他们了,甚至不知道企业是什么时候‘死的’。”他说。
这样的一个机构也是胡伟所期待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自己不需要机构给多少钱,不需要给多少资源,“就像你这样,坐在我身边听我说说我这些年的难处就行了。”
他觉得自己像孤军奋战的战士,“办一个证可以只花半天时间,也可以拖你半年。”他清楚地记得,为了几本证件,他往政府部门跑了一两百趟,有时候“腿都快跑断了”,回到宾馆还要马上开始装修。
“想想蛮心酸的。”他说。
张成曾去相关部门办手续,但“工作人员聚在一起讨论买菜,就当没有看见我”。李杰想为公司更名,可被有关部门卡了半个月,一会儿是缺了这个证,一会儿是那个要求不达标,甚至有个女工作人员说:“你咋又来了?”
最后,愤怒压不住了,李杰冲到了领导的办公室,大声喊:“你们不能把我当小孩耍啊!如果她记不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培训完再上岗啊!为什么改个公司名称这么这么难呢?”
李杰如今在武汉创业。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已经挣到了房子和车子,这个90后创业者说,省城的相关机构有绿色通道,很多业务都能一天办完,窗口也都是“素质很高的年轻人”。
他很坚定地说,自己不会再回老家创业了。
张成惋惜李杰的离去。他担心出现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失败者离开,他们会劝说未来打算返乡创业的青年,“别回去,那里不适合创业。”
返乡创业青年越受挫,离开得越多,城市发展也会更慢。张成为此忧心不已。
这个青年商会的年轻会长不想妥协了。他给被赊账困扰的年轻人支招,都少去店铺,收银交给店员,就“公事公办”。他很清楚,外部环境不够好,可正因如此,才需要去努力。“如果连我们都不愿去改变,都去妥协了,这个环境还可能变好吗?”
硬扛着活下来
很多年轻创业者离开时,张成都不知情,那一年多的时间,他的项目也在“水深火热”中。最糟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大不了就重回当年去深圳的光景,一分钱没有而已。
那时候,老家发大水冲了土地,证件不全的他跑到深圳。分文不剩的张成在公园住了两天,饿了两天,他每天去喝公园浇花的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给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给我打点钱吧,我真的要饿死了。”
这一次,虽然不会饿死,但积蓄再经不起折腾了。他看准了儿童摄影领域,准备再试一次。
他想跟医院院方谈合作,免费为新生儿拍一张出生照,孩子几斤几两都写在上面。等孩子大一点儿了,再去家里免费提供洗澡和按摩的服务,并为孩子拍满月照。当时,老家县城的儿童摄影市场竞争激烈,提倡服务意识和品牌意识的张成认准了这个领域,决心要做下去。
可光是进医院的产科就难倒了公司的初创人员。他们被保安轰出来,有时候对方生气了,还把张成他们摁在墙上。后来,张成决定早上6点前就去,晚上10点后再来。
杨子明走过困难期的法则也是硬扛。在浙江的那段日子,他辗转各家工厂完成订单,他担心家乡的妻子,大着肚子还要为他跑贷款。他担心老家的夏天潮湿,工厂的设备会生锈。
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回家。”
有一次,客人要求的生产日期漏打了,产品要得急,但工人手上都排满了活儿。杨子明啥话也没说,一个人去了车间。
每晚工厂下班,他独自站上流水线,打开打码机,把纸盒一个个放进去,再码整齐。20万个纸盒,他一个人干了大半个月。
这个出生于1982年的返乡创业者说,在浙江的那半年,他每晚都留在车间盯着,他怕工人偷懒,更怕自己偷懒让单子被抢走。他“说尽了好话”,终于熬完了这半年,挣到了周转资金,妻子也顺利批下了贷款。
他回家了。
他希望有一天,在中国夜景卫星图上,自己的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
回乡以前,杨子明和温州的大老板告别。对方眼睛红了,“做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要求你说。”
“我不可能打一辈子工的。”杨子明说,“我还是要回家啊。”
创业4年多,他说自己从家乡得到很多支持,新的厂房是有关部门帮他联系的。厂子从村里搬到了城里,离家就3公里。虽然,他根本不会回家,把家安在了厂里。
这个返乡青年很自豪,自己的工厂一年也能为家乡纳税6位数,还可以解决三四十人的就业岗位。他拿出自己设计的品牌和专利,预备慢慢加大生产量。他希望就从这个市郊2000多平方米的工厂开始,诞生文具行业最新最好的品牌。
张成已经拥有了5家摄影店面,如今,他的店面爆满,地暖、衣服罩子、游泳池、专业育婴师、二次消毒的衣服柜等等元素吸引着小城的父母。
可在最初的时候,劝他放弃的人太多了。几乎没人能想到,张成近乎“傻子”般坚持,真的敲开了医院的大门。免费的摄影工作持续了整整9个月,很多消费者怀疑张成是骗子,“哪有这么傻的老板?还免费送东西?”
还有人直接说,“你们干这些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
张成就当没听到这些话,他提倡的上门服务一直没断,最远的一次,他们免费跑了200多公里为消费者的孩子拍了几张满月照。
这一次创业,最大的不同是这个年轻人不再打算妥协了——招聘的条款都按照他在深圳总结的套路,他招聘的大多都是在外地工作返乡的年轻人,“如果能给到差不多的待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周末还能帮着家里干点活儿。”
这些在外面“感受过社会危机感”的年轻人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力,奖金、提成、分红、甚至入股,张成靠这些留住了人才。
免费拍照业务打开了市场,也让这座县城的年轻父母近距离接触到了营销的概念。张成说:“一定要把好的观念坚持下去,你要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出结果。”
这个年轻人始终觉得,小城市想要跟上大城市的脚步,就要靠这些返乡青年的努力,一点点改变行业规则、产业生态,最终一点点改变人们的思想。
“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坚持下去,能被改变、被撬动的产业就会越来越多,最终让一个城市进步。”他有些兴奋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