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拜访过最潦倒贫瘠的土地,也踏足过最富丽堂皇的宫殿,我握过黑人老农布满老茧的手,也搭过老派贵族香粉扑鼻的肩。我曾像无拘无碍的浮萍飘荡过半个星球,听着、看着无数灵魂在我面前熙熙攘攘,有的如演说般慷慨激昂,有的如梦呓般喃喃低语。
有些我听得懂,这些灵魂便为我打开新的一扇大门,为我奉上最稀奇的珍宝;
有些我听不懂,这些灵魂便只能面露遗憾,留下个不明所以的微笑便再无踪迹;
于是每天我都在问自己:语言是什么?而语言背后又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我好像有无数答案,可又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它们就像我数年前那段如梦的旅程,只有梦里人,才懂个中味。
毕竟谁又说得清,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那么我想你该也会好奇,这些蝴蝶,都如何舞动它们的翅膀?下面就请万国学院的教书先生们来给我们说道说道。

几年前我从加勒比海畔回乡探亲时,惊讶地发现西班牙语在国内竟被称为「小语种」。然而这门占据二十个主权国家官方语地位的语言,以五亿母语者的傲人数据紧随汉语雄霸世界语言榜第二名——在西班牙语面前,英语才是真正的小语种。我在美国东海岸生活的数年岁月中,使用西班牙语的频率也几乎与英语持平。英语世界的大本营美利坚合众国,四千多万美国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走在美国大都市的街头,有时候我会陷入一种恍惚——仿佛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拉美。
精通西语者得拉美,得拉美者得美洲,得美洲者得世界。
白宫的政客们在不遗余力地讨好着拉美移民,华尔街大亨们每天都在盯着拉美的风吹草动,常青藤的学者们皓首穷经地钻研为何这片土地能让所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失效。拉美百年沉浮的诸多激辩数载的论证中,只有一条结论是野心家们心照不宣的:西班牙语世界是政商两界的兵家必争之地。
两百多年前,大西班牙帝国余晖已至,哈布斯堡王朝将日不落帝国的荣耀拱手让出,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拉丁美洲荒原。丰饶肥沃的土地,储备惊人的矿藏,美轮美奂的风光,瑰丽奇幻的文明,都无法改变其血管被切开的命运。伊比利亚人带来了战争、天花、种族灭绝、庄园与奴隶制,带走了不计其数的黄金与白银;盎格鲁人带来了民粹主义、贸易剪刀差、毒品交易、游击战与武装干涉,带走了不计其数的石油、初级农产品、人才与债券;如今,华商们蠢蠢欲动的身影开始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这片土地的各个角落——我们究竟要继续在这苦难的土地上如同之前的宗主国们一样狠狠地咬下一块肉大块朵颐,还是要以人类共同体中所共有的灾难记忆使得这个美丽的角落与我们共存共赢?
寻找到这些复杂问题的答案,永远都需要迈出最基础的一步:学会西班牙语。可西班牙语难么?难也不难。不难是因为其优雅的语法与简洁的逻辑,只需要不到二十周便能融会贯通;难是因为,她承载了太多超越语言的魔幻与现实,二十年也未必初探门径。然而,不难而又能带来好运的事情会有多大概率轮得到我们的头上呢?
你若敢于知道,我便敢于带你驶向那片魔幻现实的荒原。船上见。
船长 葛旭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法语都是一门简单的语言。我们将用 20 周的时间学会她。词汇方面,英语和法语经历了几千年的相爱相杀,在词汇层面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神奇特征。在最常见的 7000 个法语词里,有大概 5000 多个和英语「形近义同」,也就是说,不用记也认识,比如法语的「艺术」就叫 art ,「革命」就叫 révolution ,「发展」就叫 développement 。如果仅以阅读为目的,初学者只要记住无法「望英猜义」的词,便可在「词汇」上「攻克」法语。我们统计了一下,需要记忆的,只有 1453 个——而这些词,记 1 个,少 1 个。语法方面,法语大部分规则都可以和英文做类比。不能类比的,只有一个知识点会对法语阅读造成障碍,即:法语中动词的宾语如果是名词,要放在动词后,如果是代词,则要放在动词前。比如法语讲「我爱中国」的词序就是「我( Je )爱( aime )中国( la Chine )」,而「我爱你」的词序却是「我( Je )你( te )爱( aime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 20 周的学习,使不太勤奋的学员具备法语中级阅读能力,使勤奋的学员具备法语高级阅读能力和初级视听说能力。

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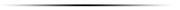
在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之前,世上并没有规范的「德意志语言」这个玩意儿,而在此之后,麻烦也跟着来了。终于跻身世界语言之列的德语,成为多少语言学习者痛苦的根源——也许是名词毫无道理的词性,也许是动词的十八个变位,也许是听上去咬牙切齿的发音。毕竟,能够让马克·吐温专门贡献数千字长文来吐槽的一门语言,必定不是凡品。 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 一文写于 1880 年,此时正值他学习德语第九个礼拜——而孤阅的课程数据告诉我们,第九周听课的人到第十周起码跑了三分之一。所以,在面对德语的时候,一代文豪也泯然众人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头拜倒在德国十八世纪以来所构建的神坛前。想想歌德、席勒、海涅!想想康德、谢林、尼采!想想马克思、俾斯麦、韦伯——这份名单起码还可以再扩充两百字——用他们的语言阅读,用他们的语言书写,甚至思考(如果你足够努力或者活得足够长的话)!尽管德语作为学术语言已渐渐失去曾经盛极一时的存在感(还不是因为它难⋯⋯当然也因为人越来越懒),然而有趣而无用,不正是我们自由选择的初衷么?记得本科系主任是德国当代文坛教主马丁· 瓦尔泽的铁粉,多次盛赞称他为越老越红的辣椒。当初在翻译课上被虐得死去活来,现在回头看,似乎德语也是如此,一开始呛得人涕泪横流,之后再咂摸,却是够劲儿。有一句几乎说滥了的俏皮话:德语很烦人,学会了就不是凡人——我保证,在德语的浸淫下,很快你将到达彼岸,看到 die(阴性名词的定冠词)再也不会浑身一哆嗦了。或者,马克·吐温其实也给德语指了一条出路:它应该像拉丁文一样死掉!他老人家若是有幸看到我们的教材 German for Reading 一定会老怀大慰——没错,我们将要把德语当作一门死语言去学习,专注精神攻克那些古老而神圣的文本。至于学会说话——谁在乎呢?当然,有意进军拉丁文或者古希腊语的有志之士,还得洗干净脖子等着。在进阶之路上,德语只是垫脚石,而绝不是绊脚石。
罗倩

拉丁文与希腊文同为影响欧美学术与宗教最深的语言,而以拉丁文绵延时期最长。从罗马文明的兴起,到基督教在欧洲滥觞 ,拉丁文的影响力一步步加深。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拉丁文是欧洲不同国家交流的媒介语,也是研究科学、哲学和神学所必需的语言。直到近代,通晓拉丁文也都是研究任何科学教育的前提条件。拉丁文不仅是天主教的礼仪语言和公用语,而且是许多历史上学者、作家、哲人的主要写作语言:哥白尼、笛卡尔、牛顿、高斯、斯宾诺莎……
拉丁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对汉语施加过影响。由于英语中有 50% 到 80% 的单词来自拉丁文(越是学术性的文献,其拉丁文成分越高),许多拉丁文词通过英语进入了汉语。如汉语「卡」(英语:card )来自拉丁文的 charta (最早来自希腊文)。公共汽车的音译「巴士」(英语:bus )来自于 omnibus (即拉丁文:「给一切人的」、「公用的」)。其实拉丁文自万历年间来华,交流历史虽长久,但可惜国人正式开始拉丁文的学习,是在晚清民国时期,并且多半学习是为了应付入读英美大学的语言资格考试,并不当真。例如 1902 年时,马相伯就曾对决心学习拉丁文的蔡元培说:「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 ;基督教背景出身的马相伯尚且如此,广大中国留学生更不待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个小课题:梁实秋为什么不在哈佛读硕士了?)。
虽然拉丁文今日在任何领域都不再是必需,拉丁文仍然是通向大多数人文学科和学科历史的必由之路。广大的语言学习者,或者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同学,如果没有学习拉丁文,隔空谈物,总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希望万国学院全新升级的课程能在半年内带大家遍历拉丁文的基础语法和词汇,管窥这一人类历史上承载着最多文化内容(或许没有之一)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