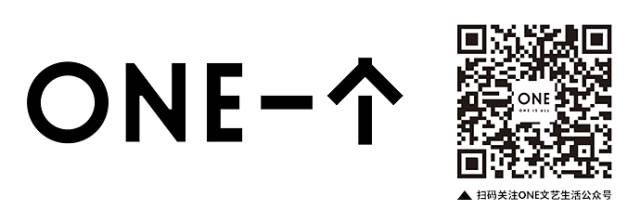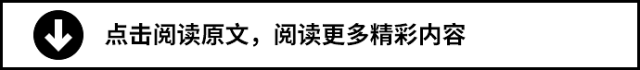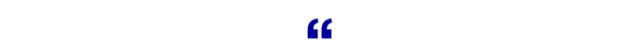
成为妻子的人拥有最无上的智慧,是最会察言观色的幻想家,那种趋近真相的想象力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


我们是两个文静的女孩,船身猛烈的颠簸和失重飞翔的感觉,让我们有种失语感。快艇正在飞越暹罗湾一处不知名的海域。二月中旬,还是暹罗湾最佳旅游季,再过半月潮湿的西南风一来,整个半岛就会进入漫长的雨季。我们要去的岛屿漂浮在海湾的南端,隶属于泰国春武里府,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趁了越南战争的便利,被开发成黄金度假海岸。望着原生的小岛和礁石,张晴和我,一种不符合东南亚气质的沉静,我知道她内心也在感赞,海水的蔚蓝和这种搅浑一切历史又将它们压入海底的力量。她的青色丝巾被海风吹开,一半压在救生衣里,一半飘在船舷外。
挨近张晴坐着的中年妇女将身体紧蜷,双手捂住耳朵,好像晕船是听觉引起的。除了我们,船头还有另外四个人,视野是绝佳的,没有人像电影里那样张开双臂,或者朝奔涌的海水呐喊。但愿阿尔戈号从未飞过深蓝的撞岩——我在心里喊了一声(古希腊戏剧《美狄亚》开篇词)。上船之前,我们为大巴靠窗的座位争论了一番,张晴认为她一直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进去前需要跟她说一声。而我认为不需要。我们保持沉默到现在。另一艘船从后面驶来,比我们的船小一些,显得更轻快。它驶过我们时,我仔细观察了船上几个人的脸,肃静,光秃的树枝,凝固的旱地,迟疑,似乎大家都被大场景撼住了。我亦带着大陆深处的干渴,这种干燥症在体内运行,眼底生涩,和这水天一比照,面庞越显得枯黄。当我们看到目的地的椭圆轮廓时,太阳正要没入海平面,光很温柔。
我们在两天前开始留意那个戴平顶帽的女人,因为张晴听到带队和导游的几句谈话。我们这个团,算上中国带队和泰国导游在内共三十三人,基本都是家庭出游,导游就按家庭为单位编了号码,只剩我们和那个女人,导游将我们三人编制为“五号家庭”。
事实上,我们和她从未交谈过,她时常戴着平顶帽和耳机,胳膊交叉放在腹部,那是拒人于千里的身体语言。张晴留意到她,因为她身上有一股酷劲儿,她说那个女人从不穿向热带献媚的花裙,也没有出行的慵懒,皮肤不白,衣服都是饱和度极低的颜色,基础款式在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我没有注意这些,我第一次留意到她是在曼谷的佛寺外。她和我一样不拜佛,或者说只有我们两个人能确定自己不信佛教。张晴不太一样,虽然她不像其他人一样请香、祈愿,但我看得出她的敬畏和虔诚,她望着佛像的眼神里仿佛有双手正在缓缓合十,瞳孔像被湄南河的清水洗过,有萤光。我知道这个时候她是不想被打扰的,我很知趣地站在寺庙外等着张晴和进香的众人。几次我都看到了那个戴平顶帽的女人,她和我一样在寺外朝四处张望,但她没有要和我交接眼神的意思。我曾几次朝她望去,她感受到了我的目光,便随意盯往一处,稳稳地,有时是寺顶的金色三角,有时候是脚底下正踩着的一块小石子。这个保有神秘感的女人此时正坐在船舱中间,用一条缀着灰色大象图案的纱笼裹着头发和帽子,她的胳膊放在船舷上,身体半匍匐,随着船体起伏。
“要不是亲眼看到国民穿黑衣去吊唁”,我说,“我真不会相信这份爱会如此深沉。”
“不同的背景,总是难以想象对方。”我们回味在大皇宫见到的场景。
“还挺讽刺的。国人穿黑衣去大皇宫凭吊他们伟大的君主,而外来的游客穿红着绿,欢喜地去点评建筑和拍照。”
“人类的悲喜从来就不相通,”张晴说,“做不到互相理解,更别说感同身受了。”
我们望着落日聊起天来。“他们对婚姻和性的观念很不同,把性看得轻松,婚姻的庄严性似乎一点没受影响。”
“一面发展色情市场,一面赞扬忠贞和专一,有些矛盾。”
泰国导游和我们年龄相仿,叫作小菁,她说自己是战争移民的第三代,清迈的家就是国王当年恩赐的土地。她的言语间总透出对已逝的拉玛九世的爱戴,行车期间给我们展示了许多照片。她笃信佛教,将带游客拜佛也看成一种功德。虽然年纪轻,但做导游已经多年,眉眼之间,俏皮和老成共存。事情变得有些不同,就是因为张晴听到了她和中国带队的聊天。昨天从热带水果园出来时,我去洗手,张晴先上了车,她坐在最后一排,过了一会,带队和导游也上了车。小菁对中国带队说,你们中国人观念也很开放嘛,这个团就有人带着妻子和情人一起。随后有游客上车,他们立即中止了谈话。张晴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们很快滤掉几组大家庭,剩下的人里可以按进这三个角色里的人就一目了然了。
我和张晴约好傍晚去散步。我们住的酒店坐落在海滩边上,靠海的一侧是一排椰子树。让这个岛出名的,除了阳光和沙滩,就是繁荣的色情行业。传言中的黑珍珠和椰子鬼突然站在眼前,我们都有些紧张,每次路过椰子树下站着的女人,不自觉地都会加快步伐。“我们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说完我们俩都笑了。我们牵手在海滩和椰树中间的沙地上奔跑,像两颗飞跃的露珠,我的纱质防晒衫在风中轻轻飘起,和张晴的长发一起。月光清冽,海面反着光,一波一漾。酥酥的。外部世界和内心都是这个感觉。我们走累了,捧着椰子坐在石台子上,又看到了那个戴平顶帽的女人。我和张晴几乎同时看到了她,又同时收回了眼神。
“晚上了,还戴着帽子,”我说,“低调的人,还有这样低调的审美,真难想象她会是别人的情人。”
“我说完你不要立刻转头哦,在我三点钟方向的太阳椅上坐着那对夫妻,你慢慢转头,别太显露。”
在前面的躺椅上果然看到了那对夫妻。两个人坐在椅子上,头顶悬着一颗节能灯,发出淡白色的光。戴平顶帽的女人在我们左边,在海浪的最外沿走来走去,从不越过我们,也不会朝另一个方向走太远。“她的身材其实很好,腰很细,腿也长,换身衣服肯定惊艳。”我们一边喝椰汁,一边观察。“人生真富戏剧性。这短短二三十米距离,”我望着那个女人的背影,“三个心事重重的人,三颗星星,得不到、曾拥有和不知所措。”
“你觉得妓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吗?先抛开国内那种固性思维,”张晴说,“一个人决定用自己的身体赚钱,这如果完全出于自觉,又有什么可诟病的呢?”她不时转身观察那些椰子树下的明艳女人。
“对社会而言,应该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吧。你想,如果你的丈夫或者男朋友——”,张晴打断了我,“为什么人人都喜欢在讨论问题时代入自己。先不要去代入,不给妓女留活路就一定稳定了吗?”我没有改变观点,只是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对答。“用自己的身体赚钱,又不伤害他人。人们总持有偏见,在工地出卖力气挣钱的女人就比出卖身体赚钱的女人高尚?我不这么觉得。”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但此时张晴保持掌控权,我沉默了一会。张晴继续说,“我们缺乏性教育,就把它看成是天大的事,如果还守着‘灭人欲’那一套,那过去这一百年还真是没有意义。”
“一百年而已,滚滚历史中的一个浮沫,只是开端的开端。我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我说,“我们以前总是轻视这些东南亚国家,如今看来,真是傻得彻底。”我刚说完,张晴用食指戳我的胳膊,“回头看一下。”我们身后的椰子树下,一个欧洲面孔的白人正在和树下的女人交谈,“他们在谈价格吧”,那个高鼻梁的男人年纪不大,谈吐举止也十分绅士,“这么帅的人,真的是没天理”,他们大约是谈好了价格,白人拉着女人的胳膊离开了。“好想有个艳遇啊!”她喊了一声。我和张晴站起来朝大海的方向走去,“真正遇上了,你又怂了,不知道你。”“也是的,哎呀。”
我们从戴平顶帽的女人身边走过,她坐在一摞救生圈旁,面前有几个人泡在填满月色的海浪中,她就盯着那些人,黑黢黢的像浮冰。
“你究竟信不信佛?”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一种单纯的敬畏,可能因为我没有信仰。”
我觉得张晴站在佛像前的样子非常美,但我没有告诉她。我们不再聊天,去路边的水果摊买了小菠萝和山竹,盘腿坐在地上吃了起来。我和张晴是研究生同学,生活态度很不同,但引力总能大过分歧,有时候为一个问题能争论到冷战三天,而那个问题只是开端于说一个人“读过书就不会这样了”是不是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傲慢。我们都很警惕、自省,而且引以为豪。我们商量着去秀场看成人秀,票价很高,有些犹豫,“去看吧,别处也看不到。”“嗯,去。研究下当地文化,做个田野调查。”我说完,张晴推我一把,把最后半颗山竹果肉塞进我的嘴里,“有病吧,吃药。”
夜色里,度假天堂又变回了小渔村。乡村小路上一排不高不低的树,树影婆娑的缝隙间露出有涂鸦的木船,鱼干,浆洗的布衫。每走几步就有一个便利店,我和张晴买了零食和一种小瓶装的红葡萄酒,有个好听的名字,FULL MOON,满月。回酒店的路上,我们又看到了那个女人,她正从相反的方向走来。街上没有别的人。平顶帽,耳机,牛仔短裤和雪纺纱短袖,V形领口让她看上去轻盈了许多。深眼窝,高颧骨,鼻头很尖。
“南方人。”我说。
“爱马仕屋顶花园。”张晴说。
我们几乎同时开口。 “我喜欢这个味儿,” 张晴说,“以我闻香识女人的经验,这一定不是一个庸俗的情人。”她的声音在长街回环,她不停在讲述香水品牌和女人性格之间的某种隐秘关联,不知为何,这时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街的尽头有些阴郁,几只不知名的黑鸟朝树的一边俯冲下去。“不如我们来猜测一下,或者描述一下他们的关系。”我打断张晴。
“他是一个手捧鲜花无数次出现的男人,栀子花,红玫瑰,鸢尾,或者其它什么代表情欲的花,无所谓,女人们喜欢花,更喜欢怀抱鲜花的男人们。她有自己的生活,一份足够体面的工作,原本可以找一个只属于他的男人,但她却沦陷在他的若即若离里。多少次出现就有多少次离开。”我们上了台阶,坐在酒店大厅外的沙发上,栏杆下是露天泳池,张晴递给我一小瓶葡萄酒。“就是有这样聪明的蠢女人,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想要的又是得不到的。她大约是知道他和太太出游,心生嫉妒,于是就要求报同一个旅行团。她劝慰他不要有压力,她不会有任何出格的举动,所以你看,她的一切都那么低调,她的五官明明是那么的迷人,她不想让人注意到她而已。”
叮,玻璃瓶碰在一起时我们没有对视,盯着对面平静的海,红色液体表层小气泡爆裂时发出簌簌的声响。“深眼窝,高颧骨,应该是个南方人,广州人?福建人?南方比北方开放。这简直是自我折磨,只能远远地看着爱的人和他名正言顺的妻子出双入对。真的难以想象呢。”
那个女人出现在街道拐角处,朝酒店走来,她上了台阶,将手提袋放在沙发上,进了更衣室,再走出来时,是一身亮黄色的比基尼。我和张晴完全被她吸引了,她的好身材胜过旅行团里任何女人,包括张晴在内,我觉得张晴的身材已经足够好。
她先用脚尖试了试水温,然后慢慢地走进了泳池,水立刻将她湮没。像一只入水的白蜻蜓,她游泳的姿势像在飞翔,双手划过夜空,池中是一轮满月,月太满,太亮,看不到星光,水面只有黑和白两种颜色,缠绕着,荡漾着。再远一些,停着我们白天乘坐的大巴,大巴上是几道电线,电线上零散落了几只鸟,一动不动。“我也觉得她是只图爱情的女人,”张晴说,“这类女人最盲目了。”我们重新陷入沉默。两瓶酒都见底了,她还在泳池内往返,像一只海豚或者水精灵。
我们离开天台时发现那个男人不知何时坐在内厅的木椅上,一个人,正在用手撑着下巴抽烟,那个角度刚好可以看到玻璃外的整个泳池。可能是大厅的灯过于昏黄,我觉得他散发出一种弱者的失败气息,像他前方的弥散的烟圈。张晴看了我一眼。我们进了电梯,张晴说,“或许他妻子正站在落地窗前朝下看呢。”
酒店供应的早餐不错,黄油非常浓郁。第一天出海,大家吃早餐时就显出不同,打破矜持和沉闷,在互相赞美衣着。那对夫妻下楼比较晚,太太穿着一件细吊带裙,缀满了芭蕉叶,这位太太也是有风情的,一种圆融的气质,服务生给她拉出椅子时,她说了声,谢谢。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观察其他游客,他们会不会和我们一样假装不知情。总之,世上只要有人,就无所谓秘密的。
“女人就是放弃得太多。”张晴转身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张晴穿着米字旗图案的泳衣,罩一件针织衫,身体灵巧,像一只鹿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八点半大巴准时出发。“岛上有人蠢得可爱,你看,这一大片椰树林,寸土寸金的度假区,竟有人还在种树。”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着窗外一片片的椰树,海风将叶子吹动,里里外外都是海盐的气息。
车辆在缓慢行驶,人们的情绪有些古怪,所有的谈话都与婚姻家庭有关,导游小菁开着带有性暗示的玩笑,人们笑得很保守,尤其是男游客,格外的拘谨。“一场荷尔蒙萦绕始终的旅行。”我们坐在倒数第四排,戴平顶帽的女人坐在最后一排,压低帽檐,似乎睡着了。
张晴摘下耳机,“她有一个软绵舒适的沙发,读茨威格的小说直到午夜。她用玻璃杯喝水,杜绝任何有颜色的液体。”她试图把故事讲得可信一些。“她喜欢听钟表秒针走过的声音,喜欢计数,数到一百会重新开始。她被剥夺了自我命名、失控、预测未来的权利,她不喜欢大厅或者影院那种空旷的地方。她想要自己被城市遗忘,有一天睡醒,她觉得没什么可以再反省,决定打包行李去北方,任何一个有咖啡馆的城市。她不会要孩子。羞愧和辩护一直在碰撞。养一株生长飞快的藤蔓植物,每天给它浇水。有一天她突然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男人,或者任何鲜花和有香味儿的谎话。对!她很有可能是那个人的前女友?前妻?有过亲密关系后分离,再相遇,这个桥段比较适合她那高难度的隐忍。或许她才是那个先到的人,她的愧疚和爱成正比。没有谁可以说服她过上更体面的感情生活。”
“她会梦到一个池塘,一个住所,托命于水。一个完完全全的女人。”
张晴的声音很低,声音柔软得像腰肢,眼神里全是理想。我望着她笑了。“这不好笑,孤独的人都是这样的,喜欢走楼梯只是因为走楼梯慢一些。”
“我们把一切想得真美好。”
“我们就是两个美好的人啊。”
我们在沙滩上分开了,我要去海滩晒太阳,而张晴只想坐在凉亭下用眼睛看。我不理解她,她也不需要我理解。我独自去玩降落伞时又碰上了那个女人,不一样的是,身边坐着那个“丈夫”。快艇将八个人送往海的中央,然后逐一放飞。他们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两人没有交流,也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和别人一样,他们挨得很近,她的帽子放在船员那里,我终于看到了她的相貌。海风很大,她的长发被风吹起,刷在那个男人的脸和脖子上,他没有动手去掀开。他一定拼命地通过这种外在抚摸去感受她、连接她。
同船的是另一个团的中国人,四个非常活泼的女生还有其中一个女生的母亲,他们高声谈论着拍照和落水瞬间的感受。我对拍照没有热情,只是想感受一下飞翔在海面上空的感觉。很快轮到了那个女人,船员给她穿救生衣裤时,那个男人站起来帮忙,并且将她身上的锁链扣子一一检查了。仍旧没有对话。他把她的头发从救生衣内抽出来,散在外面。他的手指是修长的。有两个女生看着他们,大约以为他们是一对冷战中的夫妻。
我将双手持平在风中,没被固定的身体部位只有脑袋、胳膊和小腿,我尽可能地晃动这些部位,觉得自己像一只牵线风筝。一叶没人注视的筏子。戈壁上快速掠过的黑鸟。一只空碗。回岸时我刻意坐在船的最外沿,谁也不看,只盯着海水。或许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独处时间,因为他太太恐高或其它什么原因。
当我再回到沙滩时,远远看到蜷在凳子上的张晴,面前的桌上放着啤酒和几个小菜,她旁边坐着我们团的领队和另一个男人。前面一个给女儿抹防晒霜的高鼻梁女人,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在女儿背上涂抹。下午两点半,阳光正烈,沙滩上的人们已经退回了各种露台遮棚,海风将垂下的遮阳布吹得飒飒作响。回旋着海浪的冲刷声,世界格外安静。有一对高个子的男女用极慢的速度在走,男士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像是梦中的场景,是城市正在教我们遗忘的。一种有些愚蠢的感动,慢悠悠的和谐,这里不再有最重要的东西,口头的契约就很足够。
“我很文静吗?”张晴问我,“看来我的外表很有欺骗性。”
“没什么,人把真实的自己都藏得深。说来,我对你的了解也是局限的。”
我们租了一个遮阳篷,并排坐着,一直到晚餐时间。我们进去得最晚,靠窗的那一桌还有两个位子,我们坐下后才发现旁边坐着那对夫妻。我们对视一下,刻意将注意力转移到眼前的菜品上,一种长在海里的青菜。我不由得有些拘谨,好像我的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一掌之隔的妻子,可能她也正从我们的表情中判断着事态。她用开水烫了两人的餐盘,她给他盛米饭,汤,茶水,完成这些后她向服务员要来方糖,往自己的茶杯中加了两块。她慢条斯理,面部很放松,任何人只要和她目光交接她都回以微笑。我和张晴怀揣秘密,小心翼翼,像两个偷摘果子的人。
“你猜他妻子知道这一切吗?”我和张晴躺在酒店的床上,窗帘没有拉开,夕照和不知名的鸟将窗台装扮,一切都是暖洋洋的。“她其实早早就洞悉这一切,她的不动声色,让她成为一个牵风筝线的人。”我说着,想到了玩降落伞时的感觉。“她的线有长长一轱辘,她自己清楚手里的线还长着呢。你看那些树,展示给人的是绿叶和果实,但它们的灵魂确实在枯枝里,是被遮蔽的那部分。她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是离不了她的。或许她的隐忍是为了自己的骄傲,他不需要我的帮助,他只是想让我认可他犯错误。她已纵身跃进比婚姻更深的地方。她从他的领口、指尖、发梢、眼角,她从他的脚步声、呼吸频率、叹息和佯装,这一些都在明明白白地讲述事情原委。成为妻子的人拥有最无上的智慧,是最会察言观色的幻想家,那种趋近真相的想象力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她或许明白,一段关系中,最牢不可摧的在场往往是缺席。平顶帽女人的风筝线在他手中,他的风筝线攥在她手中,她在掌控一切,放飞的总会落地。”张晴没有说话,她盯着窗外栏杆上的鸟儿出神。“一个聪明女人保持缄默时比急躁时更难以防范——美狄亚为剧烈欲望所俘虏,理智试图将肆虐之火降服。”
“她喜欢的花一定是百合或者郁金香!”张晴补充了一句。
我们突然心怀敬意,张晴和我,为一种扑面而来的神圣感和窥破婚姻规则和技巧而失落。良久,张晴突然站起来,立在软绵的床上有些晃悠。“太有感觉了!帮我把阳台的门全打开,我要朗诵!”她从背包中拿出Kindle,对着室外,酒店靠外侧是一面玻璃墙,拉开玻璃门后,我们的居处像一个迎风的洞穴。外面是连片的椰子林,几户小院点缀其中。
“但愿阿尔戈号从未飞过深蓝的撞岩,航海来到科尔克斯的海岸,但愿佩里昂山里的松树,从未被砍来供那些佩里阿斯去取金羊毛的勇士制造船桨。要是这样,我的女主人美狄亚,便不会因为狂热地爱上伊阿宋,航海来到伊奥尔科斯的城楼下了——”
破裂。援引誓言。订下新律条。火把。分娩。我听着张晴的诵读,这五个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风把一片叶子吹进屋内。读完,她将Kindle扔在床头,像游泳入水一样躺了下去。“其实我也想在夜里站在椰子树下,看有没男人会来找我,如果有人牵我的胳膊带我走,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好的赞美。这种想法是不是贱,可我会为此兴奋好久,真是太可悲了。”
“我不是这样,我要得他们的仰慕,先展示气度,再展示石榴裙。”我想了想,说道。
“这就是妻性吧,但我只想是个纯粹的女人。我无法想象结婚、生小孩。”
“你觉得他妻子和情人哪个好过一点?”
“都不好过吧,如果她们都图爱情。”
“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幻影,‘如露亦如电’。”
“可能它珍贵就在于明知道是一场空还要去追求,亲证这场破灭。破碎的美总让人无法自拔。”
“如果戴平顶帽的女人是贪图他的钱或者房子之类的财产,那这一切都毁坏了。”
“我们这次旅行真的太戏剧性了。”
“像一场冒险。不然也太没意义了。”我刚说完,张晴一个大跨步跳到我的床上,我很自然地把手掌放到她的胸上,“石韵,你这个流氓。”我们纠作一团,互相挠痒痒,感觉像是童年里的嬉戏,女孩儿间稚嫩的把戏。我们大声地笑着,窗台外的几只鸟被惊到,扑闪着羽翅往更高处盘旋着。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张晴突然大声喊叫了起来。我们彼此牵制着双手,笑得面庞通红。“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她有些艰难地吞咽了一下,“要是有人问起,她肯定会这样回答,我敢肯定。”夕阳的光褪尽,我将阳台的的门合上。张晴还仰躺在床上,“我一无所长,但感情上是属灵的。”
行程的最后一站,免税购物中心。我们和那个被多次想象的女人相遇了三次,她买了一只包,两支口红和一款男士墨镜。帽子下的脸上是一种灰烬般的平静,其实她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张晴觉得如果我们主动打招呼,说不定还能交谈一番,她想要印证。我觉得不需要,求证会破坏掉这一切。“我们的好奇出自我们自己的生活而已。”
她没有被我说服,她拉着我的胳膊,和那个女人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她想找个恰当的机会。“这太荒唐了。”我说,“明天就回归各自生活,是不同的平面,哪里还会有交集”。张晴的心已经跑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她执迷地要去探寻一种隐秘。我拽着她的胳膊想往相反的方向去,她很用力地挣脱开,小跑了几步。我和她拉开了距离,她用一种极度悲凉的眼神看我,我没能读懂,然后她不再等我,朝正在吸烟处点烟的女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