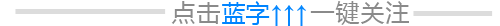

竹林七贤
摘自《世说三昧》,岳麓书社出版,经公众号岳麓书社(微信号:ylss1982)授权转载。
“美容之风”也可叫作“容止之风”。《世说》有一个门类,叫《容止》。
容止,就是容貌举止。这个词现在很少用,但在古代却是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史书中介绍传主的外貌时,总是会说“美容止”,或“善容止”。
《容止》一篇便记载了许多帅哥美男的故事,我们对“美容之风”的解读也就围绕他们展开。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奇怪的是,早期的文献对于女性美的记载比较多,而在魏晋时期,对男性美的发现和欣赏仿佛一下子被唤醒了,男士爱美,成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精神事件。
其实,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这种风气自汉代就已肇始,魏晋时终于流衍而成一种朝野相尚的风气了。和我们今天男士也用护肤品一样,汉末以来,在上层贵族和名士圈里,就有了“傅粉”[1]的风习。
在《世说·容止》篇中,第一则是曹操“床头捉刀”的故事,紧接着就是著名的“傅粉何郎”之典: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一说魏文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容止》2)
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为司空时收纳其母尹氏,何晏也就“拖油瓶儿”地成了曹操的养子。
何晏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夙惠》2)
七岁的小男孩居然“划地为庐”,不愿意“认贼作父”,真也不易。或以为何晏有“俄狄浦斯情结”,也可聊备一说。何满子先生说:
“据弗洛伊德的‘奥迭普斯情结’说,儿子对母亲怀有特殊的潜在性爱。他画地为‘何氏之庐’,正是对占有其母亲的曹操的反抗,一种所爱者被夺取了的本能的嫉妒,或至少有这种潜意识的成分在内。”[2]
史载,曹丕对何晏很不待见,不呼其名字,动辄称其为“假子”[3]。“假子”本有“养子”“配偶的前妻或前夫之子”二义,但在曹丕嘴里,怎么听怎么像是“假儿子”!我猜想,这里面未尝没有遗传学方面的妒忌,因为曹操形貌矮丑,曹丕大概也不会帅到哪儿去,而何晏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美男!
美貌的人往往极端自恋,何晏就是好例。
刘注引《魏略》说:
如果说“美姿仪,面至白”是何晏的“天生丽质”,那么,“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就是他的“外饰”,魏明帝曹叡(一说魏文帝曹丕)怀疑他的“面至白”乃“傅粉”所致,也就顺理成章了。
于是给他热汤面吃,何晏吃完以后,大汗淋漓,就用“朱衣”[5]的衣袖擦了擦脸,没想到,面色居然变得更加皎洁明亮了!这和《魏略》的记载颇矛盾,似乎“傅粉何郎”完全是个冤假错案,故学者多以为此事不可尽信。
其实,《世说》从来不在乎可信不可信,关键是好玩不好玩。要我说,面至白而好涂脂抹粉的大有人在,因为自古迄今,黄色的中国人原本就有一个千古不易的美的标准,那就是——白!
何晏这个人,因为在齐王曹芳正始时期依附曹爽,后被司马懿所杀,所以在随后的历史书写中被严重“妖魔化”了。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何晏应该是曹魏时期不可多得的第一流人物,在他和天才玄学家王弼的共同努力下,开启了令后世向往不已的“正始之音”,其玄学造诣和清谈水平之高,可以想见。而且,由于出身和门第的关系,加上不可思议的美貌,使何晏成了当时贵族士大夫阶层的“时尚先锋”和“大众偶像”。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谈。
魏晋男性美的标准,除了“白”,还有“高”。
和今天一样,“形貌短小”者简直就是“二等残废”,像刘伶那样“身长六尺”“貌甚丑悴”的就只好“土木形骸”。
自汉代以来,史书中描写人物,身高就是重要的一项。
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后汉书·郭泰传》:“身长八尺,容貌魁伟。”《后汉书·赵壹传》:“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三国志·诸葛亮传》:“身高八尺,犹如松柏。”等等,不胜枚举。
到了魏晋,对身高的描写开始和优美的自然物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美丽的词语。
在《世说·容止》篇中,就有不少玉树临风的“伟丈夫”: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容止》3)
《世说》中到处是“人比人,气死人”的故事,魏明帝曹叡的小舅子毛曾真是“没头脑”,你长得歪瓜劣枣不要紧,可干嘛非要凑到大帅哥夏侯玄身边去呢?结果给人“抓拍”到了这样一个比例严重失调的“快照”,且美其名曰“蒹葭依玉树”。古书中的“时人”或“好事者”,有时真比现在到处挖人隐私、报人糗事的“狗仔队”还可恶几分哩!
夏侯玄被称为“玉树”,因其几乎把帅哥的两大标准都占了——白,而且高。
紧接着的一条说: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容止》4)
夏侯玄被比作“日月”而且“朗朗”,足证其白;而把李丰比作“玉山”,则是白且高的另一个比喻。可惜的是,这样一对美男竟一同惨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之下!
至于阳刚美男的代表嵇康,更有一则经典的描写: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5)
还有一个名士叫裴楷的,也是个著名的帅哥。《容止》篇第12则说: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裴楷和“土木形骸”而“龙章风姿”的嵇康一样,都是不加修饰也很好看的,即便“粗服乱头”,也被称为“玉人”或“玉山”。
至于西晋清谈宗主王衍,只要看看他那双和玉柄麈尾“都无分别”的手,便知道其人有多么白了: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容止》8)
潘安仁(潘岳)、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容止》9)
想想看,“连璧”——连在一起的白璧,那该是怎样的光彩照人呢!
卫玠的舅舅、“俊爽有风姿”的王武子,一见到美男外甥就感叹:
不用说,他是在赞美卫玠的“美白”效果比自己好。
为什么古人总爱把人与玉联系起来?
因为先秦时即有“君子比德”的传统,其中最为人喜闻乐见的就是“君子比德于玉”。而把人与自然物联系在一起,在美学上也有个说法,叫“人的自然化”。
想想也真有意思,在魏晋六朝,男人的美是可以被欣赏、被“消费”的,那些和“玉”有关的好词都纷纷用在男人身上,而现在倒好,“玉”成了一个阴性的前缀,“玉人”“玉貌”“玉体”等词语几乎被女性霸占了!这说明,现代人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退”了。
近年来的大众娱乐文化,出现了“中性化”的潮流,像“好男儿”等娱乐节目的出现,表明男性美的消费浪潮又席卷而来,我想,这和女性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不是什么新鲜事,也谈不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如果说,白、高是描绘其外在之“形”,那么,内在之“神”靠什么显示呢?
首先便是“眸子”,或者说“目睛”,俗称“眼”。孟子早就发现“眸子”是了解人的关键,他说: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
蒋济甚至曾写过一篇《眸子论》,专论眼睛的功用,认为“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三国志·钟会传》)。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明才能眼亮,而眼亮,是一个人内在精神和生命活力的体现。
所以,我们在《容止》篇中,可以找到好几双咄咄逼人的“电眼”:
裴令公(裴楷)目王安丰(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容止》6)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容止》10)
又是一个“电眼”帅哥!裴楷夸王戎眼亮,怎么看都像是在“表扬和自我表扬”!
再看下面一则:
王右军(王羲之)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容止》26)
“面如凝脂,眼如点漆”,即肤色白和眼睛亮居然成为“神仙中人”的重要条件!
刘注引《江左名士传》说:
永和中,刘真长、谢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标令上,为后来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粗可得方诸卫玠。”
能和卫玠相媲美,这位杜弘治简直堪称江左第一美男了。
如果一个人容貌一般,甚至很丑陋,只要有一双明亮的眸子,也能凸显其风神气度!
谢公云:“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容止》37)
支道林的相貌丑异是出了名的,但凭着这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照样让人刮目相看。
西晋时,最有名的美男莫过于潘岳。《潘岳别传》说:“岳姿容甚美,风仪闲畅。”他和夏侯湛在一起时被人们称为“连璧”,珠联璧合,相映成辉。这是正面衬托。
也有“反衬”的例子: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左思)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7)
左思才华横溢,但貌丑口吃,也算是天公不作美。这个故事除了表明,古代的追星族绝不比今天逊色,附带也说明了另一个道理,即女人也并不比男人更不“好色”。
只要看看那些大姑娘小媳妇是如何对待潘帅哥的,就可推知,“看杀卫玠”的故事虽然有些“八卦”,但却属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此条刘注引《语林》,则讲了一个“掷果潘安”的典故:
安仁(潘岳)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张载)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
张孟阳就是西晋著名文学家张载,他和毛曾、左思一样,都是缺乏自知之明,毛曾还好,只是被人当作蒹葭奚落一番,左思和张载则一个被“吐口水”,一个被“拍板砖”,“身心”均受到巨大伤害,要多倒霉有多倒霉!
要我说,这真是“粉丝的暴政”了。从来的粉丝都是“好恶大于是非”的,他们崇拜一个人,便不许别人亵渎或影响这种崇拜,而不管他们崇拜的对象,事实上是否值得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潘岳不仅貌美,而且有“好神情”,形神兼美,这大概也是他受到女士追捧的重要原因。
而在名士圈中,风神之美、才情之美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还在外形和仪态之上!这也就是所谓“神超形越”!“神”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存在,所以,在方法论上仍不得不诉诸形象的譬喻。比如:
林公(支遁)道王长史(王濛):“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容止》29)
东晋的清谈大师王濛也是帅哥且十分自恋,刘注引《语林》说:
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
男人照镜子原也稀松平常,可是一边照,一边臭美,甚至提着父亲的名字赞叹遗传基因发生了“突变”,这不是极端的自恋是什么?
支道林大概很羡慕这位王帅哥,说:“看他敛衿作态的样子,多么轩昂而又美好!”真是举手投足间,尽显风流本色!
还有一个故事说:
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王洽)许。尔时积雪,长史从门外下车,步入尚书省。敬和遥望,叹曰:“此不复似世中人!”(《容止》33)
面对美丽的事物,人们常常会觉得语言的苍白,当王导的儿子王洽远远看见雪中走来的王濛时,叹为观止,思维一下子发生了“短路”,只好说了一句:“这简直不是尘世中人!”言下之意,王真是“神仙中人”了。南宋刘辰翁评此条说:“雪中宜尔。”发现外部环境对人物神韵的烘托作用,可谓独具只眼。
无独有偶,《企羡》篇也有一则完全可以放到《容止》篇中的故事说: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企羡》6)
这个王恭(?—398),大概是东晋末年最后一位美男,“身无长物”的典故就与他有关。
《德行》44载: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王忱)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这又是一个找不到言辞而只好求助“神仙”的赞叹,而且,又是以洁白的微雪作为背景的。试想,在“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背景之下,蓦然看到一个“乘高舆,被鹤氅裘”的翩翩美男,可不就是恍如仙境?!
再看下面一则: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39)
也不知道谁这么会欣赏人,他看见姿容美好的王恭,竟然把他比作春天新绿的柳树,“濯”本是动词,洗涤之意,“濯濯”则是形容词,非常贴切地表达出了王恭给人的那种明净清新的阳光感觉。这固然是口头即兴的感叹,却又何尝不是在作诗!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30)
这是赞美王羲之的风度,说他如浮云一样飘逸,又如惊龙一样矫健。《晋书》本传把这个比喻用来形容王羲之的书法神韵,也是别开生面,境界全出!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容止》35)
一个被比作“朝霞”的大男人,该是何等让人觉得亲切而又温暖,简文帝是个连老鼠都舍不得加害的“心太软”的男人[6],这样的男人不是也自有一种妩媚么?
当然,美好的形貌还必须和相应的才情相得益彰,才会文质兼美,如果徒有其表,那也如“绣花枕头一包草”,让人徒唤奈何!
王敬豫(王恬)有美形,问讯王公。王公(王导)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容止》25)
王导对“有美形”的儿子王恬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的是你才华与美貌不相称啊!”王导的感叹,是对魏晋美容之风的一个精彩的注脚,说明在当时,对形貌美的追求是与对内在精神气质和才情风度的重视互为表里的。
然而,这种男士美容止的风气到了南朝便走向极端,成了单纯的“以貌取人”了。
《颜氏家训·勉学篇》就说: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南朝的史书,到处都充斥着诸如“白皙美容貌”(何炯),“洁白美容仪”(王茂),“眉目如点,白皙美须髯”(到溉),“方颐丰下,须鬓如画,直发委地,双眉翠色”(梁简文帝),“白皙美须眉”(何敬容)之类的外貌描写。
这种崇尚“小白脸儿”的风气虽然来自魏晋,但其实质又大不相同。魏晋时,有雄武之貌者如曹操、王敦、桓温,有落拓之表者如刘伶、庾子嵩、周伯仁、韩康伯诸人,照样会被欣赏,而到了齐梁年间,一个人长得太对不起观众几乎就成了一场灾难,有人就因为形短貌丑一直不被重用,这和“小白脸儿”的左右逢源恰成鲜明对照!
因为对人物的形神之美如此重视和欣赏,所以汉末直到魏晋,人物识鉴、品藻和赏誉的风气也就大行其道,一系列被我称之为“人物美学”的概念、范畴、方法和体系应运而生,并对文学、艺术的赏鉴和理论产生重要的影响。
宗白华先生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论〈世说〉和晋人的美》)从这个角度上说,这股美容之风其意义真是非同小可!
这是一场追求“神超形越”的千秋大梦,不仅晋人沉迷于此梦,千年之后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1].傅粉,俗称搽粉。余嘉锡先生考证说:古之男子,固有傅粉者。《汉书·佞幸传》云:“孝惠时,郎侍中皆傅脂粉。”《后汉书·李固传》曰“梁冀猜专,每相忌疾。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云云。此虽诬善之词,然必当时有此风俗矣。《魏志·王粲传》附邯郸淳《注》引《魏略》曰“临淄侯(曹)植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坐。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云云。何晏之粉白不去手,盖汉末贵公子习气如此,不足怪也。(《世说新语笺疏》)
[2].参见:何满子.何晏与奥迭普斯情结[M]//中古文人文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73.
[3].《三国志·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又,刘注引《魏略》也说:“晏父蚤亡,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其时秦宜禄、阿鳔亦随母在宫,并宠如子,常谓晏为‘假子’也。”
[4].刘孝标注称:“按此言,则晏之妖丽,本资外饰。且晏养自宫中,与帝相长,岂复疑其形姿,待验而明也。”
[5].“朱衣”这个细节也很可注意。《晋书·五行志》称:“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莫非,何晏此日所穿“朱衣”即“妇人之服”?
[6].《德行》37载:“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本文摘自《世说三昧》,刘强 著
为“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第三部
毛泽东一家首次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
1946年2月11日出版的《时代》,“外国新闻”栏目中的“中国”报道,有一则简短通讯——《毛的一家》。该通讯依次报道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飞抵延安的消息及毛泽东的婚姻情况等,并配发了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的一张合影照片。


△点击图片,查看所有往期杂志

△点击图片进入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