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有关“奔马和道路”的比喻文字见诸于邓子滨研究员新著《刑事诉讼原理》之中。
陈兴良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论思考,而不是司法论研究。这也正是本书不同于其他刑事诉讼法著作的鲜明特征”。
作者的自序也同样强调,
“这是一本关于刑事诉讼的书。我在本书中努力描绘的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刑事诉讼,这意味着本书不仅不以现行法条为依归,而且立法的某些体系结构将是本书批评的对象”。

《刑事诉讼原理》连续获法律新书榜单第一名
中秋节前夕同门与导师小聚间,学兄邓研究员赠了我一本《刑事诉讼原理》。
今年的中秋节就是在拜读这本专著中渡过的,也算是享受“精神大餐”了。
或许是思维惯性,或许是“路径依赖”,基于近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从事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指导性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
我
特别在意此书中有关裁判文书说理的有关论述,于是有了从这个视角来谈点品读此书的感受心得和延伸思考。
刑事诉讼是一个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各个阶段的过程。
如果说现代刑事法治必然是“说理型法治”、和谐社会必然是“说理型社会”的话,
那么,刑事诉讼每个阶段的活动均需要
说理
。
就审判阶段而言,庭审说理和裁判文书说理更是重中之重和必不可少。
《刑事诉讼原理》
“前言”“目的要旨”“诉讼模式”“正当程序”“基本原则”“居中裁判”“平等对抗”“诉讼构造”“证据证明”“法庭审判”“法律救济”
等数章中均有涉及审判说理方面或详或略、不同视角、比较法域的论述。
例如,
“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纠问成分,与东方式的纠问差异巨大。
最大差异在于判决书有比较认真的说理,从事实陈述、双方争点、证据相关性及合法性,以及法律何以适用,都一清二楚,从而有利于上诉审法官作出判断。而判决书是否说理,可以判别一国所处的法治状态”
(第61页)
;
“正当程序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不仅要有正义,而且必须让人看得见。看得见的正义意味着判决理由必须公开展示,这一展示的直接结果就是让人看到司法解决的法律依据”
(第95页)
;
“有关部门习惯于说理,对健全法治非常重要,只有听到说理,人民才有可能实现监督权,才有可能防止政府被利益集团绑架。如果政府不习惯说理,那么政府行动经常会是突然的、任性的且对失败和损失不担责的”
(第356页)
;
“检察官的抗诉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因此,不同于被告人的‘无理由’上诉,检察官必须陈明具体的抗诉理由。比如,量刑不当,没有依法组成合议庭,未参与庭审的法官参与了判决,法院审理了无权管辖的案件,作出了与其他同级法院既有判决相反的判决,对指控事实未予判决或者对未起诉事实作出判决,判决书未附判决理由或者所附判决理由与判决结论不符,等等”
(第497页)
;
“当上诉人提出具体的上诉理由时,上诉审法院有义务对上诉理由进行调查,而且‘应当从保护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的主张的角度进行职权调查’,不应只将一审‘经审理查明’部分复制到二审判决书中……未开庭的书面审,因没有采用开庭审理的方式,所以不应笼统地说‘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相同’,因为……经过法庭调查、质证、听取被告人当庭申辩者,才可谓之查明,以书面审为主的审理,只能算作一种简易复核”
(第503页)
这些论述是从不同侧面或者维度对“如何说理”“为何说理”“说什么理”等问题的解答。
例如
,
“不能以正义的名义肢解法律,必须循法律的途径达至正义”
(第72页)
,
“正当程序真正关心的不是结论,而是结论形成的过程”
(第101页)
等“金句”就是对“为什么要说理”的哲理式回答。

德国学者下列言论的引述,
“还有一项成就,那就是法官必须要对他的判决作出合理的解释。论述的重点不仅在于法条中每一个字的适用,更关键的重点在于逻辑。法官唯有在判决中提出一个完整且令人能够理解的证据链,明确指出通往真实的道路,这个判决才能成立”
(参见[德]汤姆斯·达恩史戴特:《法官的被害人》,郑惠芬译,卫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在产生司法判决的程序中,举足轻重的不是任意的理由,而只是相关的理由。如果我们把现行法律看作一个理想地融贯的规范体系的话,那么这种依赖于程序的法律确定性可以满足一个着意于自己的完整性、以原则作为取向的法律共同体的期待,从而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他理应拥有的那些权利”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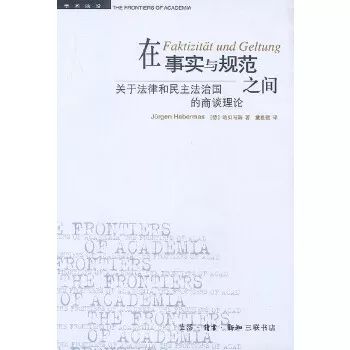
就是对“如何把理说好”的方法论指引。与此关联的是,作者在《刑事诉讼原理》中有关“如何思维”的论述,同样对审判说理(例如庭审说理和裁判文书说理)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借鉴意义,例如,不妨换位观察,反向思考,追究者感觉哪些规则最掣肘,这些规则就一定是保护被追究者最有效的”
(第25页,“反向思考”)
“希望赞同‘营救酷刑’的人明白,一旦例外地允许刑讯,无法遏制的就不仅是实施范围的逐步扩大化,而且是实施手段的不断恶劣化”
(第34页,“例外”的运用)
“何谓审判利益,不好从正面定义,但可以从反面考量,即如果中途放弃已管辖案件,会在本地区造成被动”
(第151页,“反向思维”)
“就当前醉驾测试而言,不应仅以仪器为准,而应软化过硬的数据标准,采取先形式认定、后实质排除的限缩方法,将醉驾路检分为观察和检测两个阶段”
(第352页,“先形式后实质”判断)
“各持己见者自说自话是一种常态。无法说服对方时,或许把各自的主张推到极致,看看在极致状态谁更早地陷入困境”
(第443页,“片面的深刻”)
“在明确什么是真正的法庭审判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什么不是真正的庭审”
(第456页,反向思维)
等等,均可以作为增强庭审说理或者裁判文书说理效果的方法或者策略。
此外,作者有关“纽扣案”的深度评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又为法官撰写
事理、法理、情理、文理
均恰到好处的精品裁判文书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式指引。
《刑事诉讼原理》是“体系化、原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专著”,尤其是烙有刑法学者身份的邓子滨研究员突破“饭碗法学”之藩篱、立足“刑事一体化”境域撰写的程序法学著作,更是为我们提供了多维度的品读视角。
例如,作者论道,“刑法、刑诉法学科各局严重,不甚顾及彼此看法。
例如刑法理论上研讨的特殊认知者问题,可能没有考虑到,果真有这样的案件,证明起来恐怕只能仰赖口供,而自我归罪的口供又怎样得来?
刑法中设定的犯罪成立条件,如果落实到证据上过分指向对主观心态的自我描述,就等于鼓励刑讯逼供”
(第125页)
;
“就我国刑诉法而言,有多处条文将被害人与证人分别加以规定,从体系解释角度,不宜混淆。可有的刑法学者却认为,暴力取证的对象是证人,但宜作广义理解,被害人、鉴定人,甚至没有作证资格的、不知道真相的人也可以成为暴力取证罪中的证人。尤其是刑讯被害人,比之于对证人刑讯更加恶劣。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混淆了证人与被害人的界限,在暴力取证罪中得到的个案正义,不能抵消它所破坏的体系解释所要求的同一概念的含义确定性”
(第470页)
,等等。
更能使法官办案克服单学科思维可能存有的片面之处,更好地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一体化层面达至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我这里着重从“说理”的视角,谈谈品读《刑事诉讼原理》的肤浅感受,不当之处,敬请诸位方家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