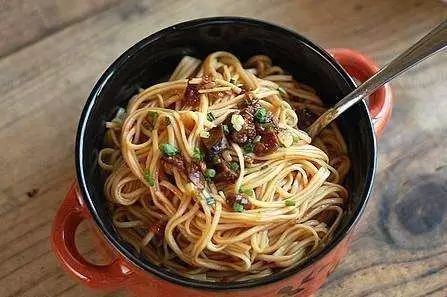天虹书稿《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既成,索序于我。我对河朔藩镇的精英素无研究,本不敢置喙。但见第三章《社会流动视野下的“河朔故事”》运用“多重忠诚”的概念,试图从藩镇本身的政治文化角度认识河北社会,探讨“忠义”观念与藩镇上层精英阶层流动,河朔节度使更替背后的深层原因,感到颇有新意。历史人物的行为与自身的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欲究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件参与者的价值观念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而“忠孝”正是历史人物价值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孝”事关建立、维持君臣关系;它也是朝廷稳定边境,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利器。但“忠孝”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本文略述我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以引起读者对“忠孝”问题更多的关注。
“忠”是对最高统治者恪守信用,矢志不渝;“孝”是对父母绝对服从,尽赡养义务。“孝道”表现在尊卑分明、上下有序的家庭关系中。理想的“孝道”具有绝对性:子女完全接受父母,无论其言行如何乖张,都不信口批评。将这种精神推广到君臣关系中就是“忠”,是臣下对君主的毫无保留的“单向忠诚”。虽然习语中有“忠孝”的说法,但“孝忠”才是更准确的表达。《礼记》有“家齐而国治”一语,表明“孝”是源,“忠”为流,二者是因果关系。
“单向忠诚”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是现实政治生活的常态。孟子的“忠诚观”有“单向性”、“双向性”和“多向性”三个侧面。他认为,“忠诚”是“双向性”关系,诸侯及臣下必须履行各自的责任、义务。如果一方失信,关系即告失效。臣子可以转而效忠其他诸侯。孟子为“忠诚转移”辩护,揭示了“双向忠诚”的合理性。“单向忠诚观”和“双向忠诚观”出现在“六亲不和”、“国家昏乱”的春秋时期,是思想家们为重塑家庭、社会秩序提出的主张。前者颂扬“孝慈”,赞美“忠臣”。后者认为,诸侯也有对百姓“尽忠”的义务:确保国家安全,百姓安康,即所谓的“上思利民,忠也”。诸侯虽然期望臣民绝对服从,但也十分清楚,要求百姓、臣子无私奉献乃至牺牲生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他们经常把“忠诚”与不同形式的精神、物质回报联系起来。换言之,“臣事君”是有前提条件的。满足这些条件是“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双向忠诚”在君主身上的具体表现。一些思想家甚至把秉持“双向忠诚观”提高到“圣人之道”的高度。显然,君臣之间是“双向忠诚”关系。“忠诚”不是“单向通道”,而是具有“双向”特性。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单向忠诚”是个例,更多的是以效忠君主为名,行追求个人利益之实。“忠”的核心是“诚”。人臣为国家利益着想,就要直抒胸臆,无所畏惧,即便是忤逆君主的意愿也在所不惜。但一些大臣以“谄媚”维持着对君主表面上的“单向忠诚”,实际上以个人利益为重。面对君主危害国家利益的意愿,他们明哲保身,恭敬从命。而一旦国家有难,他们就抛弃旧主,改换门庭,转而奉事其他侯王。“多向忠诚”才是他们的座右铭。
在初唐的政治伦理中,“多向忠诚观”因其实用价值而占有重要地位。李渊起事之初,为掩饰其倒隋的动机,谎称仍忠于隋室。他同时向突厥称臣,避免自己的基地太原受到突厥和其他中原逐鹿者的夹击。这些策略均基于“多向忠诚观”。唐建国以后,对隋朝旧臣、将领采取包容、重用的政策;只要他们为新朝效力,就接受他们的政治忠诚转向。太宗重用隋朝重臣魏征,是在政治生活中运用“多向忠诚观”的又一实例。魏征更直接否定了“忠臣”这一概念:“愿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也。”在他看来,“良臣”能对皇帝提出中肯、切合实际的政策,使君主、个人均获益。而一些所谓的“忠臣”,只知顺从上意,胸无治国大计,结果是使“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这说明,对太宗来说,效用层面的“忠”(即个人政策建议给朝廷带来的实际利益),远比口头上的“忠”来得重要。在这个前提之下,不必计较一个人是否效忠过前朝。
有唐一代,躬行儒术并不是统治阶层的处事风格。“单向孝忠”更不是政治行为的圭臬。李世民杀长兄、幼弟,武则天处死亲生儿子,都带有“鲜卑—突厥”政治的烙印。唐廷采取了一些试图改善世风的措施。其中之一是为大臣制定谥法,褒奖死者的“忠义”之举,以期生者效仿。个中的三种“忠义”行为(“危身奉上”、“危身惠上”、“危身赠国”),甚至要求臣子为皇帝、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朝廷颁赐给官员、外国君主、部族首领的封号、名字中,“忠”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史家在记录外国来客造访唐廷时,也一厢情愿地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归忠”。但实际上, “单向忠诚”只是皇帝对内、外臣子的政治期许。在这种期望落空后,唐廷不得不取销一些人的封号,更改他们的名字。这说明,“绝对忠诚”在当时是一种稀缺的政治品行,而“多向忠诚”才是主流价值观。以统治者为目标的“单向忠诚”,只是君主一厢情愿的要求,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满足这种要求的实例并不多。无独有偶,时人给太宗加谥号时,主要依据的是他“文治武功”的内外政策“功效”,没有用儒家的“忠孝”伦理评价他的得失功过。实际上,“单向忠诚”的绝对化是宋代出现的政治思想倾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范祖禹在《唐鉴》中对唐廷的政策提出了种种尖锐的批评。这从反面证实,“单向忠诚”在唐代没有大行其道。
“单向” “双向” “多向”三种形式的忠诚在唐代同时并存,为我们观察河北藩镇
节
度使(藩帅)及其下属的政治动向提供了新的视角。
忠诚不是单向、同质的意识形态,它有不同的表象和实质。
在以“忠”为基础的关系中,双方对“忠”能够作出于己有利的解读,从而获得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利益。
藩帅与下属军众,与朝廷、与其他藩镇之间关系的演变,无不与上述三种忠诚观念有关。
“双向忠诚”是藩帅与属下军人之间关系的实质。前者维护后者的利益,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后者向前者输诚,使自身利益受到保护。作者称这种并非稳定的结合关系为“互惠之忠”。当这种关系破裂时,就会发生逐帅,节度使更替的事件。而事件的根源,在于边疆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多向忠诚”倾向。为削弱这一倾向,藩帅试图用修建池亭、刻经、祈福等手段,在自己与军众之间构建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易州刺史张孝忠在修建池亭时就曾明确表示,此举意在“使文武毕会,尊卑有序”。当幽州上层军事动乱频仍之时,藩镇官员为节度使刻经、祈福,把他塑造成“忠臣孝子”。此举的目的十分明显:众军将应该像藩帅效忠朝廷那样,对他输诚送忠。换言之,藩帅期望下属对他秉持“单向”忠诚。
“双向忠诚”也反映在河朔藩镇众将推举藩帅的过程中。藩帅人选大都出自一两个血缘关系密切的家族。这表明军民对这些家族的认可和期许,但不是他们对藩帅的“单向忠诚”。在这个充满竞争的推举过程中,只有最强者才能出线。而如果他在掌权后有负众望,不能号令同僚,为军民谋利益,则得不到他们拥护,甚至被驱逐。
一些粟特人居住在河北藩镇,在当地婚姻、仕宦,有的再迁徙它处。作者认为:粟特群体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生存和发展策略:顺势应对。笔者以为,如果进一步深究不难看到:“多向忠诚”是粟特人行为的思想根源。这种观念根植于边疆社会的流动性之中。正如作者所说:粟特人在河北地区的活动是双向的,而非单一的向心流动。当地的民族融合、文化塑造不是单向过程。所谓粟特人“地方化”、“汉化”都是对粟特群体行为的简单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