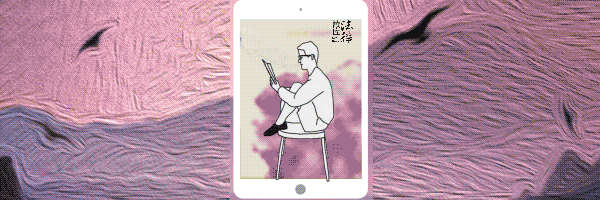
作者:周理松
来源:雨巷传奇
我入职司法机关伊始,正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形势和政策处在剧烈变革之中。
每当我春节回到老家探亲,必有一人于第二天一早准时登门来访。
“贵人到!” 随着弟弟那一句调侃式的吆喝,一个体型瘦高、手持拐杖的老人从村口走来。
他上穿灰布旧棉袄,腰系皮带,黑布裤腿似乎剪了一截,短至小腿,露出裹得很紧的棕色棉袜;
大晴天里,他竟脚穿一双深统套鞋,咯吱咯吱地一路响着,一拐一瘸地来到我的家门口。

他叫汪贵云。我的老家“云”和“人”发音相同,故我弟弟称他“贵人”似一语双关。这老头还是那个老样子,剃得光溜溜的脑袋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面色黑得像涂了一层油漆;
两只眼睛似不对称,一只睁着,另一只眯缝;见到我时他咧嘴一笑,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周干部好,您回来辛苦了!”
没有更多的客套话,没有任何听似毫无意义的寒暄。屁股一落下板凳他就直奔主题:
“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四人帮’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一个个清理出来,给蒙冤受屈的人平反昭雪,不知这个英明政策何时光顾鄙人头上?”
这个问题他不知问过多少遍了,好像只有我这个吃国家饭的“省里干部”才有发言权,才能为他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给他出切实管用的主意。
问他案件缘由、所定罪名或过错名称、最终受何处分,他总是称“说来话长”。叹息一声后,便慢条斯理,滔滔不绝诉说着自己多年的不幸。
说的都是实情,分析的都很在理,不能不令人同情,但他一没坐过牢、二没受过别的处分,三没在经济上受到特别的处罚(土改时被没收地主财产除外)。
只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运动中挨过多次批斗而已,所以很难为他找到一个具体的案由,因而也很难说清应该为他平什么反、昭什么雪。
尽管如此,他心里受过的委屈、身上受过的皮肉之苦,有许多我是亲眼见过的。
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他特别能讲道理、也特别喜欢讲道理。在过去那个年代,一般人讲道理是优点、是美德;而出身不好的人若讲道理,那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故意狡辩。
因此,凡有需要说明的事项,别人说仔细一点大家都愿意听,而汪贵云说仔细了,就显得话多。
偏偏他特别热衷于把话说清楚,把道理讲透。眼看着别人听得不耐烦,他竟毫不知趣,非得一板一眼地把话讲完。
俗话说,言多必失。当他的道理偶有破绽,被人抓住把柄时,他还一个劲儿地申辩,故显得格外地嘴硬,于是给人以“犟嘴乌鸦”的印象。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块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出身不好且嘴犟的人不仅讨嫌,而且吃亏。吃亏的时候大多随着政治运动而突如其来。
破“四旧”、批封资修、揪走资派、“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等,凡是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都少不了拿一些成份不好的人作典型或陪衬。汪贵云在大家心目中似乎最有代表性,每次运动,他都被推向前台。
不知是因为他爱讲道理,还是由于他生来就是挨批挨斗的材料,哪次批斗会如果少了他,就仿佛一桌酒菜少了一盘鱼肉,显得寡淡,于是他就成了每次批斗会的常客,批他斗他成了家常饭菜,理所当然。
问题就在于他不老实,嘴犟。
凡是批斗成份不好的人,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定他们对现实不满。
就常理而言,一个人出身不好,长期受到政府冷落,动辄挨批,他理应不会有好的心情,对现实不满应在情理之中。
但嘴犟的汪贵云死不承认自己这一点,他经常读“毛选”四卷上的文章,一有机会就捡干部们丢下的报纸看,而且看得很仔细;
广播里如有重要新闻发布,他就连忙站在喇叭箱底下,竖着耳朵一直听完,听完后还在嘴里不停地重复回味。
可见他对政治的关心,丝毫不亚于那些家庭出身好而又积极要求进步的人。生产队干部如果在公开场合讲话,突然忘了某个政治名词时,只要一问到他,准能得到一字不差的正确答案。
但是,这并没减轻人们对他与现实不满的疑心,反而以为他是在装模作样,甚至是想通过熟悉政治理论,从中寻找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武器。
对此他虽然摇头叹息,觉得十分无奈,但嘴里总是少不了一句口头禅:“天理自在人心”。正是这句禅语把大家惹恼了,批斗会上有人一再逼他解释清楚什么叫“天理”——怎能容许阶级敌人讲迷信!
揪斗汪贵云的另一个理由,是推测他的家里藏有不义之财。
按理说,土改时已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房屋等没收,分给了贫雇农,其余金银财宝也在抄家时上缴,但偏偏有人不老实,在后来的运动中,偶尔又发现其家里仍藏有金银首饰之类。
红卫兵们在批斗一个老地主时,曾在他家菜地里挖出一罐几百枚的民国时期大头银元。既然汪贵云比那人更狡猾、也更能狡辩,那就说明他的家里更有可能藏了银元。
于是把他押到台上审问,谁知他不但不承认,反而振振有词地引用一段关于依法办案的语录:“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随即,他扭过头来反问会议主持人:“你们说我家里藏有这藏有那的,证据何在?”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迎头挨了一记耳光;他不服,继续申辩,并发誓,若家里藏有金银财宝,愿拿自己脑袋作抵押,割掉脑袋赎罪。别人不听,说他的嘴巴比铁还硬;
除了耳光,紧接而来的,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但无论怎么体罚,哪怕头破血流,他还在不停地犟嘴,以种种理由证明自己的真诚和无辜。于是,被辱骂和挨打的时间更长。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午后,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人们正在开沟挖渠。挑土的、挥锤碎石的、平整路面的。一个个正在忙碌时,忽然一阵哨声响起,通知大家开会。
大家以为又是学习“最高指示”,连忙去宿舍拿语录本,不料吹哨的人大喊“不用不用”,说工地上到都处竖着语录牌,不必再去翻书,大家边干边学,学以致用即可。既然如此,突然开会,一定是有紧急而重要的事情需要宣布或讨论。
人们正在猜测时,只见两个年轻人一推一搡地押着着汪贵云上场,命令他在会场中央的位置站好。
紧接着主持人上场,在念完“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语录之后,宣布会议开始,主题是:批斗地主分子汪贵云,其主要罪行是企图篡改伟大领袖语录。
人们一听,都感到非常惊讶,汪贵云的不老实,嘴犟,大家是知道的,但他企图篡改主席语录,这是否未免过于胆大包天?
根据会议主持人介绍,工地上几块语录牌是用红色广告颜料,写成行书字体,汪贵云看着不顺眼,说应当用黑色墨水,写成正楷或黑体字,这样才显得庄重。见领导不予理睬,他竟然越说越来劲,足见其用心险恶。
“说,你是不是想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
在群众的大喝声中,汪贵云一个劲地摇头:“不,不,我不敢!”
“那你为什么说,要把语录牌写成黑字,你没看到报纸上凡有语录的地方都印着红字吗?”
“那是我的一家之言,觉得黑体字和黑色的楷体字显得更严肃庄重。”
“你还嘴硬,明明是想把伟大领袖的话涂黑吧?”
“可不能这么说呀,颜色只是一种表面感觉,与语录的思想内容无关。”
“你还犟嘴!” 只听啪地一声,有人在汪贵云的脸上打了一耳光。他笔挺挺地站着,正要开口回应,只见主持人在他背上猛推一掌:“跪下!”
他一个趔趄,双膝顿时弯了下来,两手连忙趴在地上撑着,以缓冲背后突如其来的冲力;双膝跪稳后,他拍了拍手上的沙土,嘴里嘟囔着:“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你们不要这样用力地推嘛!”
“你这个老不死的,推你搡你一下又么样!”人群中有人骂着,有人说他不老实,还敢如此犟嘴,不如拿绳子把他捆起来。
见主持人沉默不语,跪在地上的汪贵云抬起头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扫视着周围人群,然后偏过头来冲着主持人问道:“主席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他的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讥笑:“文斗武斗是说给红卫兵造反派的,与你这个地主分子有什么关系!”
汪贵云不服,又要申辩。有位批斗他的积极分子结结巴巴地骂道:“狗、狗日的,你还、还要犟嘴!”
这人顺手从地上捡起几根带结的竹根,朝汪贵云的后脑勺上一顿猛抽,抽得他那光溜溜、透着青筋的大脑袋显出一道道鲜红的血印。
他疼得难受,赶紧用双手捂住头顶,但脖子和耳朵上又在挨抽;他又用双手捂住脖子和耳朵,这样头顶又露了出来,再次挨抽,于是一道道鲜红的血印,像蜈蚣似的爬满头颈,延伸至两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