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古尔苏拉特(1989—),伊朗文艺评论人。曾供职于《电影月刊》和《电影艺术》等杂志,以及《今日德黑兰》和《七日早报》等报纸。现为电影咖啡馆网站和电影月刊《影像世界》的评论编辑。本文是他为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下称《一次别离》)撰写的评论,于2011年4月至5月间(伊朗历1390年2月)发表在《影像世界》第203期上。《一次别离》这部影片由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编剧并执导,首次公映于2011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揽获当届金熊奖(最佳影片)、2012年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无法愈合的伤口
——关于法哈蒂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

《一次别离》剧照
《关于伊丽》的延续
《一次别离》把法哈蒂在《关于伊丽》①中的观点补充完整了。法哈蒂本人在他的多次新闻访谈中也曾提到这一点。《关于伊丽》结尾时那几对情侣中的一对就有着这部影片中的思考,他们为从泥潭中走出来而努力,却再次陷入泥潭。《一次别离》可以是《关于伊丽》里面那几对情侣中的一对关系破裂的故事,比如塞皮妲为了避免他们的分手而被迫对阿里·礼萨说谎。至于特尔梅,也可以是《关于伊丽》中艾哈迈德与舒赫拉的一个孩子,他们夫妻俩教这个孩子,在回答阿里·礼萨可能提出的关于艾哈迈德与伊丽之间关系的问题时,不要说出实情,因为那有可能对大家都不利。一次教导后来导致一个谎言,特尔梅为了避免产生不利于其父亲的结果而对调查员说谎话。与此同时,纳德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女儿去说有利于他自己的谎话,却忽视了这种说谎的方式可能在特尔梅童年之时就已教给她。这样的例子还可以继续举下去。拉齐耶以其女儿索玛耶为借口从调查员的房间走出去,以便思考一下心中产生疑窦的那一刻,可与伊丽以取盐为借口而去厨房相比较;或者在影片的最后,特尔梅在两条路(跟随父亲或者母亲)中要选择一条,也与《关于伊丽》的最后塞皮妲之处境相类似。我们甚至可以就影片形式上的一些特点进行讨论,并提出这个问题,法哈蒂如何在他最新一部影片中,用设计场景和地点的方式,把我们的摄像镜头(观众的视角)置于审判者的位置,让我们就各个人物以及他们相互间的评判做出我们的评判。与此同时,在他的前一部电影②中,我们也恰如影片中的人物一样,曾不断对伊丽做出我们的评判。因此,《一次别离》通过把我们置于审判者的位置,迫使我们对影片中的各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做出判决。而《一次别离》从其他一些方面来说,也是对《关于伊丽》的补充完善和继续。《关于伊丽》在让世界认识伊朗电影的另一种光芒的方向上走出了一条道路,而《一次别离》能够使这条路得以延续。尽管《一次别离》具有一些地区性特征,可能会令不了解伊朗文化的观众们有陌生之感,但这确实是一部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影片。《一次别离》属于那一类影片——就一个国家文化深处的一些特殊内容进行讨论,却有着建立一种普世理解和领悟的能力。有意思的是,相较于《关于伊丽》,《一次别离》更多体现了对伊朗文化的回归,却享有更高的国际声誉。或许是因为现如今,在《关于伊丽》闪耀光芒之后,非伊朗的观众们能够更加容易地与法哈蒂影片中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和精神世界建立起联系。由此,可以把《一次别离》的成功部分地归因于《关于伊丽》,因为后者在使世界了解伊朗电影的某种现代风格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伴随着法哈蒂最新一部电影的成功,这种现代风格在世界各地真正的电影爱好者们中间,已经巩固了其地位。

《关于伊丽》剧照
作为建造电影世界的方法和进入电影世界的道路之细节
如同每一部好电影,《一次别离》的剧本结构和导演方式与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相符合。这是一部充满日常生活细节的电影,这些细节对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命运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对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太重要的细节的注重,就也可以是进入电影世界的钥匙。尊重这些细节,恰恰令电影把真实的生活完整地呈现给我们,正是这一点加剧了影片的苦涩和影响力。这部影片中的人物恰如《关于伊丽》中的一样是立体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是那样地真实可信和触手可及,如同从水中浮现出来。促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部分与法哈蒂截取演员们表演的方式,以及草创很多不存在于剧本中的场景有关。在影片中制造氛围的某种手法是由观众去“感知”的,在那种氛围中,有些东西甚至没有被直接提及。其他的原因还在于,法哈蒂采用了这些有时是诱导性的细节。举个例子,在我们看到索玛耶手握连接着纳德父亲的氧气瓶减压阀玩耍之前,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纳德恰好当着索玛耶的面把氧气瓶减压阀拧紧,并向拉齐耶强调说要把阀门拧紧。这时,索玛耶对纳德拧紧减压阀这个动作好奇的目光会向我们传递这种感觉——她可能要在某一时刻再来触碰这个氧气瓶减压阀;还要考虑到,在此之前影片中甚至还有一次,她指着氧气瓶,问母亲“这是什么”来表现出她的好奇。这些都在展示,法哈蒂如何在之前的多组场景镜头中铺垫一个事件,以便当观众看到那个事件的时候更倾向于相信它。该手法有时伴随着一次看起来很普通的对话出现。比如“我不会和爸爸说”这次对话——当拉齐耶决定要为纳德的父亲做清洁时,索玛耶对她的母亲说了这句话。正是这句话让我们建立起这样的想法——霍贾特一定是对这类问题非常敏感,换句话说是有些小心眼儿。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认为在医院里霍贾特伸手打了纳德这个场景更加可信,或者甚至让我们对他这样的行为有所期待。注意这些细节,会令观众更加深陷于影片中的世界,并且在观看的过程中,跟随着影片中的世界去思考那些已被讲到的内容。在纳德和特尔梅在家门口无法进去,而拉齐耶也不在家里的场景中,纳德对要往楼梯上坐的特尔梅说:“别坐在那儿,你看那儿是湿的。”对“楼梯是湿的”这个细节的交待,能够使影片的一些观众比其他人更早产生怀疑——可能拉齐耶滑倒在楼梯过道上不是由于纳德的推搡,而是楼梯湿滑所致。另外一个例子与这样一组场景镜头有关:纳德和孩子们忙于玩手摇足球游戏的时候,拉齐耶惊魂未定地往脸上洒水。拉齐耶惊慌的神色,以及在那之后她在公共汽车上的头晕目眩,都会令我们产生疑虑,可能在拉齐耶把老人带回家的过程中发生了某种事故,也可能她的头晕仅仅是由于怀孕而出现的现象。在听到拉齐耶亲口说出事实的那一刻之前,我们这种被引发的疑虑都不会消除。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影片甚至用演员们的眼神(比如在银行里霍贾特看成沓的钞票的眼神)和他们对话时声音语调的高低变化来表达。很多东西,通常是在我们第二次(或更多次)观看影片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当然,发现它们并把它们联系到一起,对于那些此前进入过《关于伊丽》那更加复杂(也更加绚丽)的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观众们来说,或许是更加容易甚至是更有乐趣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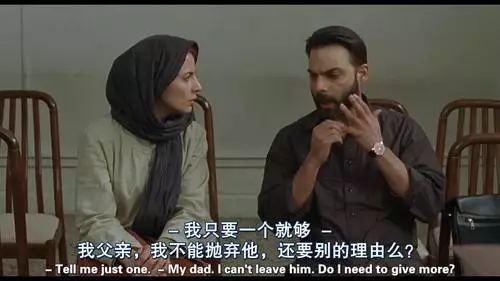
《一次别离》剧照
三代人的故事
《一次别离》中有三代人,冲突与争执发生于中间这代人之间,而这些冲突不自觉地对第一代人(纳德的父亲)和第三代人(特尔梅和索玛耶)产生了影响。西敏和纳德竭尽全力不让特尔梅卷入争吵中。西敏在整部电影里一直由于关心女儿而着急;纳德则担心事件的发展会向女儿的学校延伸,尽管他努力把他关于“不知道拉齐耶怀孕一事”所说的谎话向特尔梅展示出正当合理的一面,也仍然不允许自己向女儿提出对调查员就此事说谎的要求。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能避免特尔梅涉足此次争吵之中。是她,在纳德把拉齐耶从家里赶出去之后,要惭愧地忍受邻居女人沉重的目光;是她,由于纳德的行为,从她的同学们那里听到了伤人的话语,在她的老师伽赫拉伊女士面前感到羞赧。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当特尔梅要从父亲和母亲之间选择一个的时候,她遭受了最重大的打击,这不仅仅是要在他们两人中间做出选择,更是去与留的选择和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在整部影片情节推进的过程中,特尔梅多次被置于要做出选择的境地。在影片一开始,当西敏正在收拾她的行李之时,问她:“你不跟我走吗?”影片的后来,纳德对她说:“如果你认为错在我,你就去对你妈妈说让她上来。”这些选择最后终结于影片结尾处两个艰难的选择。一个是她要在短时间内对调查员给出答复;另一个是她要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做出最终的选择。特尔梅在这两种处境下的状况,有些类似于塞皮妲在《关于伊丽》结尾处的境遇。特尔梅要选择或者说真话,或者为了她的父亲而说谎,正如塞皮妲也要选择说出实情,或者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说谎。最终,无论特尔梅怎样选择,她的肩上都将永远会有沉重感,她都会令父母中的一方失望。正如塞皮妲要么让阿里·礼萨失望,要么考虑大家的利益,在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下,相较于其他任何人,她都会因为这个选择而背上更沉重的负担,从而使自己受到伤害。无论是特尔梅还是纳德的父亲,在整部电影中都凭着“醒着的良心”行事,特尔梅通过她的一系列问题,老人用他的目光,多次对纳德形成了质询。因此,纳德在浴室中和西敏在汽车里的哭泣(这两次流泪都发生于老祖父在场的时候),除了释放情绪减轻精神压力的因素以外,还可以归结于这两人在面对他们的良心之时的羞愧。纳德在法医处为父亲脱衣服时感到惭愧的场景,也可以归结于这种出自良心的羞愧。或者,纳德坚持对特尔梅演示拉齐耶的摔倒不可能是由他的推搡所导致的场景,除了归因于那是他为了重新赢得女儿的信任而做出的努力以外,我们也可看作是他就自己没有罪过这一点对自己和自己良心的说服。最终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为了使特尔梅和老祖父免受打击的努力全白费了,他们两人都成了这场争吵的牺牲品。父亲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状况辞世而去,特尔梅也正如她名字的意思一样(人们用来盖在陵墓上的一块织物),要以她痛苦的抉择覆盖在一个死去的关系③之上。

《一次别离》剧照
隐藏在生活经纬中的真实
《一次别离》的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可能出于某些个人原因和某种兴趣,与其中主要人物之一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甚至从心底里希望事件以对其有利的情况得以了结。但如果我们完全中立地看待这些人物,并通过影片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来对他们做出评判的话,我们很难简单地认为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是对的。影片中纳德、西敏、拉齐耶和霍贾特做出的所有反应与行动,考虑到他们表现出来的个性和他们身处其中的境地,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理的。法哈蒂也聪明地安排了一系列外部环境,由于这些完全明确具体的反应,不时就有一次灾难发生,而这些反应又或许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出的类似行为。让我们回顾拉齐耶被赶出去之前发生的一系列状况。比如纳德的父亲裸露着身体无力跌坐在浴室门的后面,并且成了挡住门打开的障碍,而那也就发生在他曾到了死亡边缘的几分钟之后,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种令人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会如纳德一样做出那样的反应。拉齐耶再次回到纳德家中这件事,考虑到拉齐耶的宗教信仰状况,以及无法忍受偷钱的中伤这些因素,我们也不会认为她的行为是不合道理和不可理解的。我们甚至会认为霍贾特也是对的,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所带来的诸多压力,他如此想要把为其孩子索要解冤赎罪钱④的行为变成对社会中产阶级的报复。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下去,并且都指向这一点:连类似于纳德中伤拉齐耶偷钱的一些错误的设想,也都是影片对仅仅根据部分事实就做出判断的错误性提出的警告之一;或者说,拉齐耶对邻居妇女所说的“倒垃圾时感到头晕”这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谎言,也可以是非常苦涩的,因为它会致使人们在回顾与反思之时陷入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并让他们共同制造出那苦涩的结局。与此同时,既不能认定人物中的某一个是这些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也不能判定另一个人就完全有理。好像所有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过错,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这正是法哈蒂的电影恰如真实生活的地方,不能简单地把正确与错误彼此划分清爽,或认为所有道理都属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社会的一个阶层。仿佛真实以某种方式隐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经纬之中,以至于无法如此简单地辨别它。无论什么细节都会反馈到我们自身,微小的错误和罪过会导致巨大的牺牲。《一次别离》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坐下来,在其中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
苦难的结局还是无尽的苦难?
法哈蒂在本片的结尾不明示特尔梅如何选择的决定是那样地正确,一如他在《关于伊丽》的结尾展示伊丽尸体的决定。基于悬疑结构的《关于伊丽》如果再有个开放式的结尾,并且不明确伊丽是死是活,除了会在影片的结构可行性上引发问题之外,也会令观众的看法产生偏差而感到不舒服。如果那样,很多观众在影片结束之时,可能会不再关注塞皮妲、阿里·礼萨和其他一众人物的命运,而仅仅要去寻求伊丽是否还活着的答案。但是在《一次别离》中,正是不明示特尔梅的抉择,才更让我们去思考各位人物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命运。这是一种能够在影片结尾限制或完全放弃简单地做结论和公布导演立场的手法。在影片的结尾,我们至少要接受一个别离,霍贾特和拉齐耶也可能在所有那些事件之后如同纳德和西敏一样分道扬镳。无论如何,拉齐耶在影片中最后的台词是这样的:“我以后可怎么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啊!”《一次别离》最容易让我们回忆起《关于伊丽》中的这句台词:“一个苦难的结局好过一个没有结局的苦难。”仿佛是刚刚看完这部影片一般,我们正在正确地理解《关于伊丽》这部电影中这句闪光的台词的含义。影片所展示的纳德与西敏的难题,不仅仅在于纳德的父亲或者特尔梅的未来,而是根源于在遇到生活中的诸多难题时,他们的看法与处理方式的分歧。一种好似裂痕一般的分歧,在所有那些事件之后变成了一道裂缝。在影片的结尾,生病的老人没有活下来,是否给霍贾特付钱的争论也没有了消息,在纳德与西敏的关系中那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这正是那个真相,特尔梅与索玛耶在霍贾特和拉齐耶的家中一起玩耍之时,她曾乐观地想,所有的难题都马上就要了结了,但她还是要艰难地接受那个真相。罪过不在纳德也不在西敏,只是有时出现在生活中的一些伤口是无法愈合的,一个人无能为力,只能伴随无尽的苦难而生活,或者选择一个苦难的结局。
①该影片还有一个中文译名是《海滩的那一天》。阿斯伽尔·法哈蒂凭借本片获得200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
②指《关于伊丽》。
③指父女关系或母女关系。
④原文是“Diyya”,指为解除血亲的冤仇而支付赎买钱。影片中霍贾特的妻子拉齐耶的流产,一度被归咎为纳德的推搡所致。
原载于《世界文学》
2016
年第
2
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公众号责编:文娟,校对:春华)


世界多变而恒永 文学孤独却自由
2017
年《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
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
:
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
010-59366555
征订邮箱
: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