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艺
术
的
,
太
艺
术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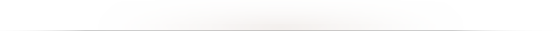

距《寂静玛尼歌》六年之后,柴春芽又一部与西藏有关的小说《你见过央金的翅膀吗》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却又如长篇小说一般有着浑然天成的结构和贯穿始终的线索。
在这本书的跋中,柴春芽认为“自己在面对西藏文明时,是个一无所知的孩子”,而希望以诗歌的方式进入西藏,其实,抛开对于文学体裁的刻板教条,《你见过央金的翅膀吗》本身亦是十一首奇幻而瑰丽的长诗。关于西藏的文字和意象太多了,柴春芽笔下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西藏,你想必从未见过。
本期微信的文章节选自柴春芽为《你见过央金的翅膀》写下的两万字后记,文末的三首诗则是柴春芽在后记中提到的诗人昌耀和高晓涛的作品。

***
小说和诗歌中的西藏现实之旅
文、摄影/柴春芽
殖民地,军阀,大独裁者,大清洗,民族乃至种族的大融合,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斗争,频繁的内战,主义、科学与迷信的混杂,信仰与原始巫术的共存……这一切,是生活在喜马拉雅以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拉美人共同拥有的人类渣滓。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同样也是西藏的百年孤独。那里的人们就如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所说:追寻“一个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没有人能决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爱情将变为现实,幸福将成为可能;在那里,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独的民族,将最终也是永远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机会”。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追求,《西藏流浪记》第七卷“寓言书”,实现了我从“美国BEAT”一代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转向,同时,也完成了我从法国新小说派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转向。
在此之后,我写作了《西藏红羊皮书》(它先于我的处女作《西藏流浪记》出版面世)中一系列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
在小说中,我将希望寄托在格桑喇嘛的身上。我在塑造一位智者的形象。这位智者能够让这个矛盾重重的世界趋向和解。
“您知道,”拿破仑曾对法国诗人兼政治家丰塔纳(Louis-Marcelin de Fontanes)说,“世界上我最欣赏的是什么?是以无力之力来创立某种事情。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即军刀和智慧。久而久之,军刀终究会被智慧所战胜。”
我相信非暴力的佛教智慧终将战胜军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在小说(同样是以无力之力来创立某种东西)中,让具体的国家和民族(西藏以及西藏的一切,只是一种符号)消失,因为我只想道出人类。

如今,有关西藏的言说已经泛滥成灾,那些以大汉族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垫底的、走马观花式的游记性散文,那些扭曲历史真相和遮掩现实残酷的商业小说,那些加了滤光镜并且经过Photoshop后期处理的明信片式的风光照片,那些以毫无科学根据和宗教理论为支撑的看似探讨生命轮回实则是用烂俗的穿越小说的路数拍摄的爱情电影,那些雪山啊草原啊骏马啊卓玛啊之类无病呻吟虚饰矫夸的流行歌曲……
够了!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妖魔化之后,西藏成了汉地小布尔乔亚和中产阶级的另一个臆造的幻景,成了炫耀自身财富的一个资本,成了寄托自己信仰虚无的一个集贸市场。

2006年夏天,我刚从戈麦高地的草原回到北京,摄影界正在热烈讨论一件事。一个摄影团去西藏,旅游巴士刚一停稳,一群头顶摄影家协会或者其他组织的各种头衔的人蜂拥跳下巴士,齐刷刷举起专业相机,对准一位藏族老阿妈狂扫滥射,就像一群侵略者举枪对准了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原住民。老阿妈无力冲出重围,最后,她哭了。这个哭泣的老阿妈的形象,久久存留在我的脑海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又令人揪心疼痛的寓言。正是这个寓言,使我在谈论西藏时不断警策自己:如果用一种不恰当的言说,那将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对我而言,亲历,阅读,检索和比较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西藏的学术专著,与藏族朋友的友情,甚至是与一个藏族女人的爱情,还有与另外一些进入过西藏的汉族同辈不断的争论,构成了现在这个以小说家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我观照西藏的一幅精神地图。这幅精神地图或多或少具有叛逆色彩,而在这个精神地图上漫游的人,因此便成了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在其著作《知识分子论》里所说的不向权贵说话的“放逐者”与“边缘人”。
但是,关于西藏,如何言说?

虽然我是一个摄影师,但我不敢用照片来言说,在中国,最有资格用照片来言说西藏的,是一个名叫吕楠的摄影师,在默默无闻的八年里,他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西藏的农区度过的。观赏吕楠那组名为《四季》黑白照片,你能够在藏人最细节化的生活常态里发现人性的力量。你也能够看到吕楠刻意回避了彩色摄影对藏人那种粗粝生活的遮蔽与伪饰,所以他用的是黑白胶卷,从而使影像颗粒粗糙,保持了影像与藏人真实生活的一致。
理应来说,作为一名小说家,我该用小说的方式来言说西藏,事实上,我正在这么做。小说,作为叙事的艺术,与西藏独有的、全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小说与史诗,其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人的创作,一个是人代神言。人代神言,自然需要格萨尔这位神灵的授权。他让文盲成诗人,他让卑贱者因其诗人的身份和海洋一般的记忆力而受人尊重,因此,史诗《格萨尔王》是神授的艺术,所以杜绝人为的杜撰。当一个藏汉混血的作家写出小说《格萨尔王》时,身在青海玉树的神授艺人达瓦扎巴对我表达了他的愤怒。人的傲慢和僭越,已经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史诗的高贵地位,在一个官方作家的笔下,被骤然拽落尘埃。

如果用诗歌的方式言说西藏,我不敢触摸的,是史诗《格萨尔王》。好在是,我拥有一批俗世中的诗人朋友,他们有藏人,也有汉人。与这些诗人朋友的交往、闲谈、同游,构成了另一个面向上的个人西藏心灵史。我愿意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诗人朋友的作品。另一方面,某些关于西藏的非我朋友所作的诗篇,填充并且修补了我自己原本贫瘠破碎的心灵。分享,而且缅怀,对于逝去的高原岁月,对于孤旅与远足,对于生命中那一段既是塌陷又是飞升的体验,对于既成的过去与可能的未来,这些诗歌作品,足以成为某种理想主义与道德行为的见证。
言说的自信由此而起,因为我更愿意谈及他们,而不是我自己。
我愿意相信自己在面对西藏文明时,是个一无所知的孩子。
以诗歌的方式进入西藏,由此开启言说的自由,这是一个方便的途径,因为诗歌是思维和智性对于作为表象与意志的世界所能具有的最为简洁、直接,而且是最为有力和真实的称述。

《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
昌耀
西羌雪域。除夕。
一个土伯特女人立在雪花雕琢的窗口,
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三个孩子
同声合唱着一首古歌: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是那么忘情的、梦一般的
赞美诗呵—
咕得尔咕,拉风匣,
锅里煮了个羊肋巴,
房上站了个尕没牙……
那一夕,九九八十一层地下室汹涌的
春潮和土伯特的古谣曲洗亮了这间
封冻的玻璃窗。我看到冰山从这红尘崩溃,
幻变五色的杉树枝由漫漶消融而至滴沥。
那一夕太阳刚刚落山,
雪堆下面的童子鸡开始
司晨了。

《僧人》
昌耀
一个闯荡人世而完全不知深浅的家伙
或有可能被上帝蠲免道德体验的痛楚。
但你是一个没有福分的人,
因此许多固执而虚妄的观念继续将你侵蚀,
有如氢氟酸液在玻璃刻下粗重的纹路。
你自命逃避残忍。
因此你继续追寻自己的上帝。
那强有力的形象以美妙的声音潮水般袭来
冲洗灵魂,让你感受到了被抽筋似的快意。
这就是信仰吗?那么信仰仅在信仰的领悟。
那么无信仰就属于麻木。
那么失却信仰就叫空虚。
那么信仰就是领悟人生五味。
难怪一声破烂换钱的叫卖就让你本能地忧郁。
你自奉人生就是一次炼狱,
由此或得升华,或将沉沦。
你是一个持升华论者。
你必须品尝道德体验的痛楚。
在你名片的左上角才有了如许头衔:
—诗人。男子汉。平头百姓。托钵苦行僧。
在你的禅杖上写着四个大字:行万里路。
你自命逃避残忍。
而逃避残忍实即体验残忍。
语言的怪圈正是印证了命运之怪圈。
但那一强有力的形象总是适时给你以爽洁快意。
你总觉得头顶有一片网系密布的河流。
或是五光十色无尽飘游的丝絮。
或是似乎一刻也不曾脱离你脐孔的胎衣。
你所感觉的不过是你心室的杂音。
而你痴信那一强有力的形象永远在头顶
与清澈同在。与氧同在。与幽静同在。
与高纬度的阳光同在。
你于是一直向着新的海拔高度攀登。
海域在你身后逐日远去,
大河在你前方展示浩渺,直到源流穷尽。
你已上溯到恒静的高山极地,
光明之顶就在前方照耀如花怒放。
太阳就在中天冷如水晶球使你周身寒瑟。
这是惶恐的高度。
这是喇嘛教大师笃行修持证悟的高度。
你感觉呼吸困难而突然想到输氧。
你如紧持盾牌逼向敌手的士兵瘫软了。
但你孤立无援。
你瓢泼似的呕吐。
你将像乌贼似的吐尽自己的五脏六腑。
你本来无须逃避残忍。
你本来就拥有行使残忍的权利。
但你却想从残忍逃亡。
你想从危机逃亡。
你挣扎。你强化呼吸。
你已如涸泽之鱼误食阳光如同吞没空气。
你懊丧了吗?你需要回头吗?
但你告诫自己: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好吗?
你瞪大瞳孔向着新的高度竟奇迹般地趔趄半步。
又向着更新的高度趔趄而去。
光明之顶始终没有从你的瞳孔逃逸。
假如你明白世俗的快意原就在自己身边
如同电气机车进站哞哞鸣响发音器一样真实,
假如你还能回忆起多氧环境的种种舒适,
假如你还记得鲸群在海流如此唱歌: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你是否悔恨失去了许多机会,
顷刻间你是否感觉一切都已迟暮?
假如你明白富氧层就在你最初出发的地方,
你以为自己将腐烂得更快一些吗?
光波以超常的压强一齐倾泻使你几欲狂躁。
此刻你渴望昏迷如同渴望黑夜。
你将因窒息而毙命。毙命也就得到安息。
但你拼命喘息像一位乞丐吮嘬一块羊脊髓。
你感觉到的屈辱是什么色彩?
肉体的花苞枯萎了,褪尽桃红。
你对自己说:不要难过,从阿谀者听到的
仅是死亡,而从悲歌听到生的兆头,
你听到氧元素远在头顶与鲸群对歌,
光明之顶被罩在你放大的瞳孔,
那强有力的形象滚滚而来时你感觉到了
被抽筋似的快意。你又向前趔趄了半步。

《八郎学旅馆的香音》
高晓涛
她是印度的卓玛或依扎莎
她是红裙渡光的招牌或是万瑛飘洒的窗扉后纤长的断指
是那一年晾干的血迹和肤色
或是纱帘后滚动的傻子和他的性爱
她是眉骨开出的夺目花朵或是鱼尸上天的透亮羽翼
她是司职于“熄灭”的女伶或是蛰伏进门廊的九尺辫穗
她是剖开的玻璃酒瓶里红艳的鸡冠或是被扔掉的另一半篮脸
坏了的一半
她也是监牢中男人的怒火和上天降下的格珍的爱情
她是神秘的联结,是冲动
或是随时开放的木花和她们尖利的蕊火
她是邪恶的长咒中难以自持的金铃动荡和摄人心魄的节奏
是进入后的改变和抹也抹不去的泪痕
是变质后印上就无法被剥夺的谎话或是反复清洗,脱下又穿上的内衣
她是你三月咯出的污血和暗地伤心的脏器或是丢弃就不会再有的迷失
是恍惚街道突现的金雨,不给你丝毫的喘息和退路
她是自暴自弃的深谷和丰腴萦怀的欲火或是海关越境的利刃而瞒天过海
她也是天灵迸裂的死者和购卖天阶的罪魁或是雨湿的邮路上孤单的誓言而无处藏身
是一个孩子手中牵着的云朵在风中回旋
或是夜路上偷吃绝望的疯子和他的牛
她是最后开口的巫师和废话或是你以虚幻换得的虚幻
是长久的欢乐和腐朽以及被广场遗忘的暗夜水涌
是悲伤你已不会再有
是病痛也已深入骨髓
她也是夺路的幸福掩面而来,抢走了羊血和祈祷的月珠,令黑夜短暂,白日暗长
或是草长的萧瑟里服毒的叛首
她已看到了极度的影子和逝去的光辉,
或者她保持沉默就足以令众生无法忍受
她是我胸中失火的药引和蜜语的喃喃
她是印度的卓玛或依扎莎
是拥有神音的雪莲或月色的肉芽随意绽露
【相关图书
】
《你见过央金的翅膀吗》
柴春芽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点击“
阅读原文
”即可购买)

【内容简介】本书是柴春芽最新短篇小说集,共收录短篇小说十一篇,各篇之间相对独立,但都以毛卜拉大草原为背景,通过阿依玛的传说串连,讲述了一个藏族村庄在时间中的轮回变化,十一个故事仿佛十一声寓意各不相同的叹息,共同编织了这奇幻、瑰丽又沉重的梦。
小说的背景设定和文笔常常让人想起《百年孤独》,藏地的故事和中文的魅力却又让它有了独特的文学性。
本书收录的部分作品曾发表于《天南》《花城》《新民周刊》《文景》《南方文学》《行走》等杂志。
— END —
关注
和
分享
,总有一个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