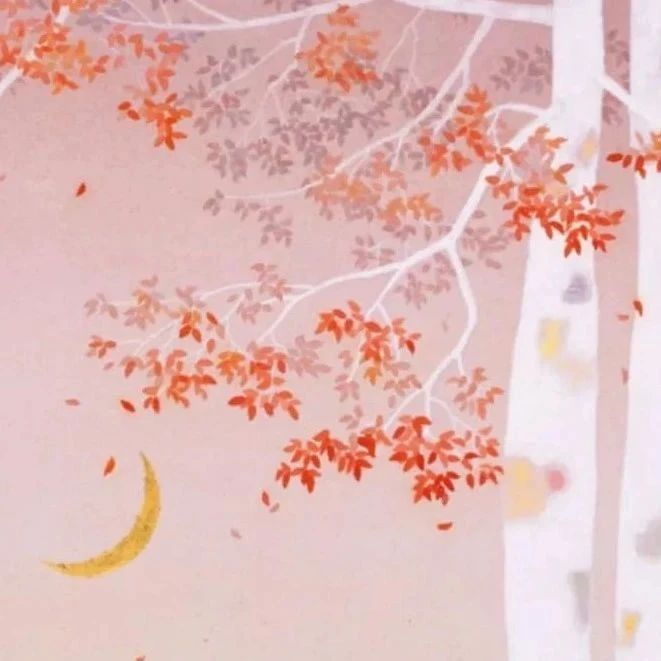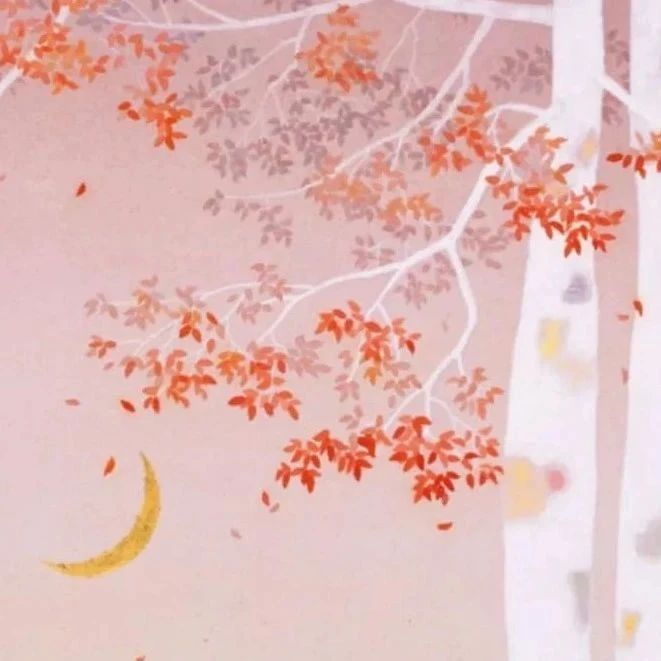《长恨歌》后三十年,王安忆新作再写上海滩“儿女风云录”。小瑟出身富门,少年时家道中落,单身北上舞蹈学校,吃尽大漠风沙,世人冷面,直至中年,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沦落舞厅谋生,在国内度过大半生之后又和父母远赴美国孤悬海外……“他向来不是有心智的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寂寞,其实是金粉世界的局外人。他享受过的好日子,其实都带有日常居家的烟火气”。《儿女风云录》以主人公六七十年的浮沉与蜕变,写出了一座城市变迁的历程。
文|王安忆
上海地方,向来有一类人,叫作“老法师”,他是其中一个。
仔细考究,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舞厅开出日场来了。窗户用布幔遮严,挡住天光,电灯照明,于是有了夜色,还有违禁的气息——舞会的内心。日场结束至多两个钟点,夜场开幕。白天的人气还没散尽呢,油汗,烟臭,茶碱,瓜子壳上的唾液,饮料的香精,胭脂粉,也是香精。窗幔依然闭着,但因为外面的暗,里头的灯亮穿透出去,一朵一朵,绽开绽开,然后定住不动了。
这类日夜兼营的舞厅,多是设于人民公园的旧茶室,关停工厂的废弃车间,空地上临时搭建的棚屋,菜市楼顶的加层。从地方看,就知道它普罗大众的性质。日场的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退休或者下岗,因为有闲;晚场就成了外地人的天下,大致由两部分构成:民工和保姆。价格也是亲民的,五元一人,男宾买一送一,可携一名女客,还有更慷慨的,女客一律免票,没有女伴的也不致落单,初次见面,总要买些饮料和零嘴。无论怎样的舞厅,都是交际场,场面上人不能显得悭吝。所以,最后统算,不赔反盈,渐渐地,一生二,二生三,蔓延开来,成为常规。很快,女多男少,性别比例又失衡。那些女宾们,伙着同乡人小姊妹,自带吃食,孵着空调,看西洋景,占去大半茶桌。没有生意做事小,主要是形象,舞厅,即便普罗大众的舞厅,也要有一点华丽的格调吧,现在好了,一派俗俚。然后,就出现了一种人物,师傅。师傅是跳舞的高手,他们以一带十,只需交付一点费用,一杯饮料的钱吧,饮料是舞厅的标配,同时,也是可见的利润,一杯饮料,可与师傅跳一曲。再淳朴的人,舞厅里坐上一阵子,也会跃跃欲试。音乐所以被古人视作教化,专辟一部《乐经》,此时显现出实效。师傅的带领下,村姑们一个个起身离座,迈开了脚步。

顶上的转灯,扫过黑压压的桌椅,零星坐了人,也是灰托托的。不意间,闪出一张森白的脸,线条深刻,面具似的凸起,就有瞬息的延宕,即湮灭在影地里,等待下一轮的光。人们知道,老法师来了。
通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午眠的人醒来,再度过假寐的时辰,拖拽着白日梦的尾翼,恹恹的。勿管舞场论不论晨昏,生物钟这样东西,已经潜移默化成定势,所以,还是生发影响力。原始的时间里,午后的一段就最暧昧,它既是凌晨,白昼开始,又像是子夜,走进黑天。更别说舞场里的人工制造,企图模拟永恒,结果是混淆,生物钟弄不好反而添乱。其实是透支,向夜晚借白昼,白昼借夜晚,借了不还或者多还。舞场里总是亢奋和颓靡两种情绪并存,此消彼长,就是证明!可是,老法师来了,情形就不一样。他自带时间,一个独立的时辰,谁也不借,谁也不还,氤氲中开辟出小天地,小小的生机和小小的循环。
给师傅的是饮料,老法师的是酒,威士忌,白兰地,金酒。就算是这样的舞厅,远远望去,像瓦砾堆,墙上红油漆写着“拆!拆!拆!”,屋顶和墙缝,流浪猫在野合,一包包垃圾从天而降,可也有威士忌白兰地金酒。在吧台里的架上,勿管真的假的,瓶子上贴着标签,曲里拐弯的拉丁字,写着古老的年份,从未听说的酒庄,至少一瓶有货,那就是老法师的特供。有时一人独资,有时几人合资,买下来,理所当然,享有贵宾级别,优先做老法师的舞伴,也可以叫作学生。
和老法师跳舞,生手变熟手,熟手呢,变高手。脚底生风,眼看着随风而去,打几个旋回到原地,脸对脸,退而进,进而退。场上的人收起舞步,那算什么舞步啊,让开去!场下的人,则离座起身,拥上前,里三层外三层。场子中间的一对,如入无人之境,疾骤切换的明暗里,人脱开形骸,余下一列光谱。一刹那,回到形骸里,再一转瞬,又没了,有点诡异呢。然而,倘若掀起一角窗幔,透进亮,一切回复原形,他是他,她是她,众人是众人。无奈遮蔽得严实,那鬼魅剧越演越烈,进到异度空间,仿佛回不来了。正神魂游离,舞曲终止,老法师将舞伴送到原位,石化的旁观者动起来。
音响送出慢步舞,人们纷纷上场,舒缓地摇曳。这样,老法师垂着手,半合着眼,对面人也是,身体没有一点触及,可是心心相印。他几乎不动,可是全场和着他的韵律。转灯放缓节奏,不那么晃眼,这样,我们就能看他仔细。他呀,至少一百八十五公分,又穿一身黑,目视更要高上三公分,抽出条子,细长细长,顶着一张脸,悬在半空。不仅因为白,还因为立体,就有占位感,拓开灯光的浮尘,兀自活动,打个斤斗,倒置着,再打个斤斗,回到原位,也是骇人。倘若离得近,好比与他舞伴的间距,看得见细部,眼窝、鼻凹、下颏中间的小坑,染了一种幽暗的青紫,刻画出轮廓。舞伴心怦怦地跳,不是骇怕,是震惊,似乎将要被攫住,携往不知什么地方,却又闪过去,放了她。不知侥幸或者遗憾,也让人震惊。灯光亮起来,眼前金箭乱射,箭头上带着一点魂,梦的余韵。就像中了魅,到舞场不就是找这个来的?唯有老法师才给得了这个!

舞厅外面,甚嚣尘上。拨开厚布帘子,后面是门,双重的隔离,才有那个谲诡的世界。走下一架铁梯,原本是高炉的上料斜桥,拆了卖了,辗转到这里。透过踏板的空当,看得见地面,夜市将要开张,排档的摊主亮了灯,支起煤气罐瓶,砧板剁得山响,桌椅板凳摆开一片。后面的水泥房子里是菜场,鱼盆里咕咕地打氧气;生蔬底下细细喷着水雾,蔫巴的绿叶菜又硬挺起来;豆制品的木格子大半空了,散发出醋酵味;熟食铺的玻璃窗里,颜色最鲜艳也是最可疑:蜡黄、酱红、碧绿、雪紫。好了,沿街的饭馆上客了,大铁镬的滚水里,翻腾着整只的蹄髈、猪脚、腔骨、肋排;小罐汤在灶眼上起泡;一人高的笼屉里,一层五花肉,一层花椒面,一层炒米粉;酒瓮剪蜡开封……这里有一种绿林气,来的都是好汉!
谁想得到,烟熏火燎里,那一具集装箱似的铁皮盒子,盛着的声色犬马。白日将尽,霓虹灯还没亮起来,灯管拗成的汉字:维也纳美泉宫、罗马天使堡、凡尔赛镜厅,陷在暮色里,蓄势待发,等候闪亮时刻。铁匣子的焊缝,不小心透出一点动静,转眼让汽车喇叭声搅得更散。远近工地的打夯机,水泥搅拌机,吊塔三百六十度掉头,也来凑热闹,这城市开膛破肚,废墟建高楼。芯子里的小朝廷,终究敌不过外面的大世界。舞曲和舞曲,乐句和乐句,休止符、附点、延长音的渐弱、跳音和跳音之间,抢进来炝锅的油爆;车轱辘碾过路面的坑;铜舀子打在缸沿;婴儿的啼哭,女人的碎嘴子——细碎却绵密,见缝就钻。可是跳舞的人,是做梦人,叫不醒的。看他们迷瞪瞪的眼睛,微醺的样子,甜蜜蜜的饮料,肌肤的若即若离,分泌着荷尔蒙,哪里经得起老法师的手,轻轻一推,你就滴溜溜转个不停。
时间速速过去,《地久天长》的终场曲里,全体下海,碰来撞去,你踩我脚,我踩你脚。跳舞让人们的心情大好,就起不来冲突,是和睦的大家庭。全家福独缺一人,老法师。

老法师遁走了。街巷的阡陌里,前院墙上爬着夹竹桃的影,后窗向外吐炊烟,主干道华灯初上,漫进一些光晕,绰约透出人和物的轮廓,看不清细部。要有明眼人打个照面,凑了哪里来的亮,就会咯噔一下:外国人!跳舞厅那种场合,本身是个传奇,这身形和脸相就像长在里面,称得协调。日常的生活却是平庸的,凡涉及一点点异端,便跳脱出来。市井中人叫作“外国人”,除此还能叫什么?既是直观的印象,同时呢,还真揭示了实质,那就是非我族类。
婴儿时候,叫作“洋娃娃”;长大些,“小外国人”;然后,很奇怪的,具体成“法兰西”;高中和大学,不只国别,还有种族,是“犹太人”!诨号的演变,大致体现本地市民的世界地理常识,是半封建半殖民历史的遗绪,也不排除卖弄的心理。事实上,他三代定居沪地,祖籍宁波,不过是个名头,五方杂居的上海,称得上原住民。沿海地区人口迁徙流动,血缘混交,遗传纷杂,只是发生在概率里,落到个体则渺茫得很。他和他的父母确实不顶像,但是他又只能生在这家里,可能是看惯了,或者这里那里,真有一点隐秘的相像。幼年的他,长一张圆鼓鼓的脸,大眼睛,瞳仁黑得发蓝,浓密的睫毛,扇子一样张开,鼻尖上翘,唇形有棱有角。婴儿肥褪去,骨骼显出来,成了外国电影中的英俊少年。西区昔日的法租界,侨属已经融入市民社会,很奇怪的,有一个群体,就是理发师,被称作“法国人”,他们所操的扬州家乡话则是“法国话”,以上海的地方成见,难免含有歧视。很难追究渊源,但多少可以证明,外国人的在地化。他被称作“法国人”,其中的意味就有些微妙了。随年龄增长,异族人的凸凹有致,渐渐变得粗阔,脸架子拉长,下颚的肌肉发达,接近通常说的“马脸”,收紧眼距,更显得深目高鼻。皮肤依然极白,不是那种半透明的牛奶色,而是象牙的瓷实的白。一头黑发,加上眉睫浓重,真是亮眼,周遭的人和物都黯淡下来。“犹太人”就是这时节喊起来的。老上海大多见过虹口一带的犹太难民,摆地摊,卖自家做的白面包,变戏法,骗走小孩子的零钱,是穷酸的同义词;文艺青年知道典出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犹太人又有了狡诈的名义;沙逊、哈同一流是发财梦里的人物,无异于青红帮,黄歇浦就是个黑社会——所以,就成了个骂名,听见有人叫,是要回敬过去的。

他的出生年月是个谜,按履历表,是一九六六年之前进校的大学生,可是,那一年滞留的在校生总共有五届,贯穿数个年头,就没办法从这里推算了;看职业,他下过乡,还参过军,这两段却又交集在一起,细考下来,原来是军垦农场,时序又乱了;他的档案且一直压在学校人事科的文件柜里,落满灰尘,没有任何就职记录,可谓白茫茫大地,一片萧然!至于户籍簿上的婚姻状况,就是谜中谜。不知道哪一个环节的忽略,单身直接跳到离异,一时上有儿有女,骤然间,又全都没有,仿佛入了道门,无为有处有还无!看外表,最是糊涂,年轻人也比不上他的挺拔紧致,然而,有时候,换一种光线角度,你会发现,他的面颊松垂下来,形成两个小小的肉囊,法令线、鱼尾纹、眉心一个川字,浮出水面,分明是张老人的脸。体态也是,就像现在,向晚的天光里,一身黑外面套了短风衣,接袖坍到肩膀底下,身形就有些塌,髋骨大幅度摆动,脚底却迈着小碎步,嚓嚓嚓的。速度倒不见得慢,很快走进一条短弄。暮霭忽然明亮起来,照出门上的脱漆,脱漆里的木纹理和裂痕,很有些年头了。钥匙插入弹簧锁,俗称“司必灵”的孔眼。这一截三四连排的旧里房子,出于某种缘故,可能是开发商资金链问题,抑或地块所属区域不同,或者只是个人的维权结果,所谓“钉子户”,于是划出动迁范围。眼见得对面日夜施工,打夯机震得墙体歪斜,楼面开裂,吊塔贴着头顶移来移去,倾下砖石瓦砾,像要把它埋了。
门在身后关上,阻住一日之内最后的天光。他立定片刻,渐渐看清周围,壅塞着各色形状的物体,床板、铁皮炉、瓦盆、铅桶、成卷的管线、泥工的桶和铲、拆解和完整的自行车,仿佛巷战的工事,壅塞着门厅,留出仅供一人过的狭道。幸亏他路熟,否则就要绊倒,伤了手脚。跻身进去,上去,两边也是工事。楼梯跷跷板似的,一头高,一头低,地板底下是空洞,听得见脚步的回声。一气到二层,稍有了些亮,晒台上漏下来,白昼的残余。掏出第二把钥匙,终于到家了。
推开房门,跳进一幅夜景图,车流在地面和高架交互盘旋,仿佛破窗而入,扑上身来。手在墙上摸到开关,瞬息寂静了。莲花状的顶灯投下乳白的光晕,平铺开来。迎面的墙安了一排扶把,东西两侧镶嵌镜子,围成一个小练功房,占去少半面积。余下大半兼作卧室、起居,客餐二用。床、柜、桌椅都是欧式洛可可风,边缘和落地细节堆砌,重重叠叠的花瓣、藤蔓、螺纹,打着小旋涡,加上裥褶累累的布艺,显得女人味重。但又有一股子清简气,除必要的日用,再无赘物。比如挂件、镜框、摆设、随手放下的衣服和鞋——进门便收纳起来,变戏法似的看不见了。倒不只是洁癖,更像禁欲,说它像僧房吧,却又不够朴,而是刻意为之,经历过风霜剑锋,就生出肃杀。
撑着扶把,绷直脚背,侧脸看镜子里的自己,调了调角度,良久,吁出一口长气,满意了。正过脸,看见窗玻璃上,逆光里的轮廓,有点不像,是个陌生人,可千真万确就是他!也是满意的。四下无声,或者是静声,超声波似的,高频率,传播不进听觉。楼宇层峦叠嶂,车在沟壑里穿行,一串串的星链,甩出去,收回来。镭射扫过夜空,此时天幕是一种蟹蓝色,星月洇透墨黑,便亮起来。巡航机穿梭来回,留下轨迹,就又亮了些。要是有一双慧眼,大约看得见低地的窗格子里,人形纸片,伸展四肢,模仿一只大黑鸟,飞,飞,飞!
和这间房子一样,属于历史的残余。前者是显学,他则是秘辛。

倘若能找到弄口的石头牌坊,上面刻着开工和竣工的年份,再找到建筑图纸,规模就呈现了。东西横贯,南北直通,占地整个街区。那时候也没什么人,清阔得很,早晚进出的动静还大些,到了午后,只看见院墙上,夹竹桃摇曳,无花果落在地上,噗噗的几声,洋辣子也落下来了,那毛刺粘在晾晒的衣服,再粘到皮肤,又痒又痛,所以叫作“洋辣子”。后来,人渐渐多起来,变得杂沓,娘姨奶妈们互相串着门,和车夫调情,曾经几何,这里有不少私家车呢。小孩子伏在水门汀地上打弹子,拍香烟牌子,摔纸壳,这些博彩性质的游戏,最早流行于码头一带,据说杜月笙就是从它起家,不知顺着什么潮流,蔓延到寻常人家。另一边呢,小姑娘们首尾衔接绕圈唱着“马铃铛,马铃铛,大家一起马铃铛”,源起伦敦大桥和窈窕淑女的歌谣,两者有什么关系,只有问英国人,这就又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去了。时间过到八十、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历史的脚步骤然加快。眼睛一眨,市政改造,左切一条,右切一条,一条一条划出去;眼睛一眨,商业用地,穿膛破肚,抽筋扒皮,一块肉一块肉挖走;眼睛再一眨,私人产权自由买卖,边角零头,一片瓦、一片瓦拆空,最后剩下这半排房子,前后不搭几个门牌号。
有两条横弄原是他家,祖父母家每月来一个奶奶收房租,他也跟着去过。弄堂里传说,奶奶是祖母的陪房丫头,后来被祖父收房,所以叫“奶奶”,祖母是叫亲娘的。有人家就在后门口交割,有的则请进去,坐在厨房里,倒一杯茶,还给他吃点心。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人,长长的烫发,一身鲜亮的旗袍,涂着红嘴唇,脸上却带着戚容,刚刚哭过的样子。前一回还和奶奶说很久的话,下一回却只开一条门缝,送出几张钞票,迅速把他们打发走了。这段记忆很短促,仿佛一闪即逝,独独留下女人的形象。那些房子忽就和他们没了关系,女人也不见了;再忽然间,变出一座小学校,不是整一幢房子,而是跳着的,这里一间,那里一间,小孩子就是在这时候多出来的。这里人家的孩子通常不出来,窗户里的钢琴,弹着练习曲,高一级的,小奏鸣曲,就是他们,现在换成拖腔拖调的读书声。

隔着直弄,人称大弄堂,和出租房屋相对的一边,有他家自住的一幢。也许这边曾也是两条同等的房产,因两条横弄口,专拉起铁栅栏,开一扇铁门进出。家里人的记事,常是以叔祖父搬走的年份,大伯伯搬走的年份,舅公舅婆搬走,姑婆姑爹离开——听起来,原先这里有一个大家族。为什么要拆散,总是有不得已的理由,人口多了,难免发生龃龉;同时呢,各自创业,各有置产;更可能是出于保全的策略。朝奉出身的祖父,手里经过典当无数,在他眼里不只是物件,还是天时运数,涨落起伏,就不能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先聚沙成塔,再化整为零,这又有一些农人的悭吝。朝上数,这新世界里的新人类,谁不是一身土两脚泥,刚刚爬上田埂头。于是,一门门亲缘出去,一户户陌路进来,大浪淘沙,余下他们一房老底子。事情并没有完,又有多少轮的更替断接,一幢楼渐渐压缩成一间,一家人变成他一个,且是后话了。近现代动荡社会的市民,向有世事变迁的抵抗力。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25年1期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王安忆
,
1954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天香》《匿名》《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等,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论著等数百万字。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等奖项。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