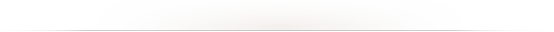文 | 王 霞
关于《冈仁波齐》,很早看过张扬的访谈,初次观影的确是把它当做剧情片看的。与《皮绳上的魂》的观影体验完全相反,《冈仁波齐》对于藏地文化和藏民生活的呈现虽然是纪实的、日常的、克制的,画面与节奏上却又是流畅的、起伏的、震撼的。相比《掌纹地:皮绳上的魂》在形式探索与内容深度上不能达成的野心,《冈仁波齐》却以笨拙而放松的题材处理方式,意外地达成了。
奇怪的是,二刷《冈仁波齐》,反而将此片当做纪录片(所谓“记录体电影”)审视,一边情不自禁以想象填充着还未有机会看到的关于它3个多小时的拍摄纪录片,一边发现人物群像以磕长头的身体此起彼伏地俯仰在318国道上,和着空谷木板的撞击声和忽远忽近的诵经,竟复沓出艺术电影中出没的诗意和象征——在张扬电影中首次亮相。
拍摄《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两部电影,张杨和他的团队赴藏区待了一年。同为“在路上”的主题,两部影片有着明显的互补和关联,从影像本体的不同方向探索,皆为呼应张扬对真实和虚构的思考。如果说解读《皮绳上的魂》的复杂和难度在于文本内部三个时空多线叙事的结构方式,那么《冈仁波齐》则是以不可复制的拍摄方式,决定了此片的巨大争议首先来自文本外部。

《冈仁波齐》没有剧本,只有酝酿了十几年的想法——“比较客观地呈现一次朝圣过程”。终于张扬在四川甘孜县芒康村找到了他需要的素人演员。磕长头朝拜行为在芒康村原本没有形成习俗,但这些来自四个家庭的老少妇孺由于各自的原因欣然前往——丧兄的老人,待产的孕妇,自卑的屠夫、赎罪的一家三口等11个藏民。
张扬团队以两台摄影机观察和记录他们的真实状态,从村中日常生活中萌发夙愿开始,他们经过2700公里的跋涉,过拉萨最终抵达神山冈仁波齐。朝圣途中由春入冬的不同季节里发生着生老病死大大小小的事件,除了老人之死其它事件都是随机的。镜头采集包括路上其它七八组朝圣队伍共600小时素材,拍摄和剪辑基本上同步进行,以便于与藏民交流细节,就地取材,有的会重新排练和摄制,体验与创作同时进行,模糊着纪录与扮演的边界。拍摄行为本身与影片主题内容同构,都处于“在路上”的自我发现与自我实践之中。

整个创作过程的不可复制性和自我指涉的实验性,对于张扬电影这其实是第二次。上一次他将镜头对准了演员贾宏声和他的一家,以复制个人真实经历的方式拍摄了《昨天》。戒毒后仍时刻濒临崩溃的贾宏声不断就生存意义向他的父亲和现实发出诘问和挑衅,最终将剧情一步步逼入炸裂状态。
张扬采取了开放式的叙事:有群体访谈、有多视角叙述、并置过去与当下两个时空、在戏剧舞台和写实空间中瞬间转换,如奥逊·威尔斯般的向外部现实世界索要一个极端人物的真实面向。影片最终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步入社会的一代年轻人进行了不可复制的精神塑像,更是由于10年后贾宏声的自戕,那一代人的迷茫与挣扎、反抗与绝望、真实如铁地定格在了贾宏声仰望天空的倔强面孔上。

父子和解、出走与回归以及现代性下的精神困惑,张扬创作始终没离开这三个相互缠绕的电影主题。但他在电影语言上的发挥并不稳定。尤其中国电影产业进入高速发展后的这几年,张扬的类型片尝试和主流话语融入始终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夹生状态。也正是因为创作的瓶颈,《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夹带着“自我寻找”的使命进入藏区,而《昨天》中困惑于“let it be”与“let it go”的两种抉择,多年后映现于这同时创作的两部作品中。
张扬作为外来者的文化身份,面临“藏区消费”敏感话题,他在去猎奇性、去符号化、去民俗化的表达上是自觉的。《冈仁波齐》中神圣的文化仪式全部划入最为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影片虽然不时切入大远景的高原地貌,在极为克制青灰色影调下,衬托人如蚁动。这不由让人联想到藏人导演松太加以“壁画美学”命名的、主要靠远景和风景支撑起的叙事风格,如同唐卡一般,没有局部和特写,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是,松太加的叙事主体是主观介入的。

影片《冈仁波齐》开始于芒康村日常生活的一个冬日早晨,烧柴、添油、搅捏糌粑,然后是袅袅炊烟下山村的忙碌:牵牛的、砍柴的、放羊的、诵经的……相对于这种乐此不疲的静态速写,叙事性在其中被降到最低层面:杨培老人有生之年去拉萨朝圣的夙愿在村子中传播开来,正逢圣山冈仁波齐的属相年,于是很快形成了一组组朝圣人群。接着镜头饶有兴致地持续着平和的观察,告诉我们每个人是如何做着春节后出发的准备:买鞋的、制手板的、做糌粑的,缝围裙的,扎婴儿袋的……静态镜头,偶有摇移,没有视线剪辑,景别限制始终让观众与画面内的藏民们保持着无意靠近的、均等的距离。这种对于别样生活的去戏剧性、去主体性、不介入的纪录方式,导演显然是清醒地保留了或者说没有丝毫矫饰一个文化他者的视角。

有意思的是,在23分钟的乡村日常写照后,第一个磕长头动作毫无预兆地突然裹现在村民送别的行为中。正因为所有指向朝圣的行为都被赋予了日常性,包括这个以等长肉身五体投地去丈量信仰的动作,所以它瞬间带来的理所应当、又难以理解的冲击力将以悬念的形式贯穿在此后的叙事期待中。
尽管文化他者的视角下,11个朝圣者被群像化,镜头不介入“朝圣事件”内部,他们的朝圣行为被同质化,但是此后相继出现的每一个危险、困境、挫折和事件,都将指向对恒定的、无阻的、不断修正的“磕长头”动作的解惑:呼啸而过的卡车带来的威胁,突然临盆的孕妇,小女孩的头痛,受恩于路边长者,遭遇碎石滑坡,腿被砸伤后的交流,施惠给磕长头的兄妹和一头毛驴,在水洼中不退缩,听杨培老人讲猎人的故事,等待虫子爬过公路,对撞坏拖拉机毫无怨言,轮番拉车与磕头,打电话回家问想我吗,歌声中携手,为继续旅程在拉萨打工,代人磕长头,在冈仁波齐脚下老人安静去世——所有的这些都以无惊无扰、心存感激、坦然面对的“磕长头”对待,这就是磕长头的意义。它不再指向特定的宗教和信仰,而是指向了它们的修辞体“虔诚”本身。影片的主体行为“朝圣”也被“在路上”悄悄撤换掉。借此,这一趟他人之旅才得以让画面外的我们在反观自我中见了众生平等,见了天地仁慈。

影片甚至为此屏蔽了一路上所有自带文化消费嫌疑的非藏民,包括以《转山》和《冈拉梅朵》重为代表的文化意淫的外来者,不管是骑行的、摩旅的、越野的汉人、还是骑马的印度朝圣者以及来自西方的背包客。哪怕是被记录下来且非常具有叙事价值的真实事件。如:“转山”的骑行小伙与朝圣者合影时摔下山崖,朝圣者们停下来为他念经超度,并许诺在大昭寺门前为他点一盏灯。
然而不管是张扬的摄制方式还是视觉风格,都不能阻挡争议,更大的原因还来自溢出文本的现代性困境。恰恰得益于前二者,这个问题才显得更加突出。
因为观众被导演置于文化他者的见证视点中,文本之外的现代性语境与文本之内的藏地生活完全不同。当我们的日常生活已完全被统摄在现代性商品逻辑中,观影过程的悬念和心灵震撼,恰恰是文本内外不由自主地比对造成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地域民族文化”早已在世界范围内被纳入到现代性的文化再生产系统中。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发展、国家话语的战略需求、精英消费群体的文化立场、多元一体的全球化格局都在这个系统中进行着协商与共谋,作为“地域民族文化”的主体,藏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俗、文化习惯、信仰仪式,不仅会因为粗糙的包装和修饰被贩卖,还由于藏民文化的传承者也处于这个系统内部,他们会因捍卫传奇、歌咏传统和文化怀旧的保守立场而取消本土文化的深度、收缩可阐释的空间——如影片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已封闭性的念经做结;或者因现代性带来的标准化模式和经济理性对藏民信仰行为已做了不知不觉的改造——如津津乐道于318国道上磕长头的文化现象原本在现代化来临之前是不存在的。

当然,在张扬看来,手机、电视、太阳能和现代交通工具还没有进入藏民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善恶伦理被置于前现代阶段。善恶伦理一旦进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伦理关系将被细化为程序伦理、权力伦理、消费伦理、乃至与影像相关的视觉伦理等等,人与人之间很难有机会发生最直面的、最短距离的善恶关系。所以在高速公路上磕长头的藏地行为一旦收入镜头,堂而皇之借城市商业院线,势必会进入现代社会搭建的各种伦理视域,面对现有的、或者是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中的种种伦理框架的层层议论在所难免。
当素人演员在文本内部欢乐地唱到:“我们有一样的母亲,却有不一样的命运,幸运的人成了喇嘛,我命运多舛,去了远方……”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歌声会给文本之外的现代社会带来怎样五味杂陈的议论。那么,我们可否借他者的虔诚寻回我们不久前迷失的灵魂呢?
影片信息

导演: 张杨
编剧: 张杨
主演: 尼玛扎堆 / 杨培 / 索朗卓嘎 / 次仁曲珍 / 色巴江措 / 仁青晋美 / 姆曲 / 扎西措姆 / 江措旺堆 / 达瓦扎西 / 仁青旺佳 / 丁孜登达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藏语 /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17-06-20(中国大陆) / 2015-09-15(多伦多电影节)
片长: 117分钟
又名: Paths of the Soul / Kang rinpoche
剧情简介
普拉村村民尼玛扎堆在父亲去世后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带着叔叔去拉萨和神山冈仁波齐朝圣。时正马年,正好是神山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小村里很多人都希望加入尼玛扎堆的朝圣队伍。这支队伍里有即将临盆的孕妇、家徒四壁的屠夫、自幼残疾的少年,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故事也怀揣着各自的希望。为了去冈仁波齐,这支十一人的队伍踏上了历时一年,长达2000多里的朝圣之路......©豆瓣
-END-
栏目编辑 | 再说 责任编辑 | 汪忆岚

扫码关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联盟影讯、活动预告、购票渠道等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