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公众号
点击右上角“...”设
置星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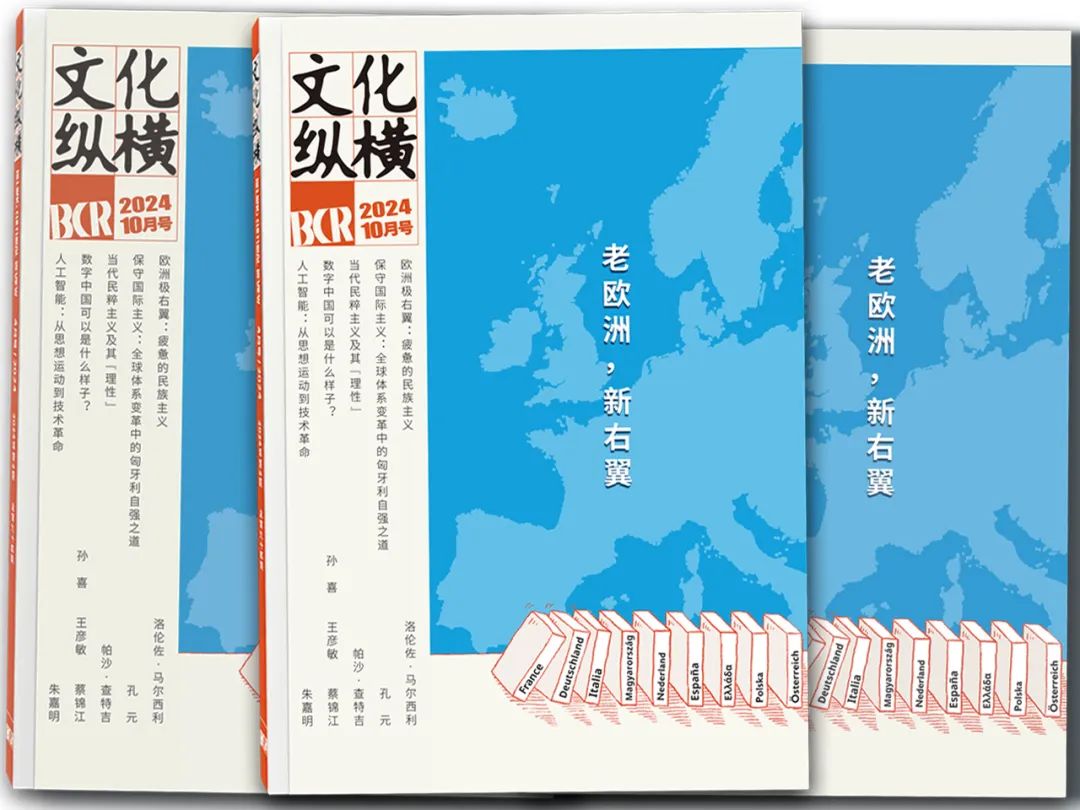
✪
孙歌
【导读】
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冷战后近30年狂飙突进的扩张后,如今正遭遇日益严重的危机。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冲突、社会撕裂以及新技术的创造性破坏,都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让全世界笼罩在不确定的迷雾中。在这样的历史节点,需要重新焕发社会主义的活力与潜力,在21世纪的全新时代条件下探索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开辟新的道路。
对此,本文尝试提出了“生民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理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特殊意义。作者指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
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社会主义和自下而上的生民社会主义两种力量
,在一个有机结构里互相缠绕,时而互补,时而龃龉。作者比较中日两国的公私观念指出,
在中国民间社会,历史上始终存在以相互扶助为基本机制,以均平为理念的生民社会主义。
正是这种“生民社会主义”的朴素的情感意识,使得近代以来在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过程中,
中国人比较容易接近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以社会主义为旗帜,开启了革命的历史征程。
本文指出,
在当代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社会主义在救灾和大规模基础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光有自上而下的机制,无法与并非整齐划一的生民的诉求相对接。
这启示我们重视潜藏于中国历史,且仍然活跃于当今民间社会中的生民社会主义传统。只有妥善协调两种社会主义的张力,发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才能释放民众的创造力,进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分的社会动能。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6月刊,原题为《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思考“生民社会主义”》,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
——思考“生民社会主义”
▍
民间伦理的生命力
“生民”这个概念来自《诗经·大雅·生民》,原本是跟后稷的溯源、祭祀、族群繁衍这些内容息息相关的。在历史传承过程中,“生民”逐渐成为“百姓”的同义语,但它并不直接等同于“人民”。
人民是一个与国家、民族直接相关的现代概念,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市民”,生民则是我们的现代国家诞生之前、在悠久的历史里传承下来的概念,即使原本所指的内容褪色,它仍然带有强烈的“天之子民”的色彩。
把“生民”这个前近代用语和“社会主义”这个外来概念结合在一起,也许不够严谨,但对我来说却很有魅力。透过这个我生造出来的用语,我发现某些看似混乱的现象可以得到解释,某些一直被遮蔽的问题可以得到揭示;在我们的语境里,有一些共同的感觉,可以借助生民社会主义和国家主导型社会主义这两个范畴得到表达。
当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两种力量,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它们相互纠缠,有时候互补,有时候龃龉,像是两股麻线拧成的绳子
。
换句话说,生民社会主义和国家主导型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立的两种社会主义,而是在一个有机的结构里相互缠绕的两种力量。
我把它们拆分开来思考,是为了思考这两种社会主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走向里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各自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先从离我们很近的民间生活谈起。《四郎探母》这个民间故事有很多版本,因为在我们的民间生活当中,《四郎探母》的故事刚好踩到了几条非常复杂的红线。在一个民间版本里,四郎和铁镜公主最后都被处以死刑。在另一个版本里,四郎最后回来探母,就没有再回大辽国去,他背叛了辽,回归了大宋,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结局。还有一个版本流传更广,杨四郎顺利探母,然后又回到了铁镜公主身边,是个大团圆的结局。总之,《四郎探母》有各种相互抵触的版本,这个状况本身就说明了这个故事的复杂性。
有意思的是,我前一阵在网上找到了国家京剧院
《四郎探母》
的演出视频,它用的是最后那个非常温暖的版本。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的艺术领域里,大团圆的处理仍然有受众,它甚至被作为《四郎探母》的代表性版本。它里面有几个环节的处理,这里简述一下。第一个环节是杨四郎的探母意愿。他在听说佘太君押着粮草到边境来的时候,15年没有见母亲,他怎么着也想回去见一面,但并不打算借此回归大宋;铁镜公主偏偏又是一个善解人意的贤惠媳妇,所以就帮他骗取了令箭,让他回去探母;不过当天晚上他必须赶回辽国,否则铁镜公主恐怕要遭难,这就让四郎面对两难的选择。这个版本里杨四郎的原配夫人被删掉了,不然剧情就太复杂了。民间传说里,据说四郎见了原配夫人以后,仍然说我们两个不能团圆,我得回大辽。那么他回大辽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履行自己对铁镜公主的承诺,以免因为自己的背信弃义而导致公主被杀头。15年间和一个契丹公主的感情以及公主冒死为他骗取令箭的举动,让四郎不得不割舍他在大宋的亲情。在杨家众人难舍难分的拉扯之中,四郎的两难选择用京剧表演身段演绎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环节是佘太君。我们通行的政治伦理中的家国,是国第一,家第二的,可是佘太君见了四郎以后,一句都没有问“你怎么效忠的国家?”,她问的是:“你媳妇贤惠不贤惠,你们俩感情好不好?”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佘太君有一个向着北方作揖的动作,感谢大辽给了儿子圆满的家庭。四郎这时候说:“两国交恶,您的儿媳不能回来拜您,我替她一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家国情怀里,家在前面,国在后面,而这两者在这个场景里是有矛盾的。
第三个环节是回大辽以后四郎险些被斩首,铁镜公主做了一系列努力,最后用她和四郎的儿子消解了萧太后的怒气。萧太后原谅了四郎之后,竟然把一支令箭交给了四郎,说:你现在要到前线去戍边。这个委任也非常有趣,
一个刚从敌国回来的敌国干将,你把军权交给他,让他到第一线去,他有没有里通外国的可能?这种委任实在匪夷所思,但在京剧里这些全都不是问题。在京剧里,走上前台的是人情,而人情里边暗含了另外一种忠孝节义的伦理观。
在看这出京剧的时候,我强烈感受到中国思想史里积累起来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的论述,与民间百姓日常的现实感觉之间有一些错位。微妙的地方在于,四郎不是没有家国情怀,他有,但是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国而是家;而且四郎有两个不同的家,哪个他都难以割舍,这时候主导他离开原生家庭回到铁镜公主身边的,是他对冒险盗令箭的铁镜公主做出的一定当晚回去的承诺,那是一个毒誓,他对自己的誓言要负责任。回大宋探母是孝,回大辽践行誓言是义。总之,这是一个比家国一体这一单线意识形态远为复杂的百姓生活故事,知识分子的论述逻辑很难有效解释。《四郎探母》之所以能演到今天,大团圆的版本之所以在所有版本中胜出,是因为它非常朴实地把民间生活里的自然情感用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它到今天仍然还有生命力,大家还是愿意看,据说在台湾上演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日本有一部歌舞伎名作叫《忠臣藏》。歌舞伎在日本大致相当于我们的京剧。《忠臣藏》讲的是江户时期一个藩的藩主被幕府下令不得不剖腹自杀之后,他手下的46个武士给他报仇的故事。报仇之后,江户的儒学家们和徂徕学创始人荻生徂徕,对这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评价。儒学家们说这是忠义之举,应该赦免武士们的罪行,让他们恢复自由。但是荻生徂徕说,如果是那样,我们的社会秩序就乱了,他们确实忠义,但是是在一个藩的领域里忠义,在幕府这样更大的领域里边,他们是谋反,所以应该用武士的礼节处死他们,也就是让他们剖腹自杀;对武士来说,这是比处以极刑要体面得多的荣誉。最后也是这么处理的。《忠臣藏》表演的就是这个复仇武士集团最终自决的故事。
▍
中国与日本社会中的“公”与“私”
把《四郎探母》和《忠臣藏》加以比较,有些有趣的问题就呈现出来了。我们可以观察到中日两个社会中,对“公”和“私”的定位和理解相当不同。依照沟口雄三先生的研究,
中国的“公”具有伦理与空间的双重内涵,伦理性导致了空间边界的不确定性,而日本的“公”概念是一个边界明确的空间概念,这是相当不一样的。
中国人讲的“公”这个观念,最早是大房子的意思,里边可以聚集很多人。这点中国和日本一样,它首先是个空间的概念。但是从一开始,在中国,公这个概念就包含了强烈的伦理性。我们看一下古人的说法:“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则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无论是先秦还是两汉,我们都看到公和万物之道、和天理是结合的。所以当我们说公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空间、某一种行为,我们首先讲的是
天道
。由于这样的一种伦理特征,
所以
公和私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它的空间边界就不再确定了。即使你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由于你违反了天道天理,你也不代表公,你变成了私。
反过来,即使在私人空间里,如果你遵循了天道,其实这也可以是公的伦理、公的行为。
比较典型的是程伊川评第五伦的这段话:“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心。”(《河南程氏遗书》)第五伦是后汉的一个名臣,他以廉洁著称。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他哥哥的孩子和他自己的孩子先后都病了,他先后照顾哥哥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但是照顾的方式不一样,照顾哥哥的孩子时,因为不是自己的孩子,他觉得他应该出于公心,所以一个晚上起来十几次去看那个孩子,但是看完了以后,他回来倒头便睡,睡得很好。他自己孩子有病的时候,他由于一些原因,觉得他不应该晚上起来去看孩子,可是他一宿没睡着。后来他自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他“狠斗私字一闪念”,说我还是有私心。
程伊川对第五伦这个态度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他说:
“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心”,意思是说,你自然而然地由于父爱而一天晚上起来十几次,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本来就是自然的行为,因此它不是私心,它是公心。可是你非要憋着,假装你是公心,你不去看,这就有了作伪的嫌疑,因此你这个方式就是私心。
在这儿我们看到,父子之情这件事儿在当今社会里绝对是私事,可是在我们的思想史传统里,它可以是公。
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尊奉了自然的法则,你的行为是不是遵从了自然性。
这是中国公概念的第一个特点。由于它具有了强烈的伦理性,所以它可以打破所谓的公和私的空间分野,在私的领域里可以有公,反过来,在公的领域里也会有私。
第二个特点是公和均平的关系。
这个特点在日本是不存在的。
均平的概念,在中国思想史的脉络里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如果用一个最粗略的分析框架来说,一直到清末为止,思想史论述里的均平都是不涉及所有人的。但即使是这样,从庄子的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叶,它仍然有一个发展。我们看到庄子讲“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帝王视角:帝王要想顺利地治理天下,必须彻底贯彻大公,只有这样做了,你才顺应了自然之力——自然是最高的天理,它高于所有人为的政权、人为的行为。
到了朱子,他对均平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出于帮助朝廷完成役法的初心,所以他并不是一般性地泛泛而论。
他说:“贫富不均,最为役法大害”,要想有效贯彻役法的话,就不要搞贫富不均。除此,对贫富不均,朱子还有其他的定义:君臣父子各得其宜。就是讲究身份、讲究各守本分。可以说这样一种均平观,一直持续到清朝中叶。
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略的划分,而这样相对的均平观,是以等级性为前提的,它实际上跟民间的均平观念是有本质差异的。
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还有另外一条潜在的线索,试图打破等级性,好汉出来杀富济贫,让人人都有饭吃。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儒学内部,公观念的走向,一直到明清之际为止,基本上是偏向于王朝统治,它包含了对王朝统治弊端的批判、压力,也包含了一些改革的策略。士大夫阶层作为王朝统治的后备军,也作为在野的富民士绅,是官民冲突的缓冲剂,同时也是维护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生产者。
但是从明清之际开始,无论是李卓吾还是东林派,都开始强调生民的权利,
当然他们强调的权利不太一样。李卓吾强调的是人人的权利、万民的权利,真正是生民,而东林派强调的是富民的权利。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不再把视角锁定在王朝的层面上。所以我们看到思想史的观念开始向生民社会偏移之后,从清朝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政治领域之外,民间自己解决问题的空间扩大了。
日本文化中的“公”则很不一样,可以作为中国的一种参照。日本的“公”这个概念是具有非常清楚的空间边界的,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前面讲的荻生徂徕对46个武士处置方式的基准就是一种空间定位。
丸山真男认为这种公私分离的空间切割,打断了朱子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连续性链条,把公、私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符合西方意义上的近代思维特征;
这个说法很漂亮,不过也不是没有质疑余地的,对此我们先不讨论。公概念在日本的空间性格,最典型的例子是,
明治时期大臣在天皇面前议政的时候可以谈国家大事,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里,他们不谈国事,至少在表面上不可以谈,因为国事在确定的空间里才可以讨论。这样的习惯,其实今天在日本的民间仍然还是有的,
比如我住在京都的时候有一个很熟的卖咖啡豆的老板,有一次我买咖啡豆时随口说了一句闲话——这是我们中国人很习惯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我说:“你们文部省真的是很奇怪,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老板正色道:“那不是我们百姓能够在这里讨论的事情。”他既不呼应也不反对,就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在我的咖啡店里谈。
日常生活里这样的例子很多。这种空间的差异感觉体现了空间界限的绝对性,这个绝对性和福泽谕吉下面的这句话,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国法有不正不便,但是也不能以此为理由而破坏它。他的逻辑是如果你破坏它,国家就乱了,乱了以后要付的代价就太大了。所以到现在还有一个说法,日本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它都不会发生革命,那是因为在它的逻辑里,可以有一次性的百姓反抗,但是绝对不会有革命,不会取代政权。像福泽谕吉这样一个明治维新时期占头把交椅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
我们再来看私的问题。在中国,私虽然没有被完全否定,但基本上是一个负面概念。因为它的伦理性往往比它的正当性更强烈,所以它和公一样,同样在空间上不是绝对的。
我们刚才看到程伊川评论的公,公可以在私生活里边体现。那么在私的范畴里边,是不是也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看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在这里,皇权可以受到指责,指责的理由是你虽然假公之名,但你那个是大私,只是因为你位高权重,我们受到你的制挟而已,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正当性。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黄宗羲接下来宣布了“人各得其私”的正当性,而它的前提是“无君”。
黄宗羲的这个说法很有无政府主义的味道,而且套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来看,好像也有个人权利的概念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国的前近代思想史里,个人权利是没有位置的,有正当性的私也是以生活共同体或者说以阶层为单位,个人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共同体里面析出,所以实际上这只是富民阶层之私。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儒学传统中天理、人欲的关系设定,在主张个人之私的时候也同样不会抛开这个前提。皇帝的大私之所以被否定,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天理。小民之私在与皇帝之私相对的意义上虽然有正当性,但也必须符合伦理要求,不是无限制的。为此,明清思想史里,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戴震那里,正面提出了“私”和“己”的分离问题。也就是说,个人欲望之私被适当地克制,“己”的欲求才能具有正当性。我们知道,“克己复礼为仁”这样的伦理观念是从先秦一路传下来的,但是它里面“己”和“礼”的含义,其实在后人述而不作的过程当中被不断改变,置换为新的内容。
到了明代后期渐渐出现了比如说“人欲自然”这样的词。
自然的伦理性我们刚才讲过了,符合自然的人欲与违背自然的人欲是有区别的。人欲和自然这一对概念的结合,是在吕坤的《呻吟语》里边出现的,人欲和自然结合之后,人欲就不那么负面了,但是它仍然是私的范畴,而私的对立面是公。
明清之际,顾炎武有这样的说法:“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这是非常重要的视角。在这个说法里,公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也不是一个高位的权力概念,而是有了足够的私,集合起来就是公。
到了清中叶的时候,戴震开始主张“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所以他说“克己复礼”时,要克的不是己,而是己里面过度的私念,也就是己的私欲。可是己里面包含的正当的欲望是不应该克的,而是要保护它。它的正当性在于“天下人之所同欲”。这里我们又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程伊川评第五伦时的那个命题:公私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天理自然。
与中国私观念这样的特征相对,日本的私不具有伦理性,而且它的空间边界也极为确定。
有一些日本人和欧洲人望文生义地说,既然日本的私人领域是绝对不可侵犯的——确实是,我们中国人混熟了以后往往你我不分,而日本人私生活的边界极其清楚,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那么西方市民社会主张的个人权利在日本很容易发生;再加上战后日本有了一个新宪法,直接就把日本私人的空间转换成了个人权利的空间,好像这么看问题很有道理;但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因为日本的私只是个空间概念,而且是一个定位很低的空间概念。它不会被公直接合并,也不会转化为公,它只是从属于公。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日本的第一人称“我”,它的汉字是写成私的。
当日本人说“私”的时候,它指的其实就是个人所占据的那一点空间,而这样的空间绝对服从于公,因此它不具有市民社会与权力政治相抗衡的张力关系,而只是一个服从的关系。与此相对,我们来看中国的私,即使是强调了万民之私可以成天下之公,它也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欧洲市民社会意义上的、个人享有权利的个人之私,只不过它的边界不断地改变,它的功能在于使皇权的大私得到节制,在于张扬生民私利的正当性。而张扬正当性后边的逻辑是,只有小民的私得到了满足,这个王朝才能太平。
我们来看吕坤下面的这段话:“世间万物皆有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万世公共之心,每怜万物有多少不得其欲处,有余者盈溢于所欲之外而死,不是者奔走于所欲之内而死,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许多人物,自足以养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缘不均之故耳。”(《呻吟语》卷五)
吕坤的这一段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几方面内容都包含进去了。吕坤强调的是,欲望这个东西是符合天理人情的,而天理人情反对贫富两极分化,所以贫富两极分化伤了生之道,因此依靠均平,可以让天地得到最好的濡养。这是吕坤关于私的主张,实际上我觉得它暗示了两种社会主义的一个接触点。
我们还可以从中日民间社会对“相互扶助”的不同感觉去认识公与私。广为人知的京剧《锁麟囊》,讲的是积德行善、善有善报的故事,但是如果和民间生活的基本机制结合起来讨论,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暗含了中国特有的民间生活的经济理性。中国的老百姓在本能上都知道富不过三代,再有万贯家财,将来总是会遇到各种意外而败落。
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积累个人财富没有意义,要积累人际关系里边相互扶助的基础,那才是将来救急的有效手段。
为什么一个宗族的人会资助族内最穷的、但是看上去最有希望读书升官发财的孩子?
这个习惯的背后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期待。所以虽然不是直系,但是族人也会资助,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外人外姓也可以资助。这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善举,因为当它变成一种社会机制,甚至变成一种推动社会运作的结构形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富有经济理性的、对不确定未来的投资行为。
最典型的例子可以看清代的善堂善会,日本有位学者叫夫马进,专门研究中国清代村落善堂善会的各种善举,从修桥铺路到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到组织团练保卫村庄,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在清代,善堂善会以村落和家族为单位,它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自助和自救的机制。这里边当然也留下了后来的一个隐患,就是团练变成了后来的军阀,军阀使民国时期的百姓苦不堪言。但是不能因此反推说在清代那种村落自治机制里边,团练是应该灭掉的。中国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因为王朝并不能够真正保护民众,所以生民只能靠自救来建立基本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并不拒绝跟王朝共谋,或者说他们并不拒绝反过来利用王朝的权力,这是必须关注的重要一点。清代王朝允许各种乡村经济自治,但是它并不允许在政治上的结社结盟,为了共同体的有效运作,乡村最后演变出很复杂的官民共处机制。这种机制有的时候和王朝的行政系统是对抗的,有的时候是平行、井水不犯河水的,有的时候又是共谋的,就看它是否需要。
日本的情况则不同。前一阵跟几个日本学者连线讨论的时候,我谈到了中国社会的相互扶助,有一位比我年长的老先生说,
相互扶助这个词,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用过了,日本社会只是在战争时期用过这个词。现在我们所有的事情全部依赖国家,依赖社会相关行业,比如说保险公司。这番话让我联想到突发状态中中日社会的差别。
最典型的例子是地震。关西大地震,大阪和神户两个大城市在震中地带,一下子摧毁了很多人的生活,但是日本政府花了3天时间讨论要不要出动自卫队,结果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就被这么蹉跎了,民间也没有动作。中国的汶川大地震,政府行动很快,民间行动也很快,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有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关西大地震其实民间也有善举,不过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有捐款。在日本人的感觉里,灾难还得靠保险公司,没有保险的人,后来有不少自杀了。
也就是说,日本的相互扶助不是社会机制,它纯粹是一种个人的善举,依靠的是个人的伦理感觉。但是在中国,相互扶助不仅是善举,它首先是社会机制的重要部分,支撑着百姓的生存方式。特别是到了危机时刻,这个机制会最清晰地呈现出来。一直到今天它潜在地还有生命力,那是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直接相关的。
▍
生民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