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今天汶川映秀来了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我终于来到了唐山。在四十二年后。

今天很热,四十二年前的今天应该也很热。
热得人不想动弹。
刚才有个当地人跟我说,她当时经历过唐山大地震,虽然很小,但记忆犹新。
很多人不知道,唐山的南湖公园是人工建的,一大片在市区里的绿化,很突兀,外人不知道。这里以前是采煤的,地面下沉,于是——
于是那24万人就在唐山大地震之后被永远长眠在了这里,这下面是尸骨如山。

那剩下的活着的人呢?他们重组家庭,于是你会看到在这个城市里,有兄妹俩成婚的,因为他们虽然是兄妹,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当地人最后一再强调,别去南湖了,别去南湖了,那里阴气重。
叹气。

人是很奇怪的,人会不断地自我建构和解构一切事物,这些会在你的脑子里迅速完成,然后以你都没有发现的形式被表达出来。所以托尔斯泰晚年要离家出走,因为他要正确无误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所以在我来唐山之前,我对唐山大地震以及唐山大地震这四十二年来的想法,已经完成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
无论如何,我是总要来一趟的。

接下来,则是我在来到唐山大地震后想到的。人是很奇怪的,总是会想些和行动主线无关的内容,人的思绪飘忽不定,令狐冲会在千军万马之际突然想到小师妹在干什么,就是这个道理。
一年前的今天,我说过18年的05月12日和07月28日我一定要去一趟汶川和唐山,有朋友当时就跟我说到时肯定办不成,我忘记了我有没有回复,但我记得这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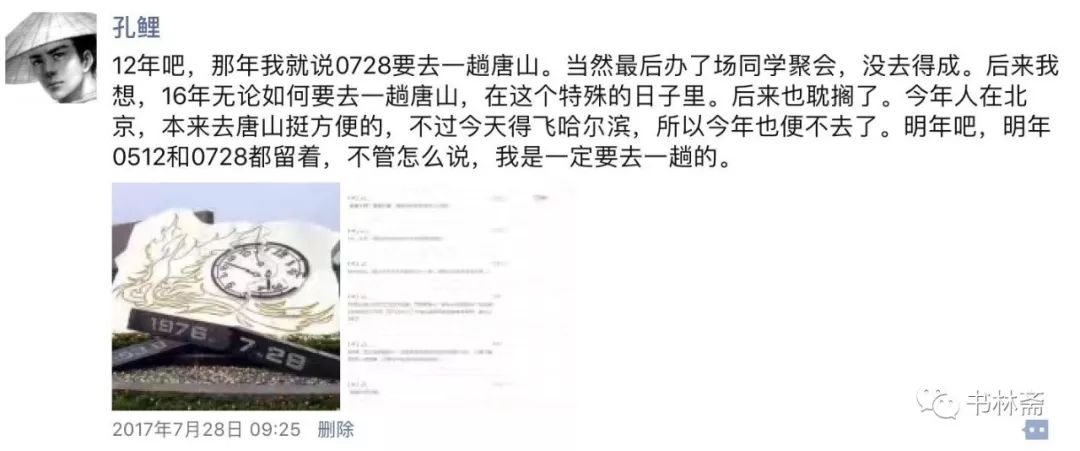
我更记得这样一句话: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如果我只是把去汶川和唐山当作一个闲暇无聊时的可选项目,那么不用想了,别说一年前了,一周前定下的计划都不一定能办成,但去汶川和唐山毕竟不是简简单单的游玩那么简单,我知道,我是总要去一趟的。
也许去了之后并不会有非常强烈的感受——事实上很多时候真的如此,当我拜墓时,由于对墓主人并不是充满着感情(比如明玉珍、巴蔓子等),可能更多只是带着学习的视角去看一看埋葬地点、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但是当你带着感情去的时候,精神意义就会强于其它,你会时时刻刻想着这件事,而它就会成为你心心念念的、会一直放在行程表里的事,最终促使你早早地就定下了。
原因无他,你对即将面对的,有了自我建构的充沛情感。这样的情感在不同的人面前是不同的,我记得很清楚的,有16年拜孔林、黄宗羲墓、王夫之墓、张巡墓、戴安澜墓、文天祥墓、海瑞墓、国殇墓园,有17年拜岳飞墓、于谦墓、张煌言墓、史可法墓、李春芳墓、福田公墓、万佛华侨陵园、列宁墓,还有18年拜顾炎武墓、李根源墓、瞿式耜墓、徐霞客墓、阎公祠、张自忠墓、秦良玉墓等。

我能立刻回忆起那时的思绪,那种大雨淋漓也要撑着伞走过去的冲动,那种山路崎岖也要满身泥泞爬过去的念头,那种路途遥远也要徒步几小时的执着。
我也能立刻回忆起当我到达目的地后,我的脑海中并不全然只剩下了眼前的事物——也许会让我心潮澎湃,也许会让我满目萧然,也许会让我无动于衷。——我可能在想,今天该吃什么呢,待会朋友圈要发什么呢,接下来行程是什么呢……什么念头都会有,就是很少会有和行动主线相关的。
因为这些行动主线早就在我出发前就确定下来了,我很早就知道我对文天祥是什么态度,我对阎应元是什么念头、顾诚对我有多重要……所以我过去,只是为了放下一块我已经知道形状的拼图。
就像我今天来到了唐山。四十二年过去,那时连我父母岁数都还很小,我更不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记忆连接点,不像去汶川就能迅速调动起十年前的画面和声音,对于唐山,我只是一个局外人。
唯二能让我不成为局外人的渠道:
一是把眼前的数目字换算成一个又一个人。
就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看到的万人坑那样,大家都有钝感,「24万人」带来的冲击恐怕比不上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任谁去国殇墓园都会动容。

只是这样的动容没法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费,这是有边际效应的,在有些动容上,你给了文天祥就没法再给史可法。
二是把那天构建到整个1976年里。
想到那年的01月08日,想到那年的07月06日,最后想到那年的09月09日,这样的构建持续影响到了今天,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是几个老人的逝世,那是无数人的离去。
在这样的告别中,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轰然倒塌,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无情碾过。

但毕竟是有四十二年的时间过去了,距离1986年钱刚写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也过去了32年时间,而我是在很久以后从父亲的书架上翻到了这本书,才知道了这回事。
那时我在想什么呢?
那时的我,目光全集中在《大自然警告过》这一章上,我惊奇于作者对地震前各种奇景的描述,我认为那是一种玄学,一种课本上一定不会讲起的玄学,于是我幻想自己也在1976年07月底的唐山,我瞪大双眼在看着那些怪事。
就像那时的人们一样,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人们是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而我则是因为觉得接下来的描述文字很不吸引我,而拒绝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有些事总会「蛮横」地冲撞到你的眼前,逼你不得不记住它,并且永远记住它。
记住那个告别了一整个时代的1976年,记住242769人。

我鞠了三躬,一个老奶奶看到了,问我给谁鞠躬呢,我想了想,说,所有的。
所以我写完这段话后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冷面好不好吃?
阅读原文处可查看文章集锦。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