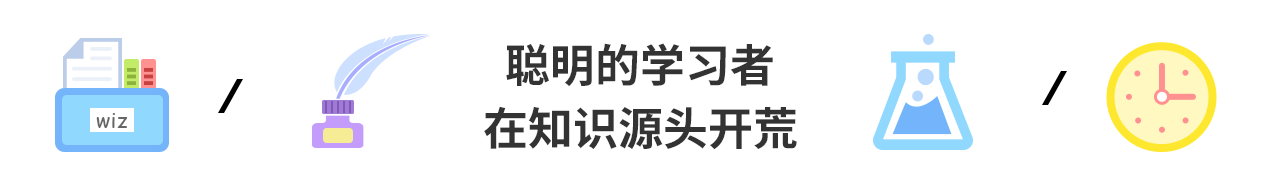
— Note170818003 —
认知写作教练雨明点评
:我从普通读者角度说说自己的感受吧。两处伏笔设计得精妙:为什么李老头不同意参加演出?那根长棍子是做什么用的?文艺晚会上的情节,点明了这两处伏笔。有一处我觉得是逆转的,本以为李老头上台一唱,立即技惊四座,掌声连连,结果却落了冷寂。你还写了另外一个人物,王立法,是想用他的困境来烘托李老头、或全村的普遍困境吗?

正文
远近都还笼着隐隐的黑纱,只有这一处院门廊亮着。橙色的白炽灯上卡着一圈不甚规整的纸板作为灯罩。光裸的灯泡在清晨的微风里晃着,光晕因年久而暗沉,藏着肉眼不易分辨的闪烁,闪烁着寒颤。
老李头已经起来了,蹲在院门口的水沟旁,呸呸吐着牙膏沫子。喝几口水漱一漱,抬胳膊在袖子上蹭一把,斑斑灰白的胡茬依旧像沾着白沫,抹不干净。
屋里没开灯,就着门廊的光依稀能辨个大概。桌上袋子里系着的半碗面条冷透了,昨夜带回来的。嗯着小调子,提到厨房倒进锅里热一热,回来蘸着馒头,吸溜吸溜吃。
老李头今年八十又三。黄土已经埋到脖子的年纪了,衣服上也总是粘着些尘土泥块。反正每天都是要干活的,洗不洗都一样。
同屋的王立发,是远房的远房侄子,说是来大城市奔前程,现在跟他住一块。王立发醒来堆开被子,从床板上坐起来,抓着头皮打呵欠,打完呵欠又抓了抓头皮。看着埋头一口馒头一口面的老李头:「还有吃的吗?」
老李头抬头看他,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小半块馒头,刚想递,就见王立发掸手:「去去去去!」
「老李头!」院门外有人喊。
咽下嘴里还没嚼的面,「诶!来了!」端起碗咕嘟咕嘟,扒拉两下,取过挂在门边的橙色褂子,馒头一口塞进嘴里,一边斜着身披褂子一边往门外奔去,差点撞在门框上。
门外的是工友,二人钻进光线晦涩的巷子里,七拐八拐来到大路上,一辆大卡车已经等在杨树下了。
等来等去,一行八人,坐进车斗里,车就颠颠上路了。众人倚着一簇一簇的带土移栽的雀舌黄杨苗,有继续瞌睡的,也有唠嗑打屁的。就老李头仰靠车头,闭眼嗯着调子。谁要是认真听的话,会发现,他这样嗯来嗯去,嗯上个几天几夜,调子不带重的。
老李头会嗯调子,同屋的王立发自是知道的,觉得这老头是牙疼没治,一天嗯到晚。烦的时候就怼他,怼到老头不吭声了;忙着打手机游戏的时候就随他嗯,有时嗯得还挺有那么点抑扬顿挫。但他从未想过,人家这嗯,还能给他嗯来钱,虽然只有五十块,够买一提烧鸡和一打啤酒了。
这一天老李头出门后,王立发抹了把脸也就出门了,是要去应聘四环上一个单位的保安。同村一个大哥给张罗的,叫他早点去,留个好印象。
去他妈的留个鬼印象。他到地儿的时候,门卫拦着不让进,说没招保安。那大哥也不接电话,报名字也没人知道他。才猜到,这大哥估计是瞎说的,借此搭话,蹭他两瓶酒、一碟肉。越想越气,气得鼓囊囊的,连饭都没吃就坐公交回来了。
到站,在村口买了几个包子回屋,刚要进门,就被等在门的村支书叫住了。说是县里下发文件,要大家响应中国梦的主题,组织精神文明建设。虚头巴脑的,放往常他才不会理,谁料村支书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说等不住了,让他转交给老李头,请他在下周的联欢晚会上出个节目。
「他能出啥?」王立发马上接过钱。
「你不知道吧,老头子会唱戏,去年我跟他一路坐车去市区,那调子就是唱戏。」
「那我也去唱两首歌,也给我发钱不?」王立发笑。村支书叫他拉到吧,叮嘱电话联系,走了。王立发拐脚去了不远处的小卖部,称了半斤猪头肉,拎了一瓶酒。
老李头回来后,王立发跟他提了,老李头摇头说不去。
后来两天夜里村支书来磨了两次,老李头总是咧嘴笑着摇头,慷慨地笑出牙花子给人家看。只是右上边缺了一颗牙,黑洞洞太招眼,人要是也冲他笑,那应该是笑他的牙豁。
磨不过,村支书要拿回五十块演出费,王立发躲出去了,老李头搓着手,看看他,又看看自己的脚尖。解放鞋,结着土,面上看上去还成,底下已经开胶了。
王立发半夜里回来,发现厕所的地漏堵了。回屋里找到一支一次性筷子,短。继续找,从老李头的床底下箱子里翻出一根细长的木棍子。刚去捅了两下,就被转醒、跟进厕所的老李头喝住了,劈手夺过去。
「嚷什么嚷!破木棍子有鬼用,还当宝贝了,带坟里去啊!」
老李头原本还在查看木棍上的折裂,听到这话,抬起头仰看着面前这个挡了光源的年青人,又高又壮。像是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枯瘦,两片嘴皮嗫嚅着蠕动了两下,什么都没说出来。
村口大杨树下,文艺晚会如期举行,先是几个小朋友在大树底下又唱又跳,表演完后还喘着气,几人分了一袋糖。再是村支书念红头文件,底下坐着的几十村民频频去厕所,但到底没敢全走。再然后村长讲话,没敢走的基本上都在坐着打瞌睡了。以至于老李头搬着他的木箱子到树下的时候,场下十几人是一片茫然和昏昏欲睡。
牛筋琴往倒绷着带子的凳腿中央放,旁边挂鼓面。他在杨树下弯腰又起身,终于摆弄好了。右手执那支开裂的鼓签,左手三粒板,“啪”地一声脆响,全场醒神。
「诸位 / 看官,」一开调,便是古腔,「小生 / 李当先 / 字自勇。今 / 应邀 / 而来。在此 / 献丑……」
村里没人听过这个。老李头是南方人,唱的是词评,古南国方言。守在村里,又不敢提前溜走的村民,大多是不识几个字的老实人,更别说古言了。
不过光听着还是挺热闹的。豁牙带点漏风,平添喜感。只见老李头摇头晃脑咿咿呀呀,方腔圆调唱过一段之后,咚一声鼓面,仿佛被人附了身,插着腰、粗着嗓子开始念白。一会儿又细着嗓子,捏着兰花指,在耳畔挽了一下,像是有一缕长发凭空别在了耳后。一会儿又呜呜咽咽,似在哭哭啼啼……最后牛筋琴弦敲得一阵紧似一阵,鼓边脆响,三粒板旋即接上……
有谁猜得到,这段唱的是吕布戏貂蝉。董卓吕布兵刃相向、你死我活。而后一直连着唱。牛筋琴的筋松弛了,敲出的音带着点软绵绵的迟滞。一本三国演义,从头到尾,完完本本,款款叙叙。
刚开始村民还看个新鲜,后来连村长、支书都回家睡觉了,大家就陆续回去了。老李头晃若未觉,嗓音杂了一把沙子,听着反而更不紧不慢了。琴也不敲了,鼓也不点了,手里握着三粒板,就这么唱着,咿咿呀呀。
唱完最后一个音,老李头摸了摸鼓签上的裂纹,收进了箱子。
将箱子搬回屋里、放回床底下的时候,对面铺位的王立发翻了个身,咯吱咯吱磨着牙。老李头坐了一会儿,起身去厨房喝水,然后煮饭。
四下唯有这厨房点着一盏小灯,白惨惨的。门外簇拥着黑夜,能瞧清的只有弦月如丝,飘在树梢。树影幢幢,掩着公路。路的尽头,无限延伸着,隐没在天际。
接植树工人的大卡车该在路上了吧。
- The End -
↓↓↓
戳原文,预约认知写作学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