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一个“妈宝男”在妻子身边觉醒自我意识时,母亲与妻子战争就开始了,然而,两个女人的拉扯足以撕裂一个男人,也足以毁灭一个家庭。
作者通过非常文学化的语言描写了母亲的心理感受,站在母亲视角审视家庭战争之后的遍地残骸。
世间有太多残害以爱为名。
然而,在母亲的视角背后,读者又能隐约看到一个懦弱、自私、不负责的儿子,他没办法完成从儿子到男人的身份转化。
雪崩来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
编者按
🕔
>>>
桑母缓缓走进这个寂静的小区,小区的门照例东倒西歪着,像极了她东倒西歪的步伐。看门人似乎永远不会从收发室里醒来,在这初春的院落门口,执意和里面的一切寂静的冬眠。
踏进这里的一瞬间,桑母就后悔了,之前走在一片春意的向阳街道的时候,她步履如风,矫健异常,她原本就是这样,五十多岁的年纪,硬朗的身体,火爆的脾气,她做什么都那么果决干脆,除了走进这里的时候,哪怕是接近大门,她都明显感觉自己瞬间老了十岁,蹒跚着,蜿蜒着,好像一条准备入穴冬眠的蛇。
这个小区的街道也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蛇,穿梭在贫瘠的杂草间,匍匐上怀抱干涸倒影的小桥,桥对面枯萎的树木张牙舞爪着,像漆黑的触角,又像蛇吐信的血吻。桑母走在蛇背上,感觉自己只是这蛇的子嗣,她必须摇晃起来,必须弓背匍匐,才能不惊动脚下母亲那潜伏的敌意。
这个小区终究还是败下阵来,如同她即将看望的儿子,她不禁回忆起儿子新婚不久乔迁新居的那段日子,一切都是喜气洋洋、欣欣向荣的,连同这原本花团锦簇的院落,昭示着美好的生活。

直到命运突转,直到娟子的离家出走,直到黔驴技穷的业主们放弃了对小区的奢望,直到一切都迎来冬眠。仿佛一段梦的消逝,从此之后,院落、家庭、爱情、理想、未来,所有一切,虚无或实体,都兴高采烈的落井下石。
桑母继续蹒跚着,虽然即将进入的那个单元门洞她已曾进入过无数次,但她还是假装迷失在蜿蜒觅食的蛇背上,她需要时间,她已经尽量拉长了那时间,还是需要继续拼命拉长。
不可否认,她爱自己的儿子,那种爱早已超越了理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越要蹒跚,因为她不想看到那个门洞里、那个房门后,所发生的一切。
终于,在漫长的冬眠里,她还是不得不苏醒过来,她的抵抗在看到404号房门旁的信箱时彻底归于失败。
她曾无数次面对这个信箱叹息,这个自从儿子溃败进房门以后就开始与众不同的信箱,虽然破旧,但是阔绰,活像个一夜暴富的土财主。土财主那里永远堆放着内容相同的信件,并且与日俱增。桑母感觉自己是这信箱的奴隶,她必须满足它,像个顺从的奴仆,但她无从抱怨,这都是自作自受。
404号门内的寂静让她有点担心,她宁愿听见那个人的痛哭、谩骂,甚或嘶吼,那至少代表门里还存在着些许生气。
她颤抖着伸手拿出钥匙,那生了锈的钥匙面对的仿佛是一个随时会被点燃的引信,只要她稍一用力,可怕的房门就会随之爆炸,展现出不忍卒视的现实。
所以她闭上眼,无声的转动手中的火柴,直到房门被打开,直到引信无声熄灭,她才颤巍巍的睁开双眼。
房间里昏暗异常,从玄关可以直接望到那唯一的卧室拉着窗帘的尽头,在有些微光亮洒下的书桌上,匍匐着一个巨大的看不清轮廓的身影,那臃肿身影不时发出微弱的絮语,让桑母逐渐放下心来。
她驾轻就熟的打开了玄关昏暗的灯,轻手轻脚走进卧室,臃肿的身影条件反射似的动了一下,并没有做出更多反应。她看着这个代表自己儿子的臃肿存在,像一个裹在破衣烂衫里的肉团,在老旧发霉的桌椅间缓慢的颤动。
冬季的苍凉早已蔓延到肉团的全身、鬓发,即便时间已是初春,顽固的衰老终究不肯做出让步,那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抵抗,桑母明白,她和她的儿子,始终在四季的流逝中悲伤的冬眠,他们是时间的死敌,现实的仇人,虽然屡战屡败,仍要屡败屡战。

此时她的儿子仍然在做着自己一成不变的事情,带着无可置疑的专注,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鬼祟。如果这狭小的卧室就是牢笼,那么他无疑是一只老鼠,他努力匍匐着,紧按住面前的那张纸,颤动的前爪在纸张间挥舞,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能无思无畏,将眼前的纸张当做最后的奶酪,即便背后的危险已近在咫尺,即便生命将迎来尽头,他也不会离开。
桑母默默打开卧室的灯,老鼠厌恶的发出一阵混浊的咕噜声,面前纸张的沙沙声迟疑片刻又重新作响,老鼠皱了皱眉毛,爪中原子笔在愤怒的一划中,结束了腾挪。
桑母似乎在那纸笔间看到了生命的火花,瞬间感到一丝安慰,她无视掉满地的废纸卷和犹如杂乱荒原的房间,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后颈,把手里的食盒放到了桌子上。
任何事情都无法对抗美食,何况是牢笼之中饥饿的动物,他们拥有珍惜生命的本能,桑母深信这一点。当她的儿子开始醉心于食盒里的晚餐,桑母轻轻拿起桌上那张纸,她并不好奇纸张上的内容,但还是照例看了看,上面的事物扭曲、暴躁、纷乱,如果可以算是字迹,那么它的前生一定是一群失去了生计的蝇虫,在看似洁白的慌张里横冲直撞,发泄着愤懑、绝望和自欺欺人。
“我的娟子:
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的我,也只能继续的说对不起,怎样才能让你原谅我,让我接你回家,我盼着那个时候,盼着你的回信,你一定会原谅我,让我去接你,对吧?我会一直等你,随时随地,我爱你,永远。 你的丈夫阿伦。”
桑母看着这张纸,她几乎每次来都会看到同样一张纸,上面的内容千篇一律,毫无新意,因此即便难于辨认,桑母还是能够在纸上那漆黑而无序的神经末梢中感受到来自记忆的触觉。

那时候,她还住在这个地方,和她的儿子、儿媳住在一起,新婚的幸福让两个年轻人每天都喜上眉梢,她也曾如此替他们高兴,努力挤出自己所能挤出的全部精神和气力,维护着这喜悦。
一切都是和谐美满的,直到命运突转,所有事情在不易察觉的丝丝寒意里迎来彻骨的冬季。那段幸福时光的逝去,一开始还没能引起她足够的警觉,那不过是每个家庭里见怪不怪的争吵,为了种种鸡毛蒜皮的琐事,为了无穷的说教与被说教,为了全中国人民都无法分解的婆媳矛盾,儿媳摔门而去,离开了家,儿子为了母亲的颜面驻足观望,直到灾难无可挽回,直到看似互不相干的一切,虚无或实体,都兴高采烈的落井下石。
桑母看着眼前愤怒扩张的漆黑触角,在苍白里肆意蠕动,不禁联想到了院子里那些枯萎的枝叉,联想到娟子,离开这里时那放肆的身影,她的身影带着漆黑的触角远去不回,将洁白的往昔无情割碎。
桑母眨了眨眼,颤抖着拿起桌角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的触角同样漆黑,和手中白纸抒发着如出一辙的绝望。桑母的目光只在“曲娟收”三个字间一扫而过,便匆匆收回,深怕多停留一会儿,就会被痛苦灼伤。

她并不担心收信人的地址会弄错,因为那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现在,她只想尽快离开这早已被触角织成牢笼的地方,然后将支撑着笼中老鼠生命的信件送到她该送的地方。
她知道那地方在哪里,虽然有时候也在悔恨和恍惚中变得有点不确定,或许是在某个空洞的烂尾楼里,或许是在某个不负责任的邮差的抽屉里,更多则是在门外那个她极端厌恶的高傲信箱里。
总之,这一切的归处,都与娟子毫不相干,她深知这一点。她的儿媳是个不愿回家的妻子,但她并不怪她,大概早在很久以前,她就忘记了对娟子的所有怨恨,也不用再思考娟子对于这个家的怨恨,那种感情早已成了一个虚无的符号,成了一片吸附在洁白记忆里的漆黑触角,扼杀着她最后的一点悲哀,却也挽救着她儿子残存不多的生命。
桑母无声走出这座牢笼,并不想多回头看一眼牢笼里的老鼠,那个温顺的小东西,从他的出生开始就是那么温顺乖巧,从不愿违背母亲的一点意愿,所以当母亲为了他的安全将牢笼筑起,他便安然匍匐在黑暗里,跑动在用洁白的纸张和漆黑的触角构筑成的滚轮中,矫健冲向生命的轮回,仿佛时间,早已凝固。
桑母经过门前的土财主时下意识看了一眼,她曾有一瞬间犹豫过,是否应该将手里的信封直接放进里面,但旋即放弃了。这不单是因为走捷径会带来对于仪式感的破坏,更多因为,这会让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在这里放下信封的情景。
那时候自己的儿子还不曾安然于牢笼,他从现实的牢狱里走出,却失陷在心灵的围城里,他的躁动、嘶鸣、绝望,像一只无所遁形的老鼠,让她恐惧,让她无法理智的预测一只看不到希望的饥饿老鼠,如何温顺的奔跑进自己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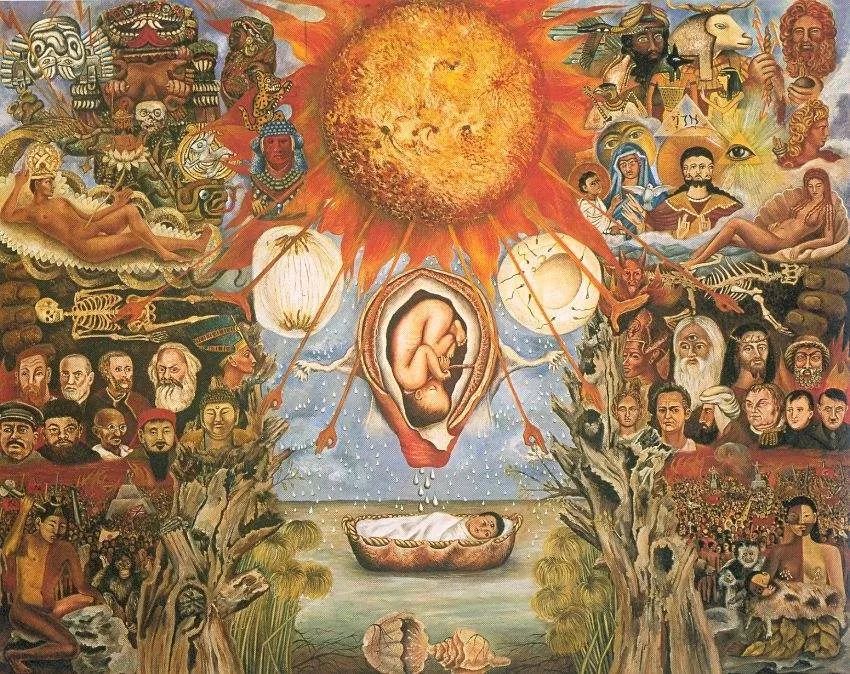
所以她放下了那个信封,一封用离家妻子的口吻写给她失和丈夫的信。在信里,叫曲娟的妻子对叫桑伦的丈夫进行了有板有眼的口诛笔伐,她那令人刻骨铭心的横眉立目、趾高气扬透过薄薄几张信纸喷薄而出。
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早已离家,即便丈夫经历了可耻的牢狱,她仍未曾忘怀对他的爱与恨,因而愿意将如此激烈的情感挥洒在字里行间,愿意留给她绝望的丈夫一丝改过自新的曙光。
桑母很庆幸自己能够通过放下一封信而让生活的奇迹在冬天里绽放。从此以后,老鼠寻到了带动他虚弱生命的齿轮,而信箱也迎来了它的富足和春天,两者得以在彼此的循环里相依为命,难舍难离。
桑母终究还是离开了,将老鼠和信箱继续保存在寂静的冬眠里。她失魂落魄的将手里的信封放进衣袋,和它的同类紧紧挨在一起。
她拼命的走着,感觉自己走在一条没有分叉的锁链上,那是身后牢笼的生命线,牵着信封即将走向的地方。她很害怕锁链指向的另一个尽头,到底多久不曾走去那里,已记不清楚。但是今天,她要去一次,为了这悲伤的日子,和娟子,说一会儿话。
这是一个阳光很不愿意光顾的地方,有着娇纵的杂草,泼辣的野花,和不近人情的冷厉。除此之外,就是一排排矗立在风中的幽影,他们整齐划一,仿佛一座座映照灵魂的梳妆台,每个黑亮的镜面都透着诡谲。
桑母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她无法面对那些镜子,那些镜子从来照不出你的喜怒哀乐,除了丑恶的灵魂。可是今天,她还是来了,她蹒跚着,摸索着,直到发现那座野花围绕的镜子,她重重跌坐进尘埃里,耳朵在寒风的吼叫中嗡鸣,那是灵魂的号叫么?还是汽车轮胎尖锐的摩擦声?桑母无法将声音从脑中祛除,它们在这血色蔷薇的包围下,是如此的鲜活生动!

就在来的路上,桑母不得不走过一座烂尾楼,那似乎是命运锁链上的必经之路。她看到那粗犷、空洞、遗弃已久的巨人的时候,被一个莽撞邮差伸手拦住。“老太太,您知道这信上的地址在哪里么?我找了半天,只看到这座废弃大楼,总不会有人往这里寄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