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
王芊霓
采访 l
王芊霓
葛诗凡
来源 l
芊霓的咖啡馆
(ID:
hibetterni
)
分享 l 粥左罗的好奇心(ID:fangdushe007)
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关于“内卷”的讨论,但大多比较浮于表面,变成了吐槽或者抱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深度访谈。人类学家项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内卷”进行了细致易懂的阐述。
2020年,可能没有第二个人类学术语比“内卷”更加出圈了,它本来是人类学家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的概念发明。
现在,“内卷”则意味着“恶性竞争”,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取少量竞争优势,挤占他人的生存空间,同时造成精神内耗和浪费。
人们可以在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识别出内卷,可以说是从幼儿园一路“卷”到职场、连婚恋也可以“卷到天上去”。
我们请到了人类学家项飙来谈内卷,今天的内卷和它在被发明之初的含义有什么区别?我们又如何描述当代生活中的内卷?
项飙非常擅长使用比喻和日常观察来深化和细化我们对于概念的理解。他把内卷描述为一种“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他更是站在人类学视野下竞争的大框架内理解“内卷”,指出
内卷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例外现象,它的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缺乏退出机制的竞争。
项飙还分享了一些如何缓解内卷焦虑的思维方式,人类学家是如何通过“想细”和“想开”来面对日常生活的困顿和焦躁的?
 ▲项飙 图源:腾讯视频《十三邀》
▲项飙 图源:腾讯视频《十三邀》
今天的内卷
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
王芊霓:
内卷最开始就是人类学家用的术语,格尔茨先在他的研究里用到,然后杜赞奇也有个术语叫政权内卷化,所以我觉得我们请一位人类学家来谈内卷来澄清这个概念,是非常合适的。
内卷的英文是involute,我查到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科普,说内卷这个词源是描述贝壳,有一种贝壳的尖尖是会伸出来的,而内卷的贝壳,它不是往外长的,它是在内部越来越卷,有很多的构造,但是你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来这些弯弯绕绕的构造。
项飙:
内卷这个概念最早是格尔兹通过对爪哇岛的农业经济的总结里面提出来。他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农耕社会长期没有大的突破。
农耕经济是越来越精细化的,在每个(土地)单位上投入的人力越来越多,我们可能会想象说投入的人力越多,你的产出也会是高的,可实际上这一点的提高,因为人力多投入而增加的产出,就也只够人力本身的消费了,就是说你多了一张嘴就被这张嘴消费了,如此而已。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平衡状态,多少年一直如此。
为什么叫内卷?
是说你在耕作的时候,大家对每一个细节都越来越关注,可是到最后产出跟你投入的关系是没有变化的,甚至是负增长。
如果你要到一个荒野上去开垦荒地,粗放地耕种,其实你的产出和投入的比例反而是更高。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北大孙立平教授就说,你看中国农民,他们种田跟种花一样。精耕细作这四个字,是对亚洲农业很好的概括。
后来黄宗智在对于长江三角洲的及农业经济的发展,他把内卷的概念引到了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史的分析,他的分析跟Mark Elvins“高水平陷阱”的意思,基本上是相通的。
“高水平陷阱”是说,中国在很早就在农业技术、行政管理,还有社会组织、人力动员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它达到高水平之后一直就没有突破。农业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就没有变化。
Mark Elvins的解释是指在17世纪以后,中国基本上开垦了所有能开垦的土地,土地没有增长,但是人口一直在增长。人口的增长靠什么来维持?主要就是靠精耕细作,靠这种非常内卷的方式。

人口增长是跟文化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文化是要多子多福,然后人口的增长倒过来就使得人力变得非常便宜,所以没有技术创新的动力,觉得有事儿就是靠人力。
这是中国农业跟欧洲农业很大的一个差别。
比如说,扁担在欧洲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你找不到扁担这个东西,而中国在任何农业家庭里都有扁担。在欧洲所有重的活都是动物做的,很少需要人做,然后欧洲后来就是说要蒸汽,要机械,就是说靠自然的物理的能源来解决。
杜赞奇把内卷的概念转化为行政和政治上。他是要解释在清朝末年的新政,要加强国家的控制,所以它要建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国家投入了很多钱,建立官僚机构,但是国家基层的行政能力并没有增强,对这个地方社会的服务没有增强。这是国家建设中的内卷。
这导致什么后果?它有了那么多的官吏,就不得不从农民那里汲取更多的税务来养这些管理人员。但这些官吏很快就变成拿了工资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农村社会服务。最后导致了农村社会的解体和革命,因为攫取越来越多,但是没有反馈。
王芊霓:
这几位学者讲的内卷似乎和今天我们谈内卷的语境很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
项飙:
这两位学者谈的内卷和今天讲的内卷在主观感觉上都是没有突破,走进死胡同,但是它的运行机制是很不一样的。
从格尔兹、黄宗智、 Mark Elvin来看,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缺乏经济意义上的竞争。因为它的目标是为了家庭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然后就是要多养孩子,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没有工业化,没有资本主义。
在人类学里面,内卷是解释为什么这个社会运行没有出现一个大的突破,没有从一个量的积累变成一个质的突破,特别是说没有从一个农耕社会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
这跟我们今天讲的内卷是相反的。
现在大家讲的内卷是指竞争的白热化。
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卷到底是怎么回事。内卷这个词还是很直观的,它显然反映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王芊霓:
中国社科院的杨可研究员有一篇论文叫《母职的经纪人化》,就是讲妈妈慢慢的变成了孩子的经纪人,她也提到母职的内卷化,就是妈妈会在一个孩子身上越做越多。
我当时还不理解,去年我也做了母亲,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妈妈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无穷无尽,越做越多越做越多,比如说我比另外一个妈妈要花的时间更多,给孩子的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给他护理抹油,脸上抹的跟身上抹的不一样,身上抹的跟屁股上抹的又不一样,总之就是特别精细。这种内卷您觉得它有意义吗?
还有一个就是在母职上用这个词儿是否可以?我的意思是现在内卷这个词已经非常的泛化,它更多的是一个贬义,是一种对社会的吐槽,您能不能用一句话讲,就是说大家现在的用法的主要错误在哪儿,或者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用这个词儿,有没有这种分界或是澄清?
项飙:
用词是个社会现象,如果大家觉得内卷这个词表达了他们的焦虑,应该是我们(学者)认真听大家的,然后去分析,不是说告诉你们不能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是帮助大家去界定内卷究竟是什么,跟历史上的用法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的母职内卷,大概是两点。
一个当然是投入的不断增加,无限的增加;第二个是很强的走进死胡同的意思,走进死胡同就是说不知道哪里是终结,然后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究竟能够带来什么产出,但是又觉得停不下来。
这个死胡同是自己循环的一个死胡同,跳不出来了,是走进一个死循环,可能是内卷是一个死循环的意思,而且是个很消耗精力的死循环。
在中国语境下面,
你为什么会走进这么一个高度耗能的死胡同和死循环里?
当然是来自于这个
群体压力
,因为别的母亲都在那么做,是来自一个群体压力,所以这里就带着有一种有意的或者无意识的竞争或者攀比在里头,这可能是一个背景和语境。

你要把它叫做内卷,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要跟原来讲的内卷做一个比较,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了。
传统上谈内卷是说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高水平陷阱,一代重复一代,从17世纪以后没有竞争,大家都只是维持糊口的水平。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死循环的陷阱,你不是每天都在重复你的工作,
你在不断发现新的抹油和辅食的品种,成天在微信群里面看别人在用的最新的东西,你如果重复的话,你心里就很慌。
而且孩子不断长大,选幼儿园就开始烦,然后到了小学就纠结,然后到小升初的时候,就是快逼疯的时候了。这个当然跟农耕社会里边的高水平相结合不一样。
如果说原来内卷指的是一个重复的,没有竞争的,不能摆脱农耕社会这么一个结构性格局,今天的内卷是一个陀螺式的死循环,我们要不断的要抽打自己,让自己就这么空转,每天要不断地自己动员自己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所以非常耗能的。
在小农社会里面,你体力上很累,但是不会有这种在精神上的这种折磨的。
传统上我们对祖先的崇拜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重复。所以不肖子孙的“肖”,是说你不“像”,没有能力去重复你原来祖先的工作,你的重复能力是最重要的。
而今天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养孩子的方式一定要跟我们父母养孩子的方式不一样,对吧?这个也是现在中国家庭教育的一个特色,不断的教育孩子,你长大了千万不要跟你爸爸一样。
所以它这个是另外一种陷阱,要不断的超越,是奥林匹克,要更高更快更强。
内卷背后:高度一体化的竞争
王芊霓/葛诗凡:
内卷现在这个词这么火,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互联网大厂程序员,都在吐槽工作“太卷了”,或者是我要去银行或者其他好的单位应聘,
然后笔试题目也只是为了让我在竞争中比别人强(为了竞争而竞争),它考察的内容本身跟我的工作内容可能没什么关系,最后大家很无奈地用内卷讽刺这个现象。
我想确定一下您的意思,我们当下在谈内卷的时候,其实是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对吗?
比如大家可能一边在拼命加班,一边在社交媒体上去吐槽996的文化,我们也注意到特别是90后95后的年轻人,其实对大的社会结构他们是已经意识到了,并且特别要去想象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方式。
项飙:
在职场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内卷是用来对现在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太宽泛了,不太精确,因为资本主义最早起源的地方,比方说英国,然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可能是德国,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这种“内卷”现象,所以它是有一点中国特色的。
内卷背后,可能指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生活和资源分配方式的原则。
首先当然是市场竞争。但是很多竞争其实不是市场性的,比方说教育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市场性的,考试这些都是国家或者学校设定的。但是他会模拟市场竞争,把这个东西搞成像市场竞争一样,让大家来参与。
然后“高度一体化”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的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不分化,是
全国14亿人民都认准一个目标,为同一个唯一的目标活着。
否则的话,如果你在职场不高兴,你去干点别的,开个面馆不行吗?不可以,大家一定要挤在一个道上。

比如大家现在对“三和日结工”其实是有一种恐惧的,就是说你怎么就这样退出竞争了,这个怎么行?
在中国,大家面临的压力不仅是说你要往上走,而且不允许你往下走。
最近一位读了研究生的同学告诉我,他去麦当劳应聘,麦当劳看了他的学历之后,第一句话就问你有没有考虑你父母怎么想。
这句话是问得很重的,不是说你这个书都白读了,学费都白交了,直接是牵涉到情感问题和道德问题,好像是一种背叛。就是说你要把自己的社会阶层往下走,是个道德意义上的背叛,到了这个程度。
全国人民朝着一个目标去,要多赚钱,买一百多平的房子,要买车,一定要成家,一定年龄做一定的事情等等。这个线是规划的非常好的,大家高度一体化,都要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争夺一样东西,是高度一体的。
王芊霓:
一体化的意思其实就是单一对吗?就是跟多元对立?
项飙:
是说在
目标上的高度单一,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
,然后
竞争方式也是高度单一
,比如说都是考试的,然后
奖惩方式也是高度单一
的,奖金或者怎么样。
从人类学来讲,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在其他社会,特别在原始社会里面,有没有竞争?是有的。但是原来我们在很多社会里面的竞争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社会生活经常分成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声望部门,另一个部门是生存部门。
生存部门指打猎种田,在这个部门,大家一般不太竞争,而是合作,让大家吃饱饭。但是这个社会里是有竞争的,谁和谁竞争呢?一般就是说头人,部落的头人或者说家族的首领,一般都是男性,这些人跟其他村里的头是有一种竞争关系的。
他们要竞争什么?他要竞争的是一个声望。所以在声望部门里面是竞争。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散财宴”,头人把积累的财富分给大家,或者把自己的财富当众销毁,通过这个方式来竞争他的声望。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这种头人对声望的竞争,跟再分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获得声望的方式是把自己的财富重新分给大家,所以声望竞争是物质上的重新再分配,最后达到一种均衡。
但是在生存方面是不竞争的,这里的安排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每个人的守猎能力有高低,比如你能够打到一只鹿,大家在声望上都会认可你的,赞扬你的勇敢以及打猎技巧,但是肉是一定要平均分配的。中国的情况是,现在像这样的分化没有了,通通就是要竞争。
王芊霓/葛诗凡:
您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面也谈到了,富有的人想要更富,同时也没有再分配的愿望,我们不存在这样的分化,每一个阶层都有他的焦虑。
底层的人还是希望能通过教育达到阶层的提升,中产阶层可能在想,是不是我再努把力就可以成为精英,我的孩子是不是就可以去常青藤,就可以读金融,去投行去华尔街工作。
然后精英的人更不想下来,然后的孩子肯定要去学艺术或者是其他什么,他们也有他们标榜自己的身份跟品位的一个办法,也没有去再分配的意愿,现状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很着急,无论你属于什么阶层,好像都很害怕,这就是您之前说的末班车心态吧,我在想这个末班车心态是不是在每个阶层都存在?
项飙:
对,问题是现在末班车都过了。一体化竞争从90年代就开始了,为什么现在大家提出所谓内卷这个问题?是
因为末班车过了,底层还是希望能改变命运,但是中层和高层不是说继续往上走,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不要掉下来,不再等下一班末班车了,就想这班车不能停,而且我的世世代代都不能停。
得到的不能再失去,这可能是更大的恐惧。
如果真有希望在,大家不会造成一种这么高度的内卷。 “985废物”这里谈的不是说学得很累,而是说上了985没用。所以内卷是想表达,我参与了那么多竞争以后,连最基本的期望都没有达到。
所以刚才你提到的几点就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横向的分化。
比如德国很强调学徒工制度,学徒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业方式。在德国我去理发,理发之前我有点忐忑,因为我们亚洲的发质跟欧洲的发质很不一样,不知道理发师能不能处理。结果理得非常好,是我理过的话里面我最满意的一次,而且理发师也很投入很高兴。
我的假设是,在德国,理发师很早就当作一个学徒工来培养的,理发就是他的事业,很上心。不是说在亚洲,读书读不出来了,没办法了,开个理发馆谋生,从此不参加同学会了。
我们的竞争不允许失败和退出
王芊霓:
您刚才说末班车已经过了,我不是特别确定,可能这个也确实是一个争议的点。
一方的观点会认为末班车没有过,所以教育的竞争才会这么紧张,还有机会,所以家长才会在孩子的教育上如此投入,比如大家去买学区房,或者是要拼命的去面试,送孩子去最好的私立学校等等,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为孩子争取到一个名额,一切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也有一种看法,可能就是像您说的末班车已经过了,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这么这么的内卷?或者是这么这么的批判,对这个现状。 您觉得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定性,还是说在社会的不同层面,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项飙:
当然这是一个很粗浅的隐喻,如果末班车指的是集体性的上升流动渠道,我认为基本上末班车已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空间基本上不太存在了。大家现在挣扎只是说在结构里面找个缝隙。
你刚才讲到的这种非常极端的例子,他不是说在等着末班车,他其实是在末班车后面跑,所以变得很极端。比如你说的“为了给孩子拿到入学资格跟校长睡觉”这种社会新闻,它说明结构性的空间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必须要依靠非常个体化的极端行为去找裂缝,没有裂缝也去钻出一个缝来。
如果说大家都意识到已经没有末班车了,那不大家都不会安生了吗?情况不会这么简单,这里就重新回到分化这个问题。
如果看一些比较成熟的社会,为什么大家相对安生了?
大家安生了并不是因为说大家知道没有希望了,而是说把你的希望你的努力重新分配。
你看到自己的特长,看到自己的兴趣,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渠道,活得好的方式也是很不一样的。
大家各自去找渠道,这样的情况下会有安生。
他并不是说努力没有用了,而是说大家还是要努力,但是努力的方式不一样,你找出自己的途径来。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末班车过了,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开出新的小道来。
所谓内卷性不仅仅是说竞争激烈不激烈的问题,而是说,明明知道最后的收获也没有什么,大家还是要竞争。不知道除了竞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值得去生活。如果你退出竞争的话,你有道德压力。
王芊霓:
我想接着退出竞争再聊一聊,您观察到中国社会的竞争几乎不允许退出?
项飙:
现在
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
刚才讲到我那位同学要去麦当劳工作,面试官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父母怎么想?你要往下走,要退出竞争,过自己的生活,你面对的道德压力是非常大的。
现在对三和青年的各种讨论背后也是有一种焦虑,就觉得这些人怎么就这样退出竞争了。因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所以,成功者要失败者一定要承认自己是失败的。
你不仅是在钱上少一点,物质生活上差一点,而且你一定要在道德上低头,一定要去承认你是没有什么用的,是失败的。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失败,而是悄然走开退出竞争,不允许的,会有很多指责。所以现在能够退出竞争的人是非常富有的人,孩子送到国外去或者是怎么样。
有退出这个机制很重要。就是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孩子上学不好,让他有别的好的出路。学校教育应该要涉及到这一块,所谓教育家是说培养一个公共教育体制,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快乐,都能够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个不容易。
王芊霓/葛诗凡:
最近是有一篇叫《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文章比较受关注,是说在清北这样的高校里面,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了成长,同伴之间彼此PK,然后精疲力竭。
在古典教育中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认识自己,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用教育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一种惯性思维。然后学生因内卷而迷茫,老师又因为找不到潜心治学的学生而感到苦恼,是以这两所高校的绩点为王的这种现象,来去引出了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可能跟您当时在北大的读书时候是非常不一样了,您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项飙:
绩点为王,精打细算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讲不完全是陌生的。1990年到1991年,我们在一年军训的时候,一点点的绩点,也被看得很大。这里是不是一个竞争问题,是不是你在跟别人的PK问题?
不是的。
你真正要的是让权威认可你,是一个取悦。
这种取悦倒过来当然会影响你和你同学之间的关系。
竞争不完全是一个水平的,是双边关系的。
竞争从来都是一个三角关系,因为竞争它需要一个第三方来确定。
在最普遍的模型里面,比方说像体育竞争,当然你需要一个第三方,一个裁判,或者说一个经济的集团社团,来确定竞争规则。这个就是第三方。
今天我们同学和同学之间的竞争,其实完全是由第三方来控制的。我们原来认为竞争是因为资源有限,是因为所谓供给需求关系不均衡。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村长的话,如果我今天发明出一种方法,让所有的人互相竞争,最高的奖赏是我对他的认可,这样我作为一个村长是不是非常舒服?
所谓的短缺,都是人为的。什么样是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东西是有体面的,这不都是人造的?
这种竞争导致一种非常高度的整合能力,就是把
所有的人都统一思想,所有的人一起消耗精力和生命,也不想别的,让大家就是这么的忙碌着。
竞争不要仅仅理解为资源有限,所谓资源有限性,是一种手段。大学里有所谓发表的竞争和压力等等,真正的能够上去的人,他真的是靠发表的?
不是的。为什么”青椒”会有那么多发表压力,彼此竞争?理解竞争一定要理解三角关系。不一样的三角关系,导致竞争的含义是很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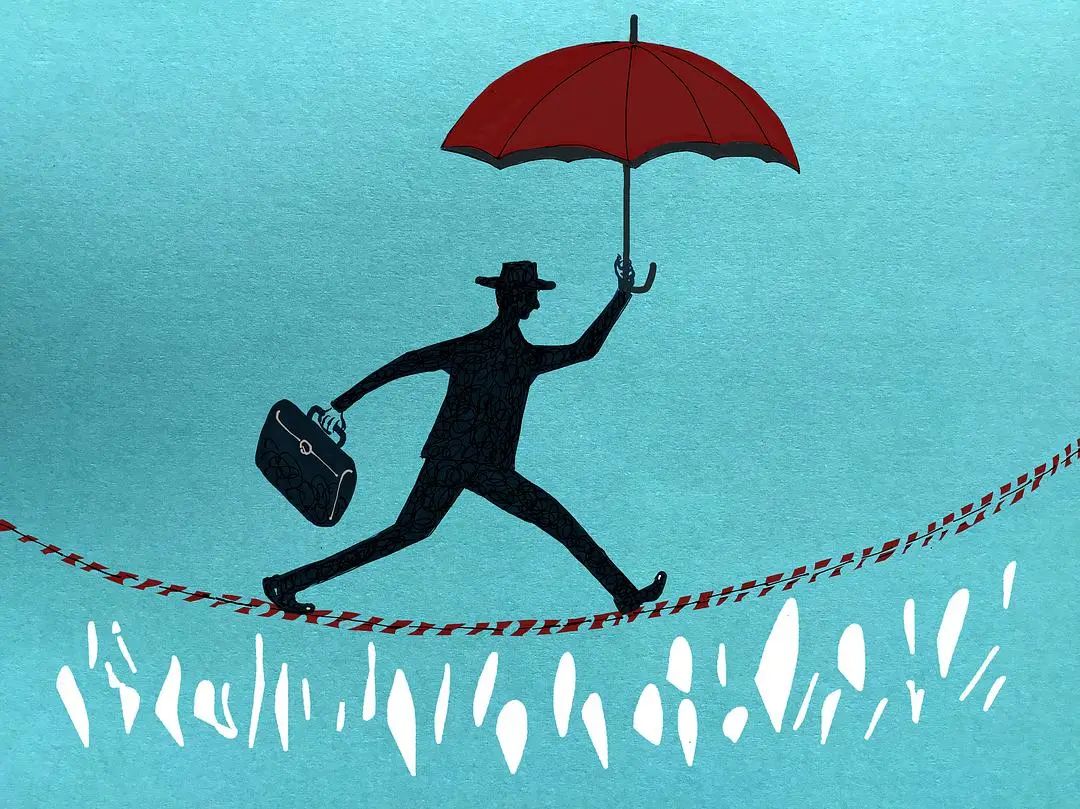
内卷是人类历史上的例外
王芊霓:
在牛津,您应该不需要带本科生对吧?内卷好像更多的是发生在本科生中间,我不知道在西方这些特别顶尖的高校,他们有这种内卷吗?
项飙:
我对牛津本科生了解很少。但是非常绩点化的,一切都工具化的小心翼翼的取悦权威,然后把同学都看作是潜在的竞争对象的情况,这个现象应该不存在。
首先,这种绩点性的竞争,或者叫内卷,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例外。在中国也就是这10年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当然也会有群体压力,牛津本科生的群体压力是什么?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期望你要说出来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有趣?
如果你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为什么有趣,就会对你的声望会打一点折扣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非常authentic(本真的),好像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取悦别人,或者说是因为别人觉得好你才去做,大家会觉得你这样的人会比较无趣。
所以你要做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narrative。这是一个习惯,他们写报告或者研究申请,你也都看到那样的轨迹,比较强调他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有趣。
中国学生出来以后,在这方面有一点困难,他们的申请报告里就写社会意义很重要。但是社会意义很重要的东西很多,再说这个社会意义重要的话题已经做过无数次了,能够做出什么新的东西?中国学生往往这方面讲不太清楚,到最后那就不接地气了,讲的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这些主流话语。
王芊霓:
这背后会不会是一个阶级问题?就是说越是家庭出身好的孩子,越能找到那种authentic的冲动,然后越是家庭出身一般的他越要随大流,他越要看人多的人往哪去,他越做不了自己。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阶级问题?
项飙:
当然。究竟什么叫不平等?
上层的人资源多生活好,下层的人生活不好,这个只是不平等的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不平等是说上层人不仅生活好,还让下层的人过得比较急,下层的人不仅是物质生活不好,而且同时你也面临很强的道德压力,逼着你去模仿别人,放弃你自己的自主性,这个就是不平等。
不平等为什么这么不正义?就是它不仅是资源上分配不平等,而且让你下层的人扭曲,所以我想说,下层的人一定要退出来,你不要跟他玩这个游戏,你跟他玩这个游戏,那大概率是输的,物质上是会输,然后在精神上也是会输的。
你刚才问到是会不会出现一个阶级问题,当然是存在了,在英国牛津也是很明显的,学古典学历史的,学生确实是出身至少是比较小康,就不用太考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