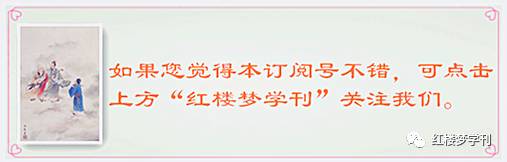

作者 秦兰勇
红楼人物中,可以互谈《西厢记》的,唯有宝玉、黛玉二人。宝钗、黛玉也曾谈及西厢,但钗黛谈西厢,实际是禁谈西厢。二玉谈西厢,出于情,少年心事,借崔张之口得以传达。宝钗劝黛玉以女德女红为重,出于礼,在宝钗看来,女子读书是末事,西厢之类的邪书更不可读不可谈。什么是邪书?有违礼法的便是邪书。至于礼法本身的合理性,则不在宝钗考虑范围之内。
袭人要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凤姐等人交待,回家后其他人都要回避,住下的话,不要用别人的铺盖,这是出于礼。袭人已被暗许为宝玉之妾,已是贾家的人了,在外面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贾家的尊严;她是贾家的私有财产,被外人看一眼都了不得。袭人离开的第二天,晴雯生病,宝玉劝她不要声张,免得王夫人命她回家养息,宝玉悄悄请来了医生诊治。王夫人关心宝玉,宝玉则全为晴雯着想。谈到用药时,宝玉有一段妙论,概而言之,即:男人是老杨树,女儿是白海棠。宝玉的劝言妙喻都是出于情,与血缘亲疏、地位尊卑皆无关。宝玉对黛玉说过“疏不间亲”之类的话,但读者不可当真。以黛玉、宝钗论,黛玉在血缘上更亲,但跟探春、迎春比呢?探春虽是庶出,迎春虽是堂姐(亦庶出),但在血缘上都比黛玉更亲。而二玉之深情,是其他人都比不了的。

凤姐惯说场面话,但也并非没有真情。凤姐宝玉同去看望病重的秦可卿,宝玉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凤姐呢?“心中虽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见了众人这个样儿反添心病”,便一方面安慰秦可卿,一方面支开了宝玉。宝玉担心黛玉“饭后贪眠,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就编造了扬州黛山林子洞耗子精的故事,引得黛玉翻身起来拧他的嘴。凤姐之于秦可卿,宝玉之于黛玉,虑事之周全,用情之深挚,令人动容。邢夫人的亲戚邢岫烟到贾府后,邢夫人无心周济,倒是凤姐对邢岫烟颇多怜惜之情,这亦是凤姐的可爱处。
翻看《管锥编》,发现中外在反对女性读书作诗方面是相似的。古人引李商隐的话:“妇人识字即乱情,尤不可作诗。”王灼批评李清照:“夸张笔墨,无所羞畏。”法国某作家说:“宁愿妇人须髯绕颊,不愿其诗书满腹。”英国某作家说:“女手当持针,不得把笔;妇人舍针外,无得心应手之物。”(以上引自《管锥编》)关于女性读书,中外文人多持反对态度,原因何在呢? 读书作诗就会乱情,乱情即悖于礼当。宝钗平时不作诗,也不教香菱作诗,宝钗每次作诗,几乎都是堂皇正大之词。宝钗诗几乎都是为应酬(礼)而作,这样说,不是在评价其艺术成就。黛玉的诗,大多是私下写的,就像女生日记,不许他人轻易翻阅。填柳絮词时,宝钗先构思,想想怎样写才能出类拔萃,这是一种竞争的心态。宝钗在写诗方面当然特别有见识,但写诗绝等同于比赛,以比赛争胜的心态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不是正路。黛玉当然知道古人写的柳絮诗词很多,但她无意与古人争胜,只是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宝钗胜在立意之高,黛玉则以情感真切动人。
人生处世,不可无礼,亦不可无情。礼太过,便流于虚伪或湘云说的“假清高”。出于真性情,方为真名士。像傅试派到贾家的两个婆子,只可视为愚。而贾赦之流的所作所为,多出于欲。愚与欲,都无所谓礼,更无所谓情。
《红楼梦》写人情世态的文字,在其他书中也能找到。《水浒传》就特别擅长写市井风情,如写王婆一段文字,令人如见如闻,惊心骇目。但红楼写至情至性的文字,则非施罗诸公所可梦到。红楼温暖人心的地方,也正在此。
在“王熙凤效戏彩斑衣”一节中,凤姐自比于斑衣戏彩的老莱子,引贾母发笑,多吃点东西。贾母说:“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一钟酒。”贾母类似的话在书中多见。贾母要娱乐,可以听女先生讲佳人才子故事,可以听凤姐讲笑话,佳人才子故事与凤姐的笑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徘徊于礼与非礼之间。“理治之书”沉闷无聊,贾母没有兴趣;主仆之间尊卑分明,仆人的语言也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只有像佳人才子这样徘徊于礼与非礼之间,甚至偶尔逸出礼法范围的故事,和凤姐(以及偶尔到贾府的刘姥姥等人)同样徘徊与礼与非礼之间的笑话,才能引起贾母的兴致。而佳人才子故事,贾母听个开头,便能猜出结局。因为这样的故事“千部共出一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千百年来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性变化,故事都是相似的,编的故事也是相似的。倒是凤姐比说书的女先生更高明,但二者性质却是一样的。
传统礼仪中不合人情处颇多,这是造成生活沉闷无趣的原因之一。鲁迅讲道德:“道德这事,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便,才有存在的价值。”而传统礼仪主要不是为了自他两便,而是区分尊卑,这样就极易流于虚伪。比如我们常常自贬以抬高他人,但暗地里又要争面子。
小红为宝玉倒茶,秋纹知道后,“兜脸啐了一口”,骂她“没脸的下流东西”,“你也不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小红被凤姐差去办事,晴雯说她“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传统礼仪就是让人各安其位,是仆人就做仆人的事,是二等仆人不能做一等仆人的事。这种尊卑森严的礼法观念,严重阻碍了个人才华的发挥。小红的爬高枝,只是借机展现能力,争取与能力相符的地位而已。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一个把展现能力贬为不安本分爬高枝的社会,是不可能有进步的。
古人中有人有感于礼的虚伪,便提倡情。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记”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具有一种破坏的力量,可以打破尊卑之别,打破年龄差距,打破国籍限制。在汤显祖看来,情甚至可以打破生死之隔。古典文学中,写情的最佳之作不是《牡丹亭》,不是《西厢记》,也不是打破人鬼、物种区别的《聊斋志异》,而是《红楼梦》。
就写情而言,《红楼梦》堪称不朽。但我们仍不得不说,当礼法虚伪、禁锢人性时,我们与其一味张扬真情,独标性灵,不如去打破这礼法的束缚。在牢笼中蹁跹起舞,不如去撞破这牢笼。
欢迎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