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7日上映,三天后有效排片基本终止。这就是体育电影《9号传奇》的成绩单(后简称《9号》)。在豆瓣上,《9号》只有7篇长影评——这是一部骂声都听不见的片子。它诞生的过程是如此曲折。用导演朱敏江的话说这是一部“没背景、没资源、没流量、没人脉”的片子,甚至在2018年开始筹备的时候,棒球题材在国内都少有人涉足。它赶上了糟糕的大环境,在它上映的2024年,中国暑期档总票房比2023年同期下跌43.5%。可以说《9号》本不该存在,但因为两个“犟种”为它搭上了所有,最终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即使把它定义成一次失败,这也是一次壮丽的失败。如果因为票房看不到他们6年的努力,就像因为老人只拖回来马林鱼的骨头,而嘲笑他一无所获。《9号》上映后,制片人刘树和导演朱敏江,向懒熊体育讲述了这6年的挣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照见了体育电影的困境,也映出了普通人的2024年,忙碌着,挣扎着,也只勉强和外力打了个平手,但又不能不全力投入生活。
《9号》讲述的故事是,前国家棒球队9号于坤,受伤告别赛场,失意的他开始执教一支由牧羊少年组成的“野山羊棒球队”。于坤让“野山羊”变成了强队,于坤和队长多杰也逐渐达成了默契,而通过多杰,于坤也认清了自己。这部电影是有原型的。多年前,在青海读书的韩国人田昌吉发现了当地孩子的棒球天赋。2006年,他开始在当地学校中组建球队。当2017年刘树在青海听说这个故事时,棒球在海南州的学校里已经成了风气,一批孩子借此改变了命运,多杰的原型华旦班玛就因为棒球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制片专业毕业的刘树认为这个故事是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从青海回来后,对它念念不忘。2018年5月,《9号》启动。它是刘树的第一部片子。刘树性格很犟。从这一刻开始,她就没有想过放弃。“我向来做任何事,是必须画句号的。”对导演朱敏江来说,电影艺术带给他的磨难,在《9号》之前就开始了。2019年,距离朱敏江的第一部电影《查无此人》上映,已经过去7年,他还在苦等第二部电影。但和制片人一样,朱敏江也很犟,电影,他还要拍。那一年刘树和朱敏江在一个局上认识。当时双方并没有对这部电影做太多交流。但半年后,刘树找到朱敏江,给他看了《9号》的剧本。朱敏江认为剧本不行,给出了意见。此后一段时间,朱敏江时不时会接到刘树看剧本的邀请,大多数时候,他都会赴约,但“不是伟大,是因为暂时没有别的东西拍”。在此之前刘树已经把剧本发给了一些电影人,但对方要么没回复,要么只是敷衍几行字,朱敏江是为数不多认真给出了审读意见的人。这一点打动了刘树,虽然当时她并没有确定朱敏江的名分。2020年,这位导演过得还不如上一年。一部已经开始勘景的电影不拍了,更糟的是,癌症晚期的母亲情况越来越不乐观。这一年的农历新年,朱敏江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要马上从无锡赶到上海一家医院。赶上疫情高速封堵,路痴的朱敏江带着母亲在乡下的路上和围栏之间乱窜,“简直困兽一样”,从上午开到了凌晨1点。几天后,朱敏江的母亲又在民宿突然呕吐,失去意识。为了抢救母亲,那一天朱敏江几近崩溃。但当慌乱到头之后,朱敏江突然觉得整个世界就这么慢下来了,他平静地点了一支烟,甚至打开了台剧《想见你》。几乎同时,朱敏江收到了刘树的消息。当晚,他成了《9号》的导演。朱敏江的第二部电影,在兵荒马乱中找到了他。《9号》成为了这位失意导演当时的精神支撑,虽然后来它又带给了他数倍的煎熬。
开机前夕,剧组大部人马已经抵达共和县,开始剧本围读。一天,人在西宁的刘树突然得知,一笔近六百万的投资到不了。当天晚上,人在西宁的她,怎么也睡不着,心脏要跳出来,“万一我猝死了怎么办?”好在刘树的包里放了日本的金丹救心丸,顾不上查说明书,一下吞了两三粒,才止住症状。至今她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在包里放上一瓶救心丹。直到最后,《9号》也只拿到了两笔行业外的投资,远远不够。钱也成了勒在这部电影喉咙上的索套,加上管理经验的缺失,造成了连锁反应。在编剧阶段,本着先省着来的想法,《9号》找来的编剧们似乎都不够成熟。他们一个一个被送上高原采风,但磨了一年半之后,始终没有形成过得去的剧本。开机也从8月拖到9月又到了10月。10月草已经黄了,眼看要彻底枯掉。朱敏江见过太多胎死腹中的项目,他知道这次拍不了就再也拍不成了。但他又知道这个行业“只有开不了的机,没有关不了的机”。朱敏江决定搏一下。“不能让它死在我手里。”开机前十天左右,朱敏江才开始接手剧本。白天他要看景,那段时间青海天黑得很晚,每天看景要看到八点多,回到宾馆已经十点。然后,他顶着高反写到两三点,甚至通宵。一大早天就亮了,他又要准备出发看景。但因为太过仓促,朱敏江认为剧本是有遗憾的。▲孩子们在拍摄中,强棒孩子的饭量很大,刘树在剧组的时候,偶尔会给他们买零食当夜宵。
按照惯例,重头戏要等剧组磨合之后拍,但全片的高潮,也几乎是最后的戏——野山羊队在全国锦标赛的关键比赛——在开机第7天就要拍,而且只给了导演2天半时间,但事实上这场戏应该拍一个礼拜。剧本要删。朱敏江只能在现场边拍边改,“划掉、划掉、不拍、不拍”。但另一方面又要把空白的地方织好,对没有拍过棒球的朱敏江来说,这超出了他的能力。另一方面拍摄进度又很慢,棒球运动的动态捕捉需要时间,这部片子偏偏又没有配视效组,很多运动镜头,只能用很笨的方式一点点拍。一个棒擦过球的镜头,剧组拍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成功。“一个很爽的体育电影,消耗的时间是很恐怖的,我们做不到。”在片场,朱敏江看着孩子们又摔又扑,知道这些孩子选对了,这个项目本来是有机会,欣慰的同时又感到愧疚,觉得对不起孩子。在一次技术指导会上,当着两岸三地棒球教练和主演的面,朱敏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丑陋地哭了”。这一哭换来了半天的拍摄时间。但这场戏也只能呈现跑垒,扑垒或者封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影片里于坤带着球队在雨中备战的戏本来需要两天,但最后时间不够,很多精细的特写和调度都无法完成。但质疑是逃不掉的,“为什么不拍孩子的眼睛,帽檐滴雨、滴汗的镜头?”一个圈内人看了这场戏后,不客气地问朱敏江:“这是你拍的?”面对质问,朱敏江不说话,只是抽烟,因为“解释没有用”。开拍前,为数不多让主创开心的事,是找到了后来因为《棒!少年》被认识的,强棒天使棒球基地的孩子们。2020年主创去基地选角,选中了一个不错的小队员,准备离开。但突然,马虎不知道从哪里,“一把刀”一样地出现了。两人知道主角“百分之一千、一万是他了”。马虎,既江湖,又纯真。在拍摄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可爱对话。“导演你喜欢什么车,等我火了给你买。”“我要玛莎拉蒂”,“好!给你玛莎拉蒂”。剧组其他人听见也来问马虎要车,马虎又心疼起钱,“不能再要了!” ▲电影海报,正中人物为马虎。
即使纯真如马虎,也被卷入了这场和时间的较量里——他需要迅速进入角色,没有循循善诱的时间。电影里有一场戏是马虎扮演的多杰在大巴车上和于坤认识彼此,真正成为朋友。这是一场情感戏,但到了开拍的时候,马虎哭不出来,几遍不行,几遍不行。摄制团队只有一个小组,这场戏不拍完别的戏也拍不成,马上要到深夜,进度已经等不起了。这个时候,朱敏江远远看见表演老师把马虎领到一边,轻轻推搡他,一边说着什么。然后朱敏江听见了马虎突然对表演老师吼了一声——哭出来了。导演知道这种“凶得像头狼”的状态太过了,但还是抢了一条。拍完后马虎嚎啕大哭,表演老师上去抱他,马虎又踢又打,不许她抱,表演老师也跟着哭了。后来朱敏江知道,那天为了刺激马虎,表演老师说他是“没妈的孩子”——马虎三个月的时候,妈妈就离家出走了。而马虎说的是:“我要杀了你!”。
在电影行业,即使票房上亿的片子,掀开看也是人性。比如一部大制作光是给车加油的钱就有几百万元数量级。因此,偷油成了普遍现象——在剧组加满油的车,有人会在晚上把油放出来卖掉。剧组还是江湖,朱敏江的第一部电影有一场在火葬场的戏。为了要钱,当地村民在拍摄现场闹事,把路灯都砸了,剧组反复报警,但没有用。局面很快演变了成一场村民和灯光组之间的斗殴。朱敏江是在乱飞的拳头中间,把这场戏抢完的。当制片人为了找钱经常不在剧组,制片组底下稚嫩的年轻人,显然不足以驾驭这些水面之下的东西,很快就被“老油条们”架空。剧组也迅速形成了两个派系,争夺资源。“都知道这是个新剧组,他们觉得可以到这里来分一杯羹,生态就是这样的。”朱敏江说。有一段时间,朱敏江发现总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自己旁边。后来,他知道这个陌生人是刘树请的退役保镖,负责保护导演和机器。因为有人放话说要让戏拍不成。有些钱的去处也说不清。杀青结束对账的时候,刘树发现了一笔北京君泰商场的购物单据,金额5万多,买的是都大牌彩妆,但事实上这部男人戏根本用不到彩妆。类似说不清的账单还有很多……雨中训练那场戏后强棒孩子就要杀青了。那天因为天气太冷,戏拍得很苦,一直拍到后半夜。刘树给孩子们办了杀青宴,杀青宴上,马虎因为舍不得当地的小伙伴,边吃边哭,结束前他拥抱了每一个人。不那么温情的是,几乎同时刘树发现,当天拍的素材不见了。拷贝是被执行导演偷偷扣下的,事因是当时执行导演还没有收到自己的第三笔劳务费。而刘树想的是剧组马上要转场到西宁,这笔钱可以晚上到了西宁再打,而且转款的U盾已经跟着她的行李先行被拉到西宁。眼看说不通,她只能想办法把钱付了了事。但事实上双方只是约定当天打款,“中午也叫当天晚上也叫当天,对吧?”那天摄影团队下午4点才出工,后半夜杀青,刘树认为按理来说都是这一天内的事,但摄影指导坚持,过了12点,就要再算一天的钱。为了要挟,在关机的一刻,摄影指导偷走了拷贝,提出钱一定要给,不得商量。最后,还是制片人妥协了。至今刘树仍对这件事愤愤不平,她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硕士,能做这种事。首映那天,那位摄影指导发消息问她,电影的情况怎么样,“我没空回答你,你不要老发我。”刘树回复。好在,2020年10月17日,在所有人都筋疲力尽的时候,《9号》杀青了。杀青前一刻,刘树看着有4万人坐席的体育场,知道自己和《9号》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主创在拍摄地。

拍完之后,刘树经常跟别人讲,自己的第一部电影2021年暑期档就要上映了,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直到四年后才上映。这几年间,她回老家的次数变少了,因为怕被别人问,“电影怎么样了?”,“怎么还在搞这个?”。杀青后进入剪辑阶段。当时剧组只给后期制作留了二十多万的预算,但这完全不足以做完整个后期,零头都不够。刘树第一次看见初剪片子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我的‘孩子’怎么是这样的?”。她要救一救自己的孩子。几年来,这位制片人像钟表匠一样,一点一点地修缮着这部电影:因此,如果翻看所有后期制作全流程名单,你会发现片子的后期制作团队豪华得不成比例:剪辑指导是华语电影最顶尖的剪辑师陈志伟;声音指导是《孤注一掷》的林思宇;视效总监和调色指导是参与了《狄仁杰》系列的韩国人李庸基……直到去年冬天,她还没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校长和老师要讲普通话?”后来她执意给他们配上了“青海普通话”。一开始电影配乐计划用罐头音乐,几万块就够了,但后来还是做了全片原创配乐,加上了四首歌曲。刘树甚至让声音指导飞到青海,给电影采集了很多环境音,其中包括鸟叫,虫鸣,这些“小小的声音”。一些努力甚至悲怆地可笑:片尾致敬部分,刘树感谢了所有人,其中包括茶水工、木工和油漆工。她还坚持在结尾加上了一段致敬原型的视频,视频素材是她熬了几个通宵,在20多个原型人物十几年来发过的朋友圈和社媒中,一帧一帧找出来的,这支视频改到了上映前最后一刻。每一次修缮都需要钱,但钱始终是不够的,后期只能做做停停。这几年,她每一周都需要用钱。她变卖的东西包括手表、包、手机,几十箱酒。刘树还开玩笑说认识了一批朝阳区搞回收的,“一打电话半小时就上门来取了。”即使这样各家银行的本金和利息还是压得她喘不过气。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部小成本电影,但事实上《9号》远比它看起来要烧钱,光是特效镜头就有543个。这些年,刘树从制片人,一步步把自己熬成了投资人,先是把钱,然后是把自己的生活贴了进去。朱敏江也不好过。这几年来他一次次被重启,投入工作。然后又是停滞。在这个过程中,和制片人一样,他只能用琐屑的努力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导演曾经自己亲自上手调整剪辑。没有剪辑软件,他用手机把电影画面一张一张拍下来,又用美图秀秀在图片上给剪辑师做上文字标注,再把标注好的图片导到电脑里。这个过程朱敏江做了无数遍,这样恐怖的工作本应该用计算机干。“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么笨拙的事情,琐碎地忍,一直地熬,它跟我的底色是相同的。”▲一张反映了制片人和导演几年后期工作真实状态的图片——一帧一帧去抠每个细节。
两个主创找了所有能找的人发声、包场。刘树还凑出50万,临时找人做抖音投流。但这部“没背景、没资源、没流量、没人脉”的片子,宣发上一点动静都没有。院线是现实的。《9号》首映拍片率是1.7%,到了第二天这个数字掉到了0.4%。三天之后,就基本没有什么排片了——这部片子在院线基本死掉了。首映那天,有朋友问刘树票房怎么样,刘树说太忙了,来不及看,但实际上那天晚上她并不忙。上映后那几天,一贯顽强的刘树偶尔会哭,不过是没有声音的,“我向来哭都没有声音”。
但另一方面,草根出身的《9号》,能出现在大银幕上,就不算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尤其对刘树和朱敏江。对刘树来说,她认为自己对得起所有人。这几年自己没有拖欠任何人片酬;因为强棒的孩子演得太卖力了,杀青后刘树赠送了强棒基地5%的电影股份,希望日后上映后分红后能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对两个投资方,虽然签的是风险投资协议,但她说从做人的道义出发,以后肯定要把本金还回去。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她画出了自己的人物弧光,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制片人,“这些年我的成长不是空白的”。《9号》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马虎带领的野山羊队,另一条是因为肩伤告别赛场的教练于坤,在执教过程中逐渐认清自己。朱敏江希望让马虎和于坤把对方作为镜子,互有成长,两条线索不断交织让电影产生“巴赫音乐一样的复调”。但内部对于坤这条线争议很大,线索中的一个情节是,于坤在执教中认识到自己最想做的还是球员,要求回到国家队,被拒绝后于坤在备赛的关键时刻离开了孩子们。这个设定始终不能服众,但朱敏江很强硬,就要这么拍。朱敏江自己比剧情更需要于坤这条线索,因为于坤的身上投射了朱敏江作为导演的不得志。可以说朱敏江把自己的人生装进了这部片子。▲电影剧照,左侧为剧中人物于坤。
和《9号》一样,朱敏江的人生一直在耽搁。朱敏江读过两次大学,九十年代末他考上南京师范大学,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电影,他动过退学的念头,但始终没有勇气。在北京的同学曾给他带来了一份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这张纸在朱敏江的枕头底下压了三年。后来朱敏江在老家江阴当上了中学老师,但在24岁那年他切断了自己的后路,裸辞,然后重新高考。高考的时候,朱敏江被分在了自己曾经工作的中学,监考老师正巧是和他同一批进学校的同事。同事反复走到他旁边,对照桌上的身份证,“像见鬼了一样”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朱敏江。那是那一次,朱敏江考上了中戏。朱敏江是幸运的。那一届,班上一共22个同学,朱敏江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在做导演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这让他“可以跟命运耗着”。中戏的老师曾认为朱敏江是建系以来最好的学生,但在毕业之后的大多数时间,这位导演不是帮同学改剧本,就是接一些小小的项目,包括给公司拍微电影。但就像于坤渴望上场一样,朱敏江只想做电影导演,如果不能,宁愿离开。指导电影的机会极其稀少,朱敏江知道自己要走出去,因为第一部电影的投资是在同学的婚宴上拉来的,此后他更是逢局必去,“去过KTV、迪厅很多乱七八糟的地方”。但关键时候,他又不够圆滑事故。这几年朱敏江写过的、改过的剧本已经有百万字,只要有人说找他拍东西,他都会如临大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很长的东西。朱敏江知道很多人找他,只是想“捞”他一下,但还是会去。一次,有人邀请朱敏江参加座谈。他顶着暴雨来到一个破旧的工业园区,结果他发现讨论的是一部根本不可能落地的抗日剧,当时“灵与肉是分离的”,但他还是要发言。在《9号》之前,这些努力基本颗粒无收。找来的人和项目大多要么不靠谱,要么卡在了作品和数据上。就连刘树在定下朱敏江之前,都有朋友劝她慎重:“一个导演快十年没有作品,问题出在哪?”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对抗一种机制。中国的商业电影被几家大发行公司主导,它们掌握院线渠道,自己投资、孵化项目,批量生产流量电影,资源在圈内循环分配。在这套机制下,编剧是谁,导演是谁,并不绝对重要。像朱敏江在“圈外”的导演越来越难出头。“你知道恐怖的是什么吗?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年、两年,是十来年了。”在《9号》上映第一天,朱敏江要上一场直播,直播之前,他注意到了两边的白发。2024年,朱敏江45岁。曾经他为了显得成熟故意蓄起山羊胡。但现在见人前,朱敏江要刮掉胡子,洗个澡,“不然人家觉得你都这个年龄了,啥都做不出来,混子吧?”这些年朱敏江从没有真正躺平,但痛苦是难免的。经常地,朱敏江会问自己,“我的人生好不完整,为什么我不能达到我的理想?”朱敏江形容自己这六年,就像在悬崖上荡秋千的小孩,荡出去看到绝美的风景,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正如他的导演生涯。但因为《9号》,他看到了一群同样在悬崖上的人。强棒的孩子大多是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和孤儿。在来到强棒之前,他们经常是饥饿的。马虎的妈妈离家出走后,有一年,爸爸带回来一个女人和小男孩,第二天,这三个人骑着摩托出去玩了,留马虎自己在家里饿了一天。后来,爸爸又去打工,女人有一天也带着小男孩走了,马虎在家里又饿了三天。在《9号》拍摄的时候,这些孩子多的时候一个人要吃三份盒饭。有一次剧组吃饺子,厨师按每人20个饺子,准备了3000个饺子。但那一次几乎每个孩子都吃了百、八十个,马虎一个人就吃了一百多个。孩子们身上最触动朱敏江的是,他看到了生命本身的饥饿——每个人都在搏命。拍雨中跑步那场戏时,当天高原零下4、5度,飘着小雪,两台洒水车不停洒水,但是按剧情,演员不能穿的太厚。孩子们在校服里面裹上保鲜膜保暖,跑了一下午,校服脱下来都站起来了。这个时候马虎会对着队友们大喊:“大家还能不能干!”。扮演于坤的演员告诉制片人,如果没有孩子们卖命的演出,那场戏他扛不下去。朱敏江还提起了一个叫宋潮的孩子。在选角的时候马虎是无争议的主角,在导演心里,其他人是不入眼的,宋潮只被分配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后来朱敏江听说,这个孩子一直在“闹”,他不甘心自己只能做陪衬。拍摄的时候,他能看见宋潮的眼神是失落的,但轮到他的戏份,又会特别努力。虽然宋潮扮演的角色是如此微不足道,但朱敏江还是有意多给了他几个镜头。因为他“太想要了”。就像多杰让于坤有所成长,强棒的孩子也成了导演自己的镜子。朱敏江觉得孩子们的搏命,让自己对导演生涯的失落和自怜,显得“太酸腐了”。“很多人都是在悬崖边,像羚羊一样在搏命。谁不是在困境中挣扎着找到呼吸的机会?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去说苦说难。”借由《9号》,朱敏江画出了自己的人物弧光——和过去实现了某种和解。“我的路会继续走,走到我不想走的那一刻为止,就是这么回事。”在跟随《9号》的这几年,这位导演时常想起自己曾和命运有过一次殊死搏斗。师范毕业当上老师后,心里总想着电影的朱敏江并不快乐。一个五月,他在从上海坐大巴车回江阴,路上,车子经过一大片油菜花。朱敏江看到油菜花胡乱生长的样子,突然嚎啕大哭:“花都能这么肆无忌惮地开,我的梦想却要压抑这么久。”但他迟迟下不了辞职的决心。直到有一天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军令状——到了12月25号那天,如果还没有勇气递辞职报告,就让这个梦想烂在肚子里。到了12月25号下班的时候,朱敏江还是觉得没有勇气。他坐在音乐老师的休息室里,心里很乱,他用二胡拉起了《江河水》,一首表达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曲子。他眼睁睁看着钟表一点点地走,直到教学楼一片安静。所有老师都下班了。朱敏江绝望地意识到,再这样等下去,“这个梦想不就完了吗?”那一刻他感觉自己要死了,在强烈的窒息感中,朱敏江突然站起来,扔下二胡,直接往高中部奔去。“那天运气特别好,校长就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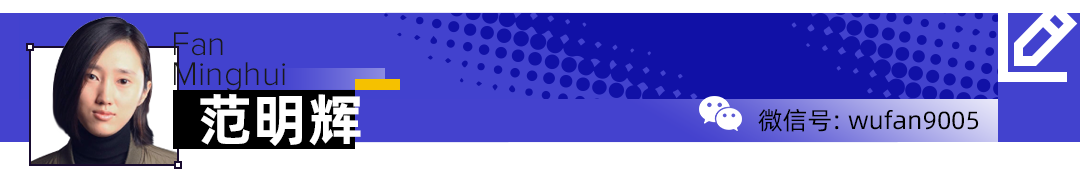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了解懒熊体育更多产品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