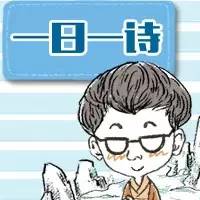刘鹏,1996-1999年复旦新闻学院硕士,2004-2009年复旦新闻学院博士;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新闻记者》杂志主编,也是复旦等高校的兼职硕士生导师、研究员等。11月2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创建90周年之际,刘鹏再次回到学院,与我们分享他的所思所念。
“人生是否成功,不在于官当得多大,名声有多响,只要踏踏实实为社会做工作,尽了自己的能力,就是没有辜负复旦新闻学院的培养。”
刘:
我199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当时新闻专业没在我的家乡招生——招的话我也未必能考进(笑)。但是,因为家庭的影响——我父亲是家乡报社的资深报人,我对复旦新闻非常憧憬,恰好那时候复旦推出跨专业“辅修”课程,我才有机会跟新闻学院的老师们学习,修读了各门基础课程,毕业时考取了新闻专业的研究生。
还记得考研复习时,赵民师兄(他本科是复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的)到我宿舍来玩,给我讲考试“秘诀”;哲学系一位年轻老师特别热心,有天中午骑自行车载我到文科楼找孙玮老师给我“辅导”专业课;孙玮老师还特别推荐了甘惜分先生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作为复习资料,我读后受益匪浅。
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学生比较少,我们和老师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关系也更加亲密。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子让先生,为人谦虚质朴,严谨认真,这在新闻学院有口皆碑。最近叶春华老师与同学们的书信集《千封信笺载师道》出版,张老师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张老师指导我做《申报》版面编辑史的研究,亲自设计了各种版面元素统计的表格,打印出来跑到南区宿舍送给我。给我指导论文的时候,从来都是用铅笔小字仔细地改在页面旁边,表示这只是参考意见,觉得不对可以擦掉。
那时夏鼎铭老师给我们上马克思新闻理论的课,每次选取一个题目让大家讨论,夏老师最后做一总结,同学们七嘴八舌,非常热烈。和我们熟悉了,夏老师晚上散步时,常常弯到我们宿舍坐一会,聊聊天。那时复旦系友谭启泰在《南风窗》当主编,每期杂志寄给夏老师,他看完后再带给我们看。毕业多年后,有一次到新闻学院参加研究生学术论坛,发现夏老师跟学生们一起坐在后排听会,那时候他已经退休好久了,他告诉我,就是想听听现在年轻人有什么新思考,让自己别落伍。
我在辅修课上第一次见到叶春华老师。记得第一天上课头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复旦新闻系是培养总编辑的!当时听了很惊讶,这位老师口气怎么这么大。后来和叶老师谈起来才明白,这一方面指的是很多复旦系友在各媒体担任老总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指
复旦新闻教育的一个传统:重视新闻业务教育,重视通过实践学习业务知识
,因此复旦毕业的学生往往在实践中表现出色,成长为媒体中的业务骨干。
刘:
硕士毕业后我就进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新闻记者》杂志社工作,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自己性格比较内向,未必适合当记者,而专业期刊这样一个既从事编辑业务,又带有研究性质的工作,可以让我保持对新闻业的敏感,同时也有机会安静下来思考些问题。虽然期间也有过转型机会,但到今天干了二十年了,仍然乐在其中。
平时工作中与复旦的老师联系非常密切,期间还在新闻学院攻读了博士学位,
感觉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复旦新闻学院
。
工作之后,更体会到复旦新闻影响力之大。带我入行的丁法章、吕怡然等老师,都是复旦学长,这些年来,无论新闻业界还是学界,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我们的系友,都能得到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不但多了一层亲切,更添了几分自豪。
问:您曾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特别是最近关于老系主任王中先生的两篇研究文章,引起众多关注。想请问您为什么想要研究王中先生呢?
刘:
其实,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新闻业界还是学界,都有“复旦派”,或者“海派”、“南派”的说法,往往带有改革派、实践派的意涵,但大多是口头说说,并没有作为一个研究进行认真的分析梳理。复旦新闻学院传统的形成,王中先生是个关键人物。因此我写了《为何是王甘——王中、甘惜分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的产生原因及时代背景》(《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和《范式的探索:复旦新闻学学派的浮现及其学术传统——以王中为中心的研究》(《新闻大学》2019年第10期),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点谈不上成熟的思考。
在研读各种史料中我发现,复旦新闻研究和教学最重要的特点有二:
一是与现实紧密互动。
王中先生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在根据地办报多年,到复旦后与新闻界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对新闻理论研究的时代要求,对新闻实践的现实问题都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他的理论思考总是从现实中来,并且回到现实中去检验。这是他的研究,也是复旦新闻研究在业界甚至社会各界影响广泛的根本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海纳百川的理论视野。
无论是王中还是宁树藩、丁淦林等复旦学者,
除了党的新闻理论,他们对中国传统办报思想,特别是西方最新的最前沿的思想和实践,从没有拒斥封闭的态度,而是“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由此也形成引领学科的创新价值
。这个特点与上海城市精神也非常吻合,说明国际化大都市文化环境对复旦新闻传统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具体到写这两篇文章的缘起,首先要感谢我读博士的导师童兵先生。当时他给我出了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海派文化与上海报业。虽然论文写得不算好,但是对上海报业史的很多资料,特别是《王中文集》,认认真真看了,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想法。另外还有两个小事,也可以一提。一是当年读研的时候,学院资料室装修,清理了一批废旧材料,我碰巧捡到一本1957年新闻系油印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汇编》,在那上面第一次看到摘录出来供批判用的王中先生很多观点,看后感觉非常震动——这些观点怎么这么精彩啊!很多话放到九十年代也仍然很有针对性!由此我对王中先生的生平和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件小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后期,那时我家就在家乡报社的办公楼上,有一天放了学,听说报社请了一位大学者来讲课,叫甘惜分,我很好奇,就悄悄在门口张望,赶上讲座结束,一群年轻记者编辑兴致很高地走出来,边走边议论,有人就说,一直听说甘惜分是个“老左”,今天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思想挺开放的啊……虽然无心的一句话,但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完全没想到,后来跟童老师读博,甘先生成了我的师爷,前些年多次去北京,童老师一直说带我去拜见一下甘先生,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缘。现在甘先生已经去世了,我想这篇文章的梳理,也是对他思想整体的一个还原、一份纪念吧。
对于王中先生,我请教过一些复旦前辈,他们说,八十年代老先生上课,没有教材也没有讲义,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那里和大家聊天。因为时代的原因,王中先生很难说有多么高深的理论素养,但是他很多极具智慧的思考,却能给人无尽的启发。
复旦新闻九十年历史,王中先生可谓灵魂式的人物,或者说是一位“燃灯者”,他开创的复旦新闻“学脉”,直到今天仍然照亮我们科研和教学之路。
刘:
在院庆遇到很多同学、校友,很亲切很开心。特别是看到80岁的八位前辈、老师,以及90岁的老校友,又激动又感动。他们正是我们学院繁荣、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一个根基,
有这些老前辈做奠基,我们新闻学院的传统和辉煌才能薪继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