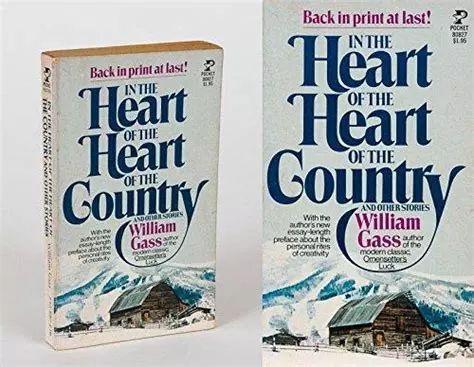
威廉•H.加斯作 叶丽贤译
就这样,我漂洋过海,来到了……
B镇……
印第安纳州一座小镇,紧附在一片田野上。一千两百人曾在这里接受过两次人口普查。整个小镇出奇地干净,树影婆娑,总是将它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外头的公路。有一块草坪上,甚至伫立着一只用木头或钢铁塑成的鹿。
跨过一条小河,你就能抵达这里。春日里,草坪转绿,连翘在歌唱,火车开进来时,在劈开小镇的铁路上,笔直明亮的铁轨也哼起了小调,伴着火车自身那令人愉悦的轰鸣声。
沿着后街小巷,柏油路面一路碎成了石砾。那儿住着韦斯布鲁克一家,门前开着天竺葵,还有霍斯法尔一家,莫特一家。人行道支离破碎。石砾间的沙尘扬起,仿佛马车过后留下的气息。我退出了爱的服役,在此归隐。
在中西部,五湖区的下游一带,冬日的天空总是暗沉窒闷的;天色放晴,允许心情出来透气的日子是少有的,也是让人格外留意的。我心里一直数着日子,手里的笔落在这页纸上时,已经有十一天没有见到太阳了。
我的屋后有一排枫树,树头全被砍去了,电线可以从那里自由穿过。十英尺高的树桩留在了那里,我像孩童一般,爬上了树桩,望着田野从我身旁缓缓地展开。那只是寻常的田地,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整,春日里满是坑坑洼洼。表土薄薄的一层,但砂石并没有多少。地里一年种玉米,一年种黄豆。黄昏时分,欧椋鸟黑压压地落在一棵落叶松上,那是地里唯一的树,矗立于田野的中央。天空变化时,田野也随之而变。站在栖木上,我觉得我失去了曾经所有的岁月。似乎我终于活在了自己的眼睛里,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想,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为了用眼睛来看,为了与新事物对抗,啊,神啊,这有多畅快,就像微风里的空气。有一些时刻,如愚人一般在树桩上忘形出神的时刻,我不由得把自己看作种子,整个人就差没有飘走,散落了,我可不就是这样吗?想要甩掉的爱情,我偏偏如愚人一般保留了下来:可这如今对我有何用处,万圣节后没有送出的糖果?
比利·霍尔斯克洛的房屋两边各有一些空地。天气好转的时候,空地上长满了蜀葵。从春到秋,比利一直在收集煤块和木头,一块块一段段地堆起来,放在门旁,保持暖和就是他唯一的工作。晴暖的日子里,我最常见到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我注意到他有一点斜视,这也许就是我从身旁走过,他却没有跟我闲扯的缘故。他的房子只有一间车库大小,十分老旧。油漆早已随着青春一起脱落,露出被风雨侵蚀、弯曲变形的灰白木板。比利也是这个模样。天冷时,他会穿一件短小又笨重,还有点褪色的黑外套,要不然,他就只穿上下身同样宽松、油迹斑斑的衣裤。我怀疑他的背带还没变旧前是黄颜色的。

插图:邰雪怡
这些电线激怒了我。因为它们,三棵树被砍腰锯头,但它们接着却毁了天空的容貌。它们像围栏一般从我面前穿过,和云朵一起围住了乌鸦。我无法把围栏穿透,但我把自己情感的枝条投掷了过去。究竟是什么激怒了我?我就站在树桩上,原地搭起了一个平台,可那些电线却阻挡了我出去的路。被砍的树,黑色的电线,那边所有的鸟儿,都惹怒了我。为了一片牧场,我蠕动着身体要穿过眼前的围栏(这篇小说存在大量关于虫子的意象或隐喻,这是其中一例);而对于这片农田,我是不是也抱有同样的感情?
教堂的尖塔状似女巫的帽子,五只鸟儿,都是鸽子,栖息在它的檐沟里。
树叶在窗框里摇曳。我说不上来这个景象有多美,有什么含义。可树叶确实在摇曳。树叶在玻璃窗中摇曳(“我”不得不透过窗户看外面的世界。在这篇小说里,“窗户”和“眼睛”一样,是有限视角或狭隘意识的象征)。
年轻的母亲头上顶着卷发夹,裹着俗艳的披巾,穿着略肥的裤子,在速洗店里来回晃荡,还抽着香烟,吃着糖果,喝着汽水,翻着杂志,朝孩子大喊大叫,那声音要盖过机器轰轰隆隆的响声。
银行外头,一个年轻人身穿新熨的衣服,正拿着钥匙准备开门。大街上,有很多老人正在梦中行走,脚步微微踉跄。受不了夏季要命的热浪,他们坐到了窗台上,双脚恰好悬在店楼投下的细长阴影里,眼睛定定地望着街道。他们的意识跑去了哪里,我并不清楚。他们的意识至少不在眼睛里。或许,他们的意识涣散了,只与温度和皮肤有关联,就像婴儿的意识,只是不那么强烈。靠近拐角处站着几个大个子,是穿工作服的雇员。一辆卡车在那里拐弯,准备在粮食饲料店过秤。药店窗户上人影在晃动。风把牲口的气味吹到了镇上。我们的目光就像老人的目光,被驱回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悯。
镇上有两家餐馆,一家茶馆。两家酒吧。一家银行,三家理发店,其中一家窗户上装了绿色的遮光帘。两家杂货店。一家福特汽车经销店。一家药店,一家五金店,一家器具店。几家卖饲料、粮食和农具的商店。一家古董店。一家台球房。一家自助洗衣房。三名内科医生。一名牙医。一名水暖工。一名兽医。一家修缮得体,涂成毛莨色的殡仪馆。无数美容店,白天关,晚上开,就像夜间开花的植物。一家优惠百货店,弹丸那么小,却有几层楼。一间简陋的棚屋,你要是愿意趴下来或者挤进去,就能从那里订到家具;那儿的家具都是用各种长度的不锈钢曲管,颜色鲜艳的塑料,金属丝,透亮的虫胶制成。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分会,一个卖根汁汽水的摊位。各种东西的小代理:化妆品、刷子、保险、贺卡、菜园子里的果蔬——无所不有——还有样品鞋——代理商脱下帽子,打开小背包,对着咖啡杯和杯中溶化的白糖就能谈起生意。一家生产大纸袋和纸板箱的工厂,位于一栋砖砌的旧楼中,旧楼还承载着“歌剧院”的传说,几个微微泛金的大字至今还挺立在楼顶上。一座卡内基捐建的图书馆。一家邮局。一所学校。一座火车站。消防站。木材堆置厂。电话公司。焊接车间。汽车修理厂……从小镇一端到另一端,沿着公路这条线,像星点般分布着五座加油站。
一八三三年,克林·古迪昆兹(克林·古迪昆兹其实是研究美国西部的历史学家,加斯很可能为其虚构了一个身份,并将自己杜撰的一段话归在他名下),一位名字来自传说的巡回布道师,曾如此概述某个印第安纳州小镇的状况:无知诞下一窝龌龊的幼雏。普遍蒙昧未开。镇上的居民基本都在戒绝文化知识……据我所知,这里没有一位研究文法或地理的教授,也没有一位能教授文化或地理的老师……其他人一年里有几个月接受一些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培训,教学形式陈旧不堪,毫不合理……难道还要我提醒你,这样的死水潭子,多适合生出一群叫人作呕的爬行动物?呱呱的妒语,鼓鼓的偏见,盘绕的疑影,温热的盲目,鳄鱼的阴毒!从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但不是在这些方面。
街道一侧,有一块区域被锯木架隔开了。一群结实精瘦、神色愁苦的男子,各个都身穿蓝牛仔裤,脚蹬牛仔靴,头戴帽子,此时正从卡车上卸下一场简陋的嘉年华会。商人在推销自己的商品。那里即将有免费的游乐设施、嘈杂的乐声、游行队伍、汽水、爆米花、糖果、圆筒冰淇淋、奖品和图画,还有所有你能忍受的掐捏、推搡、吆喝、挤撞、吵嚷、嘶喊、尖叫和咆哮。小孩子踏着彩饰自行车从旁边经过,车轮转成了彩色的虚影,绉纸带随风飘扬,狗儿兴奋异常。接着还会有一次宠物展,狗儿、猫儿、鸟儿、绵羊、小矮马、山羊都送来参展,设了奖项,却没有胜出者。旋转木马在转动。摩天轮晃悠悠地爬到高个子踮脚就能够到的高度,不耐烦的操作员用愠怒的目光称量着每个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琢磨着他们坐上机器是否安全。一只电喇叭反复播报着慷慨的活动赞助人的名字。第二天,镇上的人很快就将街上的垃圾打扫干净。
正如柏拉图隐晦地说过,我曾因遭逢不幸,双翼萎缩,穿过俄亥俄州秀色可餐的版图,我坠落了下来,落成了诗人,落到了我第六种身体里;那就是印第安纳州B镇的这所房子,外头是摄人心魂的蓝灰色窗户,里头是圣洁且神奇的脏腑。高大浓密的常青树守护着它的入口。而我正居于其中。
我记得当我迷失在一排排玉米秆中间时,自己也变成了其中的植株;这片乡土就这样掌控了我,就像我康健时能完完全全主宰自己一样——我充盈了自己的房子和身体,遍及它的边边角角。人们走过时,没有谁会发现我已经流溢到了门口。此地此身就是我的居所,我到此奔丧,只是为了再生于其间。在他人看来,这或许有点愚蠢:为了爱情。为何我会觉得怅然若失?我是如何失去她的?她从来不属于我;她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个金发假小子,总是光着脚,有着青少年的懒散,有着男孩子对体育运动和钓鱼的偏好,她就像来自吐温书中的角色,或者更糟糕,像赖利笔下的人物。岁月不会手下留情。
这里很少有人会手牵手……在B镇不是这样。除非勃然大怒,没有人会触碰彼此。偶尔女孩子会勾着彼此的手臂,摇摇摆摆地走出学校,向家里或剧院走去。我梦见我的唇沿着你的后背一路下滑,像轻舟漂流直下。我的指尖顺着你的血管向前摸去,赤裸的双手抱着你裸露的双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