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送:
2019年01月
丨
2019年02月
丨
2019年03月
丨
2019年04月
丨
2019年05月
丨
2019年6月
本月读书26本,其中弃了8本,下面的书中其中有不少都是以外链的形式记录的,请大家一定要点一点。
本月的主题是令狐冲,令狐冲的世界已经过去很久了,令狐冲的世界是混乱的。
正如同本月的阅读一样,混乱而前进着。
然后令狐冲最后的残躯在一场大雨中死去。
我们都是雨后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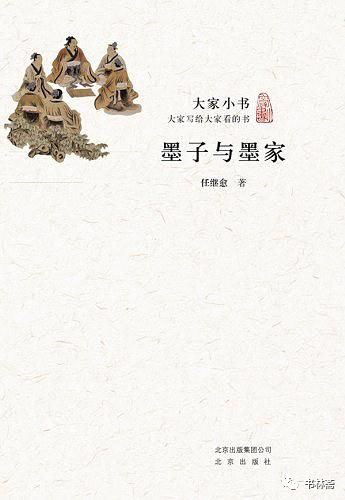
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是没法谈细问题的,只能谈大问题,好在这本小册子谈的大问题还算准确。
很多人把墨家视为战国时期的共产主义,实则不然,尽管在一部分观念和组织形态上有点接近,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因为最核心的主要矛盾不一样。
墨家认为,一切的不合理、战争都来自道德品质问题以及引发道德品质的奢靡上,墨子针对这一根本论点进行发散,从而得出了非攻兼爱的结论。——事实上这个出发点和儒家是一样的,只是两家在方法论上有一些不同罢了。
考虑到墨家在后世并没有多大影响,考虑到墨家的思想并没有太多需要被继承,我们就把它视为历史的产物好了。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历史的产物了,只要是可预见的。
包括令狐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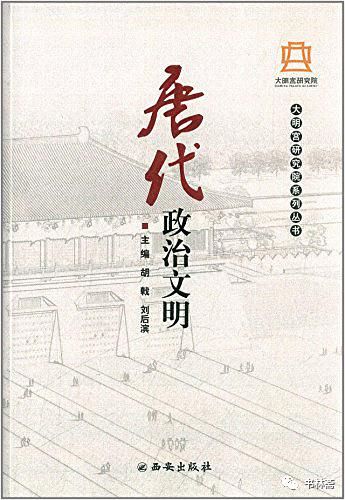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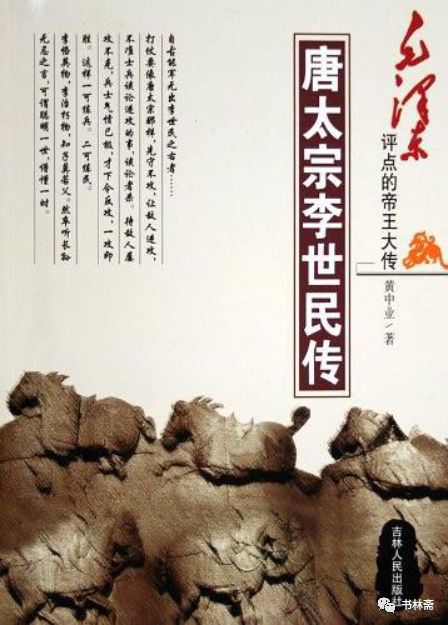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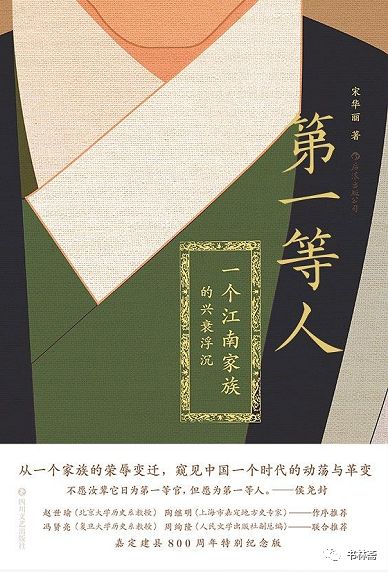
史料既详尽又扎实,在史料的甄别使用上能看出来与普通小说写作者的不同,作者应该是科班出身——果不其然,是赵世瑜老师的学生。
但我竟不知该如何定义本书。史学专著?除了罗列史料使之成文后没有任何论断。人物传记?除了侯家几个人的行踪外没有任何分析。文学小说?除了提到大量人物事迹外没有任何情节。
作者其实很令狐冲。
换句话说,本书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都是比较尴尬的,无法界定,也无从界定。更重要的是,本书的尴尬来自作者的立场——作者仿佛沉浸在侯家人的情绪中,感慨大明已失、天下已亡,却没有想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为什么李自成会起来,为什么多铎都能胜利,为什么李成栋能打赢?
明末的士大夫是想不明白的,这一点不怪他们。但作者也这样,那可以怪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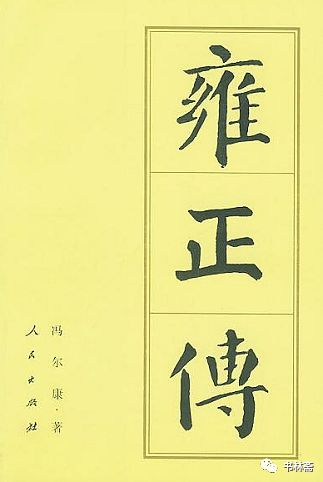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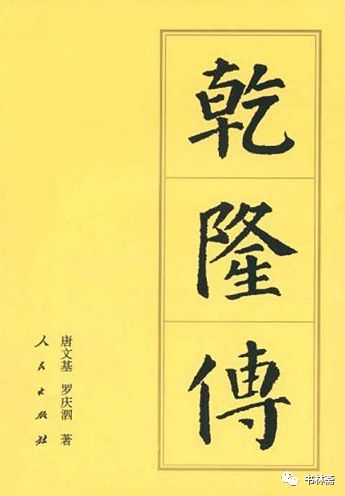
不少朋友问下篇写不写乾隆,其实是不打算写乾隆的,在翻阅了乾隆的评传后更确定了这个想法。
我个人对乾隆是颇有些好感的,这种好感来自这个人身上的某种矛盾性,一种始终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矛盾。
他爷爷比他清醒,所以也没有他直接;
他父亲比他冷峻,所以也没有他宽厚。
换言之当他面对存量时,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准噶尔部问题、粮食和银钱问题、八旗农奴问题、党争问题、金川问题、大小和卓问题,这些问题他都能处理得很恰当,但在乾隆的时候,他要做的不只是把这些问题处理恰当,所以他把问题留给了儿子。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不管留不留给儿子,都没有时间了。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清史稿》没有提及、而在《续修陕西通志》里记载的一个人:杨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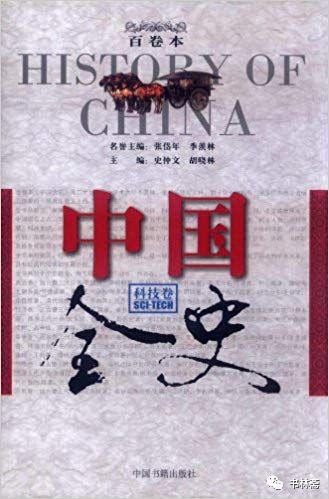
说有清一代,科学技术毫无进步是不对的,在漫长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清代的技术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这里只聊鸦片战争以前,这时的技术进步尤其体现在农学、医学、解剖学、地理学、水力学上。
数学、物理学和化学也颇有一些进步,不过这些进步很多是来自西方的译本,而非中国自发。但毕竟也有民间自发的情况出现。孙云球名不见经传,是中国独立发明望远镜第一人;黄履庄是机械专家,发明的温度计、探照灯、显微镜、螺旋水车等在农田灌溉上作用很大。
我们看到,这些发明往往都集中在两个字上:农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阻碍了技术的进步。
一方面,地主不劳而获的现实把社会上更多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封建地租剥削上来;另一方面,农民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越发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生产量。于是,封建土地制度和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得以长期存在。此外,农民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他们不能进行农业的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只能依靠劳动集约,这就决定了农业发展潜力的有限性。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得农业无法更多地向城市提供商品粮及其他农副产品,无力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城市发展缓慢,也就制约了科技的进步速度。
此外,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不能归结为某个具体对象的短视,恰恰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西方大航海的内在动因其实归根结底是中国的河西走廊关闭了,这一举动直接引发了亚欧乃至非美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而东亚的古老帝国对此一无所知,当它知道时,这个世界已经翻天覆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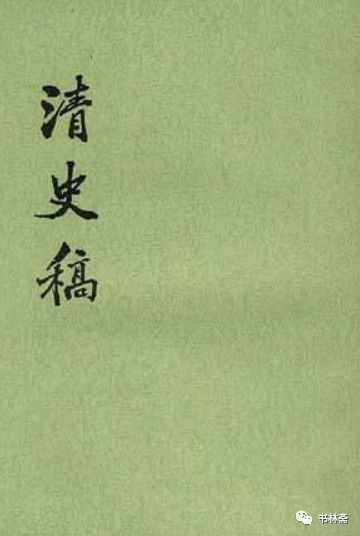

很扎实,与言少说霍元甲的一篇文章可称双壁。
言少重材料,石健重分析,因此虽然二人在对霍元甲的一些内容有出入,但都是罕见的可以对霍元甲进行还原的好文章,而不是将霍元甲泛泛而谈。
在石健的这篇文章里,霍元甲的起家和近代史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从小农经济的破灭到脚行的兴起,从帝国主义的入侵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合力,从小处入手考证,到大处发散升华。
尤其是叙说霍元甲与英国大力士(言少查原始材料后认为是美国)、日本柔道者的两场比武,作者亲自去往当年的发生地进行考证,并挖掘出了许多细节,从而引出两场比武后面的大背景,串起一条大脉络,读来十分过瘾。
如果说有什么美中不足之处的话,那便是在考证后,也许是因为原始材料的欠缺,作者将霍元甲迅速提升到了民族精神的层面上,中间缺乏过渡,略有些突兀,若是能补齐这段考证,使之更加扎实,那便更好了。
叶曙明《广州辛亥年1911:三千年大变局之策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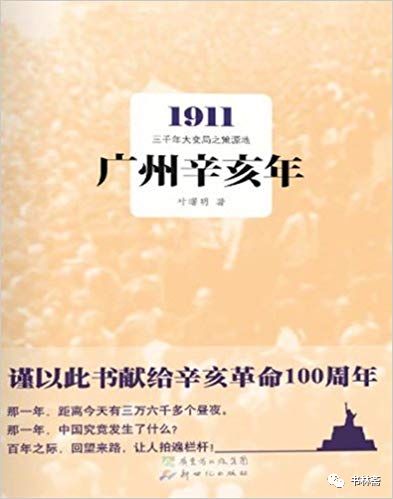
1910年,湘西一代暴雨滂沱,湖北公安一带荆江决堤,受灾者多达百万余人。
很多人以此作为天象,天灾不是问题,天灾过后朝廷没有钱和人来救灾才是问题。
大清以前是很有钱的,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这使得大清的基层治理非常成功,也因此清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地方名流、缙绅、商人的广泛支持,尤其是商人,无论是在通过票号兴盛的晋商,还是和朝廷财政息息相关的徽商、陕商与淮商,亦或是受到全球潮流影响的粤商,都逐渐兴起。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一年的出口总和和进口总额比乾隆朝也足足增长了六倍。而《辛丑条约》以后,商人们开始离心离德,地方自治被提了出来,核心就是,朝廷没钱了。广州七十二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一个新的阶级雏形就此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就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切和他们无关。但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此会对同盟会排斥——
黄兴在广州的统筹部筹集到了几万元钱,这些钱大都是粤商资助的,而后湖南来的谭胡子从黄兴手里拿到了两千元,谭胡子又把其中八百元钱带到了湖北武昌。
武昌的成员用这笔钱在汉口的俄租界租了房子,这正是武昌起义的商议地点。
10月10日,湖北武昌;10月22日,陕西西安;10月23日,江西九江;10月29日,山西太原……
那么广州呢?广州是全国唯一一座和平易帜的省会城市。这是因为当地总督与广州绅商达成了统一战线,而为何能做到呢?一是因为绅商和同盟会成员本质上属于同一阶级,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二是因为广州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绅商甚多,足以发出声音。
于是最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也能看到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不能彻底成功的。
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那些小细节处,1910年各地的灾害还带来了一个后果:这场风波引发了长沙的抢米风波,这使得湖南很多贩米的人家卖不出去米。
这其中有一家住韶山,这家主人参加过湘军,后来拿了一笔钱回家做起了卖米的生意,而就在这场风波后,这家的境况便大不如前了,而这家主人的儿子也因此被推到了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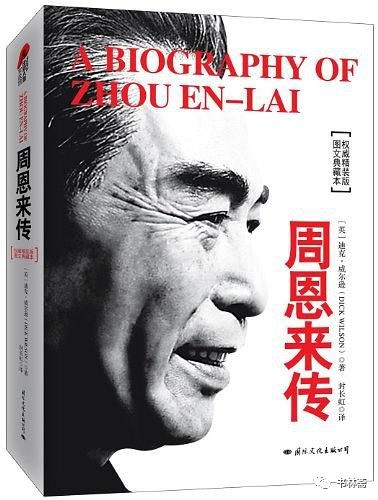
作者对传主的好感可以说是远超旁人的,你很难在一个外国人的评价里看到他对某某某的完人评语,但罕见的是这一位是同时赢得中外赞誉的,单凭此,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一件事:
他是与众不同的。换言之,他已经是与众不同的符号化,而不仅仅是一个个体了,尽管作者尽力如此,但读者还是会不自觉地想到许多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不连贯的、无逻辑的,但潜意识一定指向两个字: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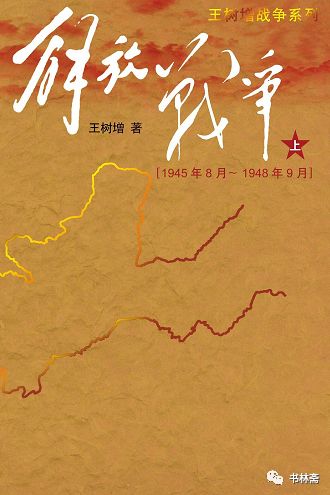
解放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政治的胜利,政治的胜利影响着军事和经济的双重胜利,于是解放战争在单单看战争可能要打二十年的情况下只打了几年。
谁先呼吁和平,谁就掌握主动权。这是第一层政治。
谁先真正争取到了民主党派,意识到民主党派的本质,并且同时意识到中国的本质,谁就争取到了最重要的中间盟友。这是第二层政治。
谁先实行了土地改革,谁就真正进行了民主动员,谁就真正发动了群众。这是第三层政治。
那么结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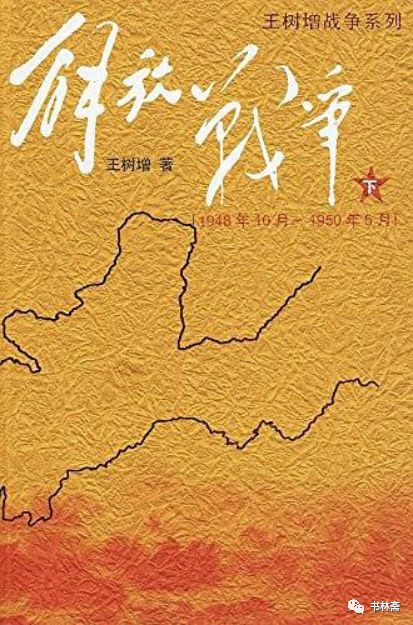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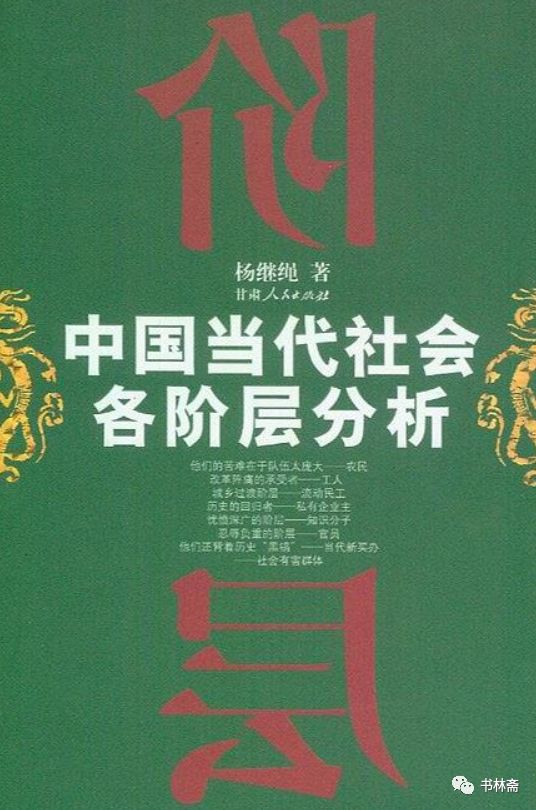
对于聊不到本质的社会学理论,读来总是令人抓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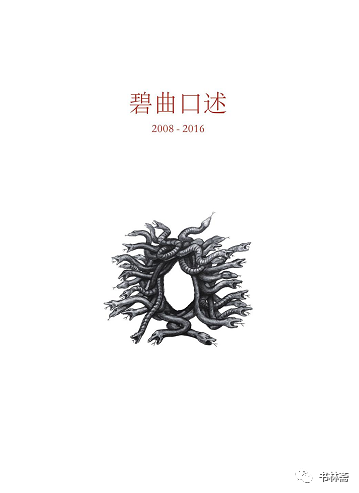
一个性工作者的自述,天然的剧本人物小传,大量的心理描写,也许真的,也许假的,但毕竟是当事人的自述,许多细节,关乎人的,关乎身体的,都是天然的创作素材。
我闻到了血的味道,它的名字叫罪恶,它诞生于令狐冲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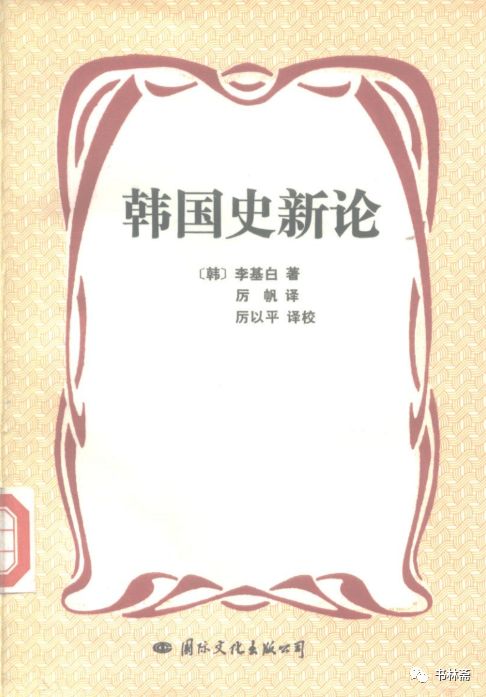
初读外国国史,最重要的一点是比较了解中国历史。
或者该国与中国交往密切,或者牢记每一百年中国大概发生了什么,只有如此才能清晰比较在他国发生何种事情时,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阅读半岛史就有这样的熟悉感,也因此尽管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却总能读出亲切感,从新石器时代到后来卫满、三韩辰国、汉四郡、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朝鲜乃至今天的半岛局势,只要牢牢以中国为一条准线,则可迅速粗略地了解半岛史。
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中国文化(包括各少数民族)辐射圈下最重要的代表,半岛和中国的交流实在是太频繁了,归降、朝贡、屈服,历史总在不断徘徊,几乎半岛的每件大事都受到中国的影响,在阅读时就好像在阅读自己的历史一样轻松,也因此本书的阅读难度极低,而价值甚高。
那么,今天半岛为什么是半岛呢?每个半岛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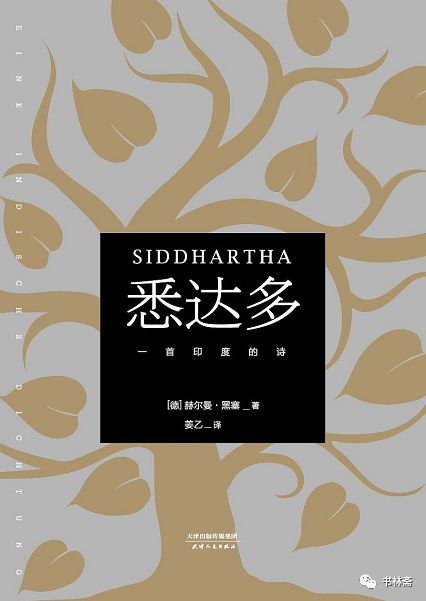
乔达摩是乔达摩,悉达多是悉达多。
悉达多曾向受世人敬仰的乔达摩问询,却最终离开了乔达摩。
悉达多不知道去向何方,悉达多在寻找自己。悉达多开始体验人生,他沉沦其中,最后在一次欢好中觉醒。
悉达多最后成为了一切。
——这是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姜乙的译本文字上是很好的,但读来仍旧会对黑塞的表达充满着质疑。质疑不是疑惑,疑惑是不理解,质疑是不认同,心灵上的安宁是无法通过与自然的和谐而达成的,在这一点上我深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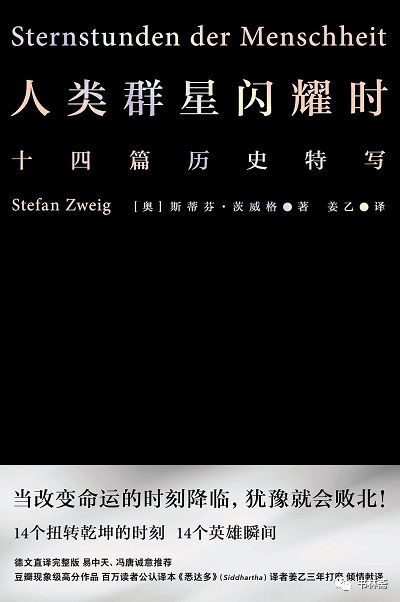
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因为历史已经走到了这里,这样的瞬间是必然的且必要的,而作者笔下的选材,则被视为独一无二的,这是从阅读序言时便不甚同意的地方。
读了前三篇,发现丝毫没有被宏大历史的精妙瞬间触动到的感觉,也许我和作者关于隽永瞬间的认知是有差别的,我所喜爱的是先师十四年后反鲁、孝文见到乌鸦叫的洛阳和主席听着《贺金缕》送别董老的这些画面,是曹丞相看着关公头颅后不久就去世、文丞相在土屋里待了三年还在求死和阎典史站在城楼上就是不肯剃头。
这是我心里的群星闪耀时。
汉斯-格奥尔格·梅勒与德安博《游心之路:和现代西方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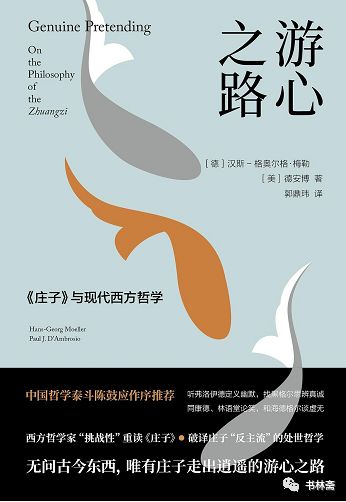
作者很喜欢海德格尔,或者说不是作者喜欢海德格尔,而是作者很认同海德格尔对《庄子》的解读。
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尽管是否存在中国哲学还需要商榷)习惯性用他们比较熟悉的规范话语,因此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新概念,而这些新概念的整体,作者则发明了真实假装理论来嵌套。
但作者却又一次犯了西方人常犯的错误,忽略了《庄子》等文本的诞生过程,这一点是极重要的。如果把《庄子》作为一个永恒的整体文本来看,那么它确实可以被建构一种哲学理论,并加以进一步探讨;但如果《庄子》的成书本身就是多元的、多时空的,那么对它进行的任何一种整体架构,都逃脱不了《庄子》最初成书时的概念。而很显然,《庄子》属于后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属于西方版《庄子》注我。当然它最具有价值的部分来自分析《庄子》里哲学幽默的章节,通过对浑沌的分析,构建出了幽默的本质,这一章读来是颇有趣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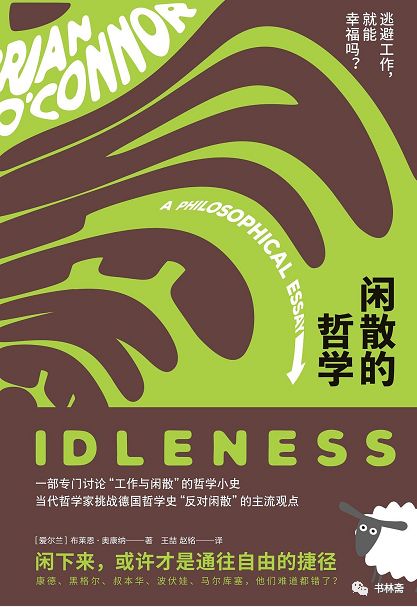
读到第四页时,看到作者表态说,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要阻止那些反对闲散的哲学论点一家独大。
心想,这莫不正是在反对我的观点吗?
随后读到了第五页,作者继续说,有些读者可能不大同意他对人类必须为远为闲散更为重要的目标而奋斗这一观点,他也不指望规劝这类人重新思考应否对闲散怀有期望。
看到这句话,我已确认,作者向读者反对的,正是我这类人群。既然如此,不妨好好看看作者都说了啥。
作者说,闲散无须律己,无须自我调控,无须为了克服或改进自己的某些不足而进行心理斗争。听起来很对,但如果我们全局来看,那么一部分人的闲散,本身就是对另一部分人的不公平,一部分人的岁月静好,背后是另一部分人的水深火热。
读到后来发现,作者批判的仅是将闲散视为非理性的那一批人,我辈自然不在其中。然后作者批判了伯顿、康德,紧接着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这倒是顺着这一支哲学的发展脉络。随后作者又接连提及了叔本华、波伏娃、席勒……
终于在最后一章,作者揭露了自己的最真实想法:闲散即自由。事实上,单凭《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里对麦克斯·施蒂纳这样的青年黑格尔的批驳,用来反驳作者便一点没有问题,甚至还有点大材小用。
这本书要是放在十几年、二十几年前会有年轻人很认同,放今天,没有,因为这个世界不会给年轻人思考是否认同的时间。
令狐冲也许会喜欢,正如同那个人会很喜欢令狐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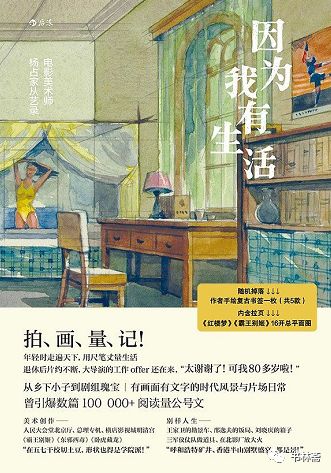
这本书读得我很过瘾,作者杨占家是电影美术师,曾经给《霸王别姬》《东邪西毒》《诱僧》《卧虎藏龙》等电影做过美术设计,本书是他的回忆录加口述,行文很是真诚。
本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杨占家做电影以前,那时他的命运随着时代大势起伏不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时代细节;后半部分是杨占家开始接触电影,这里有许多拍摄电影时的珍贵材料,不管是专业方向的还是茶余饭后的,都很值得一读。
杨占家是一个匠人,他以「因为我有生活」为书名是有用意的,因为当有后辈问他为何画图这么快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因为自己有生活,有积累,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用时不用想,伸手就画出来,甚至尺寸都记得,而没有随手画和量经历的人,就算用电脑拼出来,导演也能一眼看出那是个假把式,花花绿绿,没有灵气。
有趣。
弗朗西斯·达科斯塔《重构物联网的未来:探索智联万物新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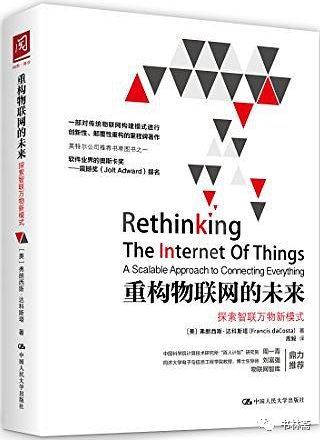
离开学校四年,再读这类书我已经有些吃力了,长期浸淫在文史类阅读中,把老本行甩到了脑后,虽然没有计算公式,但我已经需要仔细思考而不能迅速理解了。
话不多说,总之,作者区分了物联网与传统互联网之间的不同,并得出了结论,在大量微小设备接入网络时,传统的IPv6协议就不适用了,因为需要海量的终端,但计算量不大,因此成本不合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引入了全新的兼容IP和一个新概念,试图用这个新的协议来让物联网更好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这个设想在理论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怎么样,我现在还没法给出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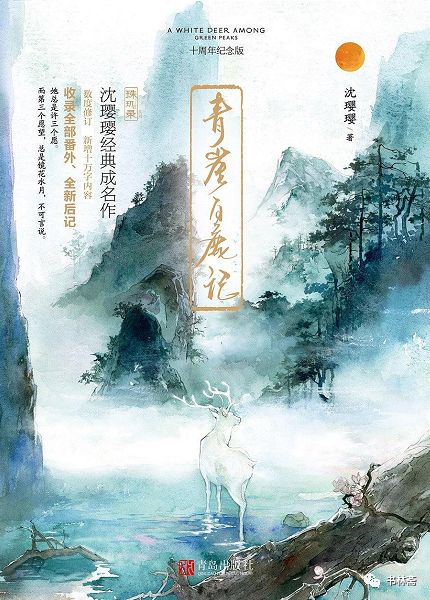
字里行间有中学时代读《听雪楼》《忘川》《步天歌》这些小说时的感觉,但如今再读,已经失了乐趣,没有了想法,归根结底还是十年过去时间了。
书出了十周年纪念,我也长大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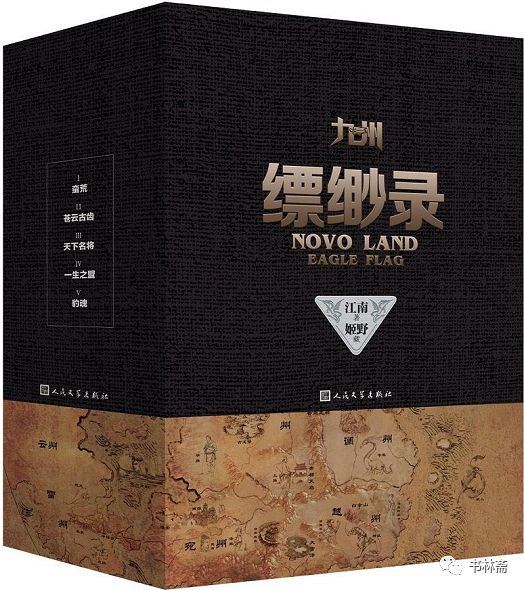
江南在新版自序里说,如今想来,没写开局而先写结局并不是因为我已经想透了这个故事,只是因为心太躁动,忍不住要略过开头和过程直奔结局,字里行间都是火山般的孤单和渴望,还有少年时无端的爱憎。
情绪。江南是一个笔端很细腻的人,尽管这种细腻在近来的作品里屡屡演变为油腻,但在《此间的少年》《九州缥缈录》《上海堡垒》和《涿鹿》中,你会被那种被称之为怅惘的情绪牵着走。每一个心思敏感的人都会不自觉地陷入其中。
所以江南无比痴迷《百年孤独》的开篇,许多年之后云云,这种几种时空跳跃后的咏叹感,构成了本书的情感基调,无论后面是否波澜壮阔都无法扭转这种情绪。
因为这种情绪的名字是失去,未来的这些人会失去一切。
而后几卷真的波澜壮阔吗?答案是否。江南写得最好的仍然是人和人的情绪。
所以读到第三卷《天下名将》时,我还是弃了,和很多年前的那次阅读说拜拜。
趁着电视剧播出,把这几本又快速过了一遍,对比戏剧改编和原著内容,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故事,但这里面的故事并不多,压缩一下,故事点其实也就那么点,但当情绪扩充起来时,就铺满了六本书——还坑了。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阅读原文处可查看文章集锦。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