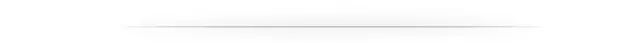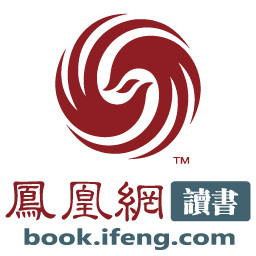本文选自《美味的欺诈》
[英]比·威尔逊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本书揭示的是一个充斥着卑鄙与贪婪的黑色故事,通过造假历史、食品政策、烹饪揭秘等内容的有趣混搭,比·威尔逊向我们展示了造假的各种险恶手段、助长奸商涌现的风气、科学蒙骗与科学监查之间的激烈对抗、为建立值得信赖的食品标准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同时也歌颂了那些食品侦探、打假英雄,他们调查厨房里的黑幕,用毕生的精力告诉人们,他们吃下去的究竟是什么。故事生动有趣,意味直指人心。
作为工业化城市中流行的顽症,食品造假在英美两国也曾风行一时。彼时彼地的人们,同样也是苦不堪言。两国如何应对、情况如何好转,不仅值得借鉴,更可引人深思。
作者:
比·威尔逊(Bee Wilson),英国著名食品作家和历史学家,多年来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担任思想史研究员。她曾在英国时政周刊《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担任了五年的美食评论家,自2003 年起,每周都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的美食专栏发表文章,其作品屡次获奖。2004 年她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著作《蜂群》(The Hive)。
德国火腿和英国芥末
◆
◆
◆
文 |
比·威尔逊

令边沁迷惑,令拿破仑害怕,
令阿库姆震惊……
——詹姆斯·史密斯(JamesSmith)《牛奶与蜂蜜》,1840年
食物掺假的历史以1820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阿库姆时代与后阿库姆时代。1820年,现代西方世界首次针对食品中添加有毒物质或添加剂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打击,而这正是由于一本小册子的面世——《论食品掺假和厨房毒物》(A Treatise on Adulterations of Food,and Culinary Poisons,后简称《论掺假》),由德裔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阿库姆(FrederickAccum,1769—1838)撰写。说这本书改变了一切可能有些夸张。
此书出版后,骗子们依然制假售假,逍遥法外;有关食品的法律法规也并没有因此而进行任何改动。一开始阿库姆本人被授予了各种荣誉,后来却遭人侮辱。但他的文章还是让人们认清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现代化工业城市中出售的食品或饮品都不如看上去那样美味,其制作方法也和我们想象的不同,而且食物是可以杀人的。
弗雷德里克·阿库姆出生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却选择成为一名伦敦人。他热爱食物,推崇品质优良的健康面包(全麦面包,而不是白面包)、烟熏火腿、浓郁芬芳的黑咖啡,以及用熟透的桃子、樱桃、菠萝、榅桲果、李子和美味的橘子1制成的果酱或蜜饯。阿库姆对食物的态度和法国美食家不同,他们无论吃什么东西都要先用鼻子闻一下,一见到鹌鹑配松露就吃到顾不得讲话。
阿库姆却并不热衷于名贵的食
物,更喜欢吃德式食品:一品脱麦芽啤酒,一碗用冬季白甘蓝和葛缕子籽做的德式泡菜,一份酸黄瓜配西班牙甘椒,一张松脆的奶油馅饼皮,这些都是他喜欢的食物。但阿库姆选择食物时并不随意,他强调说如果你对煮土豆都非常讲究,那么在牛排的调味上一定会精益求精;只有那些势利小人才会滥竽充数。他认为,厨师就好比化学家,厨房则好比是一间化学实验室。阿库姆是鉴别食品掺假的行家,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也就是1820年,他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化学家。
作为一名热爱美食的化学家,阿库姆认为美食成功的关键在于所有成分必须精确混合,同时也正因这种热爱让他对那些“品行端正”的罪犯们为追逐利益而在食物中掺假的做法十分愤慨。幸运的是,阿库姆并没有忍气吞声,他将愤慨都写进自己的书里,向世人揭露掺假售假的骗局、数不清的掺假食品,以及黑心商人最恶毒的谎言和最严重的有害物质。“打击食品掺假很困难,”他写道,“这个国家制假成风,有的食品,甚至从来就没有过真的;但说起来却只有一篇关于食品安全的文章。”2阿库姆的著作面世仅一个月就售出了一千册(这个发行量在当时已经很大了),之后又陆续卖出数万本。
如果现在再读有关阿库姆这篇论著的评论,联想到大宗食物都在制假售假,恐怕谁都会突然泛起一阵恶心。“读了(阿库姆的)这部书后,”《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的一位评论员曾写道,“我们的食欲明显下降,昨天我们脸色苍白地吃下了一块奶油冻。”3另一位评论员在《文学公报》上发表文章,抱怨道:
这本书揭露了食品商贩是怎样欺诈、哄骗、下药甚至伤害我们的。虽然人们读这部书时会觉得很痛快,但是读过之后,他们可能会被阿库姆先生所做的这项伟大工作气个半死。他的确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但是读过他的书后,我们可能什么都吃不下了。
他继续感慨地说:
我们吃的泡菜是用铜染绿的;我们吃的醋是用硫酸勾兑的;我们吃的
奶酪是在坏了的牛奶里掺入米粉或木薯粉制成的;我们吃的糖果是
将糖、淀粉和黏土混合在一起,再用铜和铅染色的;我们吃的番茄酱
是用蒸馏酒醋后剩下的糟粕加上绿色的核桃外壳煮出的汤汁以及各种香料、
辣椒粉、甘椒和普通的盐——或是卖不掉的烂蘑菇混合而成的;我们吃的
芥末是芥菜、小麦粉、辣椒粉、海盐、姜黄和豌豆粉混合在一起调成的;
还有让我们喝下去就觉得精神振奋、精力充沛的柠檬酸,柠檬汽水和潘趣酒(punch),
它们通常是使用廉价的酒石酸临时勾兑出来的。
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阿库姆的这本书。他在书中号召所有阶层应相互合作,废除掺假食品及饮品的罪恶交易与诡计。书中揭露了许多食品掺假案,比如在儿童奶油冻中掺入有毒的月桂叶,用黑刺李的叶子冒充茶叶,用白黏土制成含片,在胡椒中掺入灰尘垃圾,泡菜用铜染绿,糖果用铅染色等等。
“上帝啊!”一位读者惊呼道,“这些无耻的掺假行为何时才能结束?
难道我们的餐桌上就没有一样纯正的、无毒无害的东西吗?”
事实上,阿库姆没有揭露的丑闻,依然我行我素。这让读者感到震惊与错愕。一直以来,还没有一本化学书能够像《论掺假》一样,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
这种震惊效果正是阿库姆想要的。书名页上不但画着一个骨灰盒,同时还用大写字母写着“此处有暗藏的危险”这样一句座右铭。骨灰盒上蒙着一张画有巨大骷髅的裹尸布,两条大蛇在骷髅旁边扭动。他在《论掺假》中不断地重复着“暗藏的危险”这个主题,它源自《圣经》中“锅中有致死的毒物”。[这句话出自《圣经·列王记》(Kings),第四章,40节。]“暗藏的危险”成为19世纪食品安全运动的战斗口号,但却远远不能承载阿库姆想要表达的尖刻的道德抨击
。
他对掺假行为十分厌恶。制假售假是一种恶劣的行为,不仅是那些生活奢侈品,就连基本必需品也存在这一现象。面包师为了让面包看着很白,常会在面粉里掺入明矾。掺假背后的动机正是对财富的渴望和贪婪,贪欲压倒了一切,赚钱比同胞的生命还重要。6阿库姆忧愁地说道:“在有生之中我们处于死亡。”
为什么阿库姆的论著能够引人注意呢?1820年以前,人们对于食物掺假一事也并非一无所知。正如阿库姆在前言中所说,每个人都知道面包、啤酒、葡萄以及其他经常掺假的东西。8恐怕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酒商往酒里掺水或用医用酒精冒充其他酒类的案例。
19世纪,就在阿库姆出书前
后,出现了无数有关食品污染的谣言与讽刺。托拜斯·斯莫莱特(Tobia
Smollett)在他的小说《汉弗莱·克林克》(HumphreyClinker)中就曾描述过伦敦的食品是多么肮脏、低劣。他将伦敦比作简陋的乡下,因为伦敦城里鸡鸭猪狗到处跑。
后来游戏规则变了,蔬菜、草药、凉拌食品都出自自家的花园。正如他所描述的,在伦敦,人们在草莓上吐点儿口水再擦擦就算是洗干净了;将蔬菜和铜一起煮,使蔬菜显得更绿;装牛奶的提桶也没有盖儿,这些牛奶穿过大街小巷,早就被“婴儿的呕吐物”“行人的唾沫、鼻涕和口嚼烟草块”“车轮溅出的泥点儿,尘土以及男孩儿们恶作剧时乱扔的垃圾”所污染,有时牛奶里甚至“还漂着淹死的蜗牛”。伦敦的面包就是“掺有白垩、明矾和骨灰的毒面团;吃起来干巴巴的,简直就是对人体的摧残”。葡萄酒则是“将苹果酒、玉米酒、黑刺李汁随便混在一起,调成的一种非常难喝且有害身体的廉价混合物”。
伦敦的食品真的很糟糕,可是读过斯莫莱特这部小说的人,谁也不会相信现实情况竟然真的像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恶劣。所有人都以为,小说中的情境是作者为了营造喜剧效果而故意夸大的。不难想象,当第一批读者读完阿库姆的论著后,发现“喜剧”中的情节竟然是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他们该有多么吃惊!《文学公报》的编辑曾给出以下评论:
《汉弗莱·克林克》中,那些异想天开的骗子总能引得我们发笑,但是回头想想,现实生活中我们吃的喝的东西几乎都被掺了假,似乎我们就笑不出来了。我们只能自己咽下这些骗人的假货,否则,这些卑鄙的掺假食品以及那些残忍的商家的无赖作为,最终会削弱主要城市的运营情况乃至国民的许多消费能力,令社会失去活力,或者使人与人彼此厌恶。
阿库姆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能让读者们看到“咽下欺骗的苦果”的确是“相当严重的玩笑”。他的书之所以卖得很火,一方面是时代的原因,随着科学与工业的进步,食品掺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阿库姆本人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宣传家,他是戳穿这一连串诡计的最佳人选。他对现代英国科学及工业的发展充满激情,同时也看到这些科学和工业技术应用于食品行业后发生的许多可怕的事情。
这本《论掺假》,讲述的是一场科学欺诈与科学检测之间的战役。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此番争斗已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