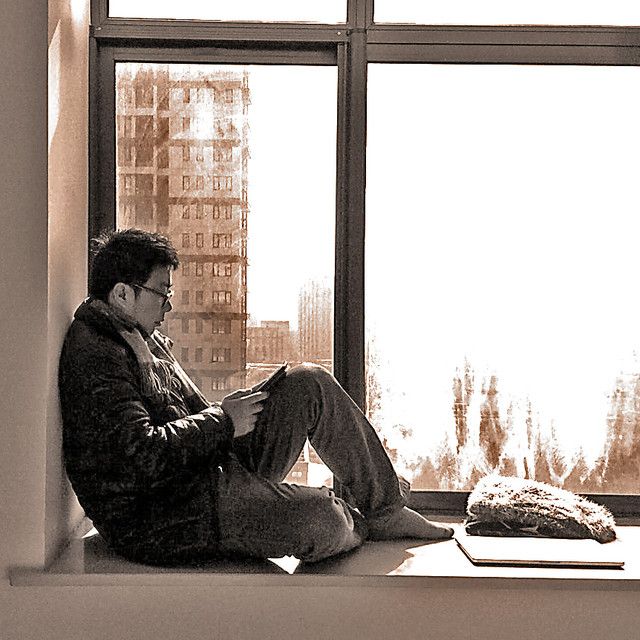图片摄于蒙特勒,西庸古堡。
按:这两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在知乎上被很多人关注,找来找去才发现在一个关于正则表达式的问答里,我的朋友Milo Yip在回答中提到了我写过的《正则指引》。正则表达式我已经很久没写过了了,但以前的书本还能给其它朋友帮助,这很让人欣慰。也更让我感到,对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和事,不管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应当心怀感念。
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与历史有关系,因为对历史根本不感兴趣。在我的认知里,历史是和地理一样,需要死记硬背的学科。而真正重要的是理科。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虽然高中阶段分理科分班,但无论文科还是理科,大家都是在混乱和兴奋中度过的,许多经历今天想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比如寒暑假一补课就有人举报甚至上电视新闻,比如高三了每天仍然只能安排六到七节课,比如到最后一学期毕业年级的老师为了反对学校的某项安排集体罢课一周……
高考之前,学校放假让大家回去好好调整,用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我和几个同学跑去电脑房(当时还没有“网吧”)打Quake3,吹空调到有点感冒,急坏了父母。要考试了,相当多的人还和上学一样,自己骑自行车去了考场,有些家长在学校附近包了宾馆的住房,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结果成绩出来,其它科目还算发挥稳定,唯有数学从模拟考试的140多分直降到88分。虽然比重点本科录取线高出接近40分,但第一志愿没有上,我还记得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就站不起来了。然后就是心急如焚地地打听消息,等各种安排,尤其是看到其他家长大显神通弄到“机动指标”之后欢天喜地,更是焦急万分。
幸而有天忽然来了消息,
211高校
东北师范大学在我省没有录满,收服从分配的考生,可以保证专业对口。于是,我就这样跨过长江,跨过黄河,跨出山海关,来到了长春。
专业是我心仪的计算机,学校却是我没想过的师范类。那时候同学通讯还得靠信件,每次收到同学们寄来的印着各种“工业大学”、“理工大学”字样的信封,都觉得羡慕又无奈。加上大一的很多基础课程是为从未接触过计算机的同学开设的,对我来说味同嚼蜡,失落的感觉就愈发明显了。
不过很快,我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学校的公告栏里总会有各种讲座的通告,尽管这些讲座并不是理工科的,但题目也相当吸引人。有一天我看到历史系的讲座通告,题目只有四个字: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希腊能有什么精神呢?我只能想起一些希腊神话,再有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时说的:言必称希腊。无论如何,且去听听他们能讲出什么花来吧。
那时候的教室都很传统,长条形,长方凳。黑板上写着四个字:希腊精神。主讲人姓周,三十来岁年纪,当时应该还是讲师。虽然是课余讲座,但信息饱满、激情澎湃。一方面按照希腊的历史展开,另一方面又分文化、政治、军事几条线分别叙述。梭伦、伯里克利、诡辩学派、温泉关等等名词,都是我第一次听说。尤其是把不同的主题串联起来的讲法,让我感到非常新鲜——在讲到希腊人热爱运动的时候他忽然问:为什么镇守温泉关的只有三百勇士?看到下面没有人回答,他才给出答案:因为其他人都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了,所以我说希腊人热爱运动嘛。
还有两个片段讲得绘声绘色,让我记忆至今。第一个是讲波斯国王大流士问一个被俘的希腊人:你看我驱使的百万大军,什么时候能踏平希腊?答案是:你永远不可能得逞,因为你的大军只是努力,只要你体验过自由的滋味,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保卫它。第二个是讲到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本来已经用若干例证烘托,再加上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对比,印象就更深刻了。
讲座听完不过瘾,还有提问环节,整个提问环节的气氛也相当热烈,哄堂大笑也是免不了的。提问环节之后,还有机会——那个年代私车还不普及,很多老师都是走路上下班。所以讲座结束之后,我追上主讲老师,一边聊一边陪他走出校园。说来奇怪,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也不因为我是理科院系的就见外,也不因为不认识我而有戒心,而是一路走一路讲,所以我听到了与《新闻联播》完全不同的关于南联盟和科索沃的故事,他听我说看过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便推荐我去看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我记忆至今。
那个晚上过去,整个世界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后来我便时常留意历史系的讲座,那段时间历史系的讲座开得也确实多,每周都有一到两个晚上安排讲座,所以我一遇到就放弃晚自习去参加,也确实受益匪浅。
有次讲座是一位老教授讲明代史。因为我之前看过了黄仁宇先生的书,所以
讲完
我举手提了三个问题,他的答复却是:“你的三个问题一个一个说,我的脑子容量有限,一下子记不住三个问题,只能一个个来。”往常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也有不少人会想一些“体面”的办法引导提问者一个个提问题,但身为教授,能够在学生面前坦率承认“我能力有限”,我却是第一次遇到。那一刻我忽然发现,坦率承认自己的局限并不会让自己丢脸,反而会获得更多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