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发自公众号
作書
刊发已获授权,在此表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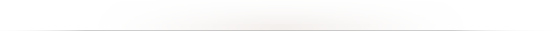
不知道为什么,这篇原发于“做書”,且依然可以正常打开的文章,无法通过审核转发出来,所以,大家请点击粗体字自行跳转看原文的导读吧。
01
当我们为痛点找到共鸣时,
城市正在死去
当人们正在疯狂搜索这个城市人群的共同痛点,绞尽脑汁想找个词把多少千万人一言以概括。
我却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中读到了一个和北京差不多“可恶”又活力充沛的纽约:
纽约人每分钟眨眼28次,但紧张时每分钟可能要眨40次;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0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镑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市,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和塑料假眼行走。
本书中你会读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平庸无名,但琳琅满目,在普通生活中五光十色,连纽约的野猫都是说不尽的都市奇谭。

纽约的清洁女工像女巫:
从夜色降临到日出时分,这些女人似乎控制着纽约:她们将占据证交所的位子,主宰空无一人的董事会会议室,向那些看不见的广告人挥舞拳头……她们能让摩天大楼里的灯光彻夜不熄。从窗外看去,她们的身影和扫帚来回飞舞,就像一群女巫在施展魔法。
纽约的修桥工人像骑士:
他们在一个地方只逗留一段时间,一旦大桥建好,他们就开拔到另一座城市,去修建等待着他们的另一座大桥。他们把所有的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但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永远孤独、飘零。
强奸服装店陈列模特的搬运工,通宵守候重磅新闻的记者;站在百老汇门口高举”受神谴的人不能上天堂“的女人冲路人大喊大叫,喊到凌晨三点司机会开着1948年的劳斯莱斯接她回家;早晨7点出现的打扮很巴黎的老头,他红光满面,专门为富婆服务……
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它很梦幻也很现实,它敢于包容任何一种人生。这里不仅是纽约,也是北京,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城市。
这个书名也是今年文景举办的“艺文季”讨论的主题——城市: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活动中,关于北京算不算理想城市的讨论,我听到了一个十分理智的答案:
北京的价值不在于已经完成了理想的状态,而是它有一种东西可以吸引你去达到,这种希望,说实话,在中国别的地方还没有看到。(唐克扬)
02
我们是被城市化的一员,
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讲座中我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主流媒体连篇累牍说深圳过去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小渔村,一穷二白,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其实是谎言。
在持续的城市化当中,这些村子很破烂,跟城市完全不相融合。每一个新到深圳主政的官员都希望把这个癌细胞除掉。改一轮,深圳很强悍的民间力量就违章一次,你要拆,我就盖四层楼,全村都违章,你再拆我就盖八层。(史建)
这些十分强悍的村落,成了深圳的城中村。有城市高楼,才有城中村的倔强,也成了外地人的新故乡。
在北京有上百个城中村,其中一个曾藏在国贸背后。
这是国贸啊,东三环的富无人能敌,各种外资银行和企业巨型招牌,千万豪车来回穿梭,俯瞰半个北京城夜景的酒廊,人均几千的餐厅,人们讲一句话得串三个英文单词才像样,张口闭口都是千万亿的买卖。化石营村就在这种风光的背后,野蛮生长。

城中村这种存在,在道格·桑德斯的《落脚城市》中被称作“落脚城市”:
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地区,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
那些红爆网络的文章中,从没提到过北京城中村的状况,因为他们在底层吗?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吗?还是因为他们写不出10w+的文章来感动你?恐怕只是因为他们穿着不体面,身上有不好闻的气味,说话粗鄙,他们是外来人,位于城市边缘处,根本不在大众关心视野范围内;还因为他们了解生活不易,茁壮扎根于这个城市,没有心思追随都市小白领的矫情与自恋自怜的小情绪,他们只想活着这件事和如何更好的活着。
心理层面上,每个来大城市打拼的外来人,都是城中村的居民。借用悬挂在北京海淀区的城中村,北四村某公寓楼上贴着的一段话,告慰每位外乡人:
“谁言在他乡,寄身成故乡。”

03
出生的时候那么惹人疼爱,
为什么临终时只剩下自己
讲座第四场主题是:当代都市人的社群认同与认同危机。这场讨论很好的解释了,当我们面对“多少千万的假装生活”时,为什么那么容易被煽动情绪,丧失主见。
现代都市的社群分为两种,现实与网络。
本地人在北京,有家人有家族,有发小还有同学。外地人孤身漂泊,只能重新建立社群,切断了乡愁后,就成了一个孤独漂浮在大城市的个体,他们渴望被了解,渴望同类。但虚拟网络中,籍贯是虚拟的,身份是虚拟的,没有血缘姻亲,人们很快就能达成“虚拟共识”——我们在虚拟网络中找到了自己的新“故乡”:同样失去故乡的你我他。
所以,在网络中广泛流转的情绪化言论,也许只是在大城市中难寻归属感的一种孤独和焦虑。
在《无缘社会》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孤独的大城市——东京。节目组着手做时,发现采访难度很大,因为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成了连警察都放弃的悬案,当他们担任起警察的工作,进一步调查发现:
后来死者身份渐渐明朗时,我们才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无缘社会》)
我们这些人啊,都抱着一个想法:如果是自己的事,还是不要去麻烦别人为好。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咬牙坚持下来,觉得失落孤独,又以此为荣,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切断了与他人的“关联”或“缘”:
所谓“关联”或是“缘”,难道不就意味着互相添麻烦,并允许互相添麻烦吗?(《无缘社会》)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无缘社会。
坚持着“没有不能上电视的话题”的“NHK特别节目”组,从几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开始,挖掘城市“孤独”的话题:
“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的想法曾像别人一样,想恋爱,也想结婚。可是,我经常换工作,收入也不稳定,再加上正好碰上泡沫经济崩溃的当口,工资减掉了很多。我觉得如果结婚生孩子的话,就得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可这样一来,大到教育费,小到圣诞节礼物,什么都得花钱。既然结婚,就要保住自己的家庭,但是不可能保得住啊。”(《无缘社会》)
紧接着,节目撕开了更大的黑幕:”身份不明的自杀者“、“路毙”、“冻死”、“饿死”等等,结果首次获知在2008年一年里,就有32000人“无缘”死去,而这个数字仍在继续增长。
这是一个不能安心养老的社会,不能安心死去的社会。(《无缘社会》)

04
我们如此易变,
因为我们的居住地如此不稳定
在“艺文季”的讲座上,陆铭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大城市现在的现状都不符合大家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是往大城市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他的《大国大城》中得到解答,但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回答,不是我的答案。
在准备来北京读研究生的暑假里,我读到了萨义德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没有直线可以连接家和出生地,学校以及长大成人的地方。所有事件都是偶然事故,所有发展都是偏离主题,所有住处都是流离失所,我们在不可名状的地方逗留,既非这里,也非彼处。
接着我来到了北京,一直待到今天。这段话几乎刻在我这几年的生活里,哪怕毕业时拿到北京户口,和他们享受一样的城市福利,但我们曾生长在不同的土壤之中,我不可能和北京土著一样有归属感:
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凌乱、无人记录,并且廉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关于社会问题的争执,到最后很容易变成地域矛盾,而外来人很可能处于弱势,这可能是大城市最伤人的部分,因为在城市这个文化语境中:
主语“我”是本土的、真实的、熟悉的,而宾语“它”或“你”则是外来的或许危险的、不同的、陌生的。(《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我很喜欢北京,就像那些留在上海、广州、深圳,或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的年轻人一样,沉迷于此。原因和那些微信爆款文说的差不多,但这些爆款文永远不会知道,我在这里,才能遇到旗鼓相当的朋友,势均力敌的恋人,那些文章猜不到也写不出我和这些人之间的故事,我们每天发生的,就是我们不愿离开的根本原因,谁都不能替你讲出来。
最后,写这篇文章,是希望能有更多真挚的文字,记录下我们这些小人物活在大城市的真实样子——残酷的真相,我们可以承受,小而简单的快乐,我们也不会去怀疑。
本文出现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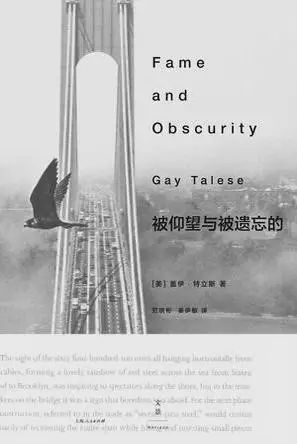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点击封面可跳转阅读《纽约:被忽视之城》)
作者: [美] 盖伊·特立斯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范晓彬 / 姜伊敏
出版年: 20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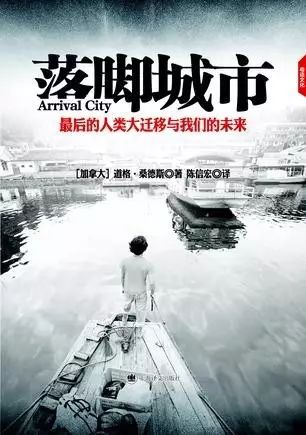
《落脚城市》
(点击封面可跳转阅读《这个落脚城市能够让你落脚吗》)
作者: [加拿大] 道格·桑德斯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未来
译者: 陈信宏
出版年: 2012-2

《无缘社会》
(点击封面可跳转阅读《日本一步步滑向“无缘社会”深渊,我们又还有多久》)
作者: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無縁社会
译者: 高培明
出版年: 2014-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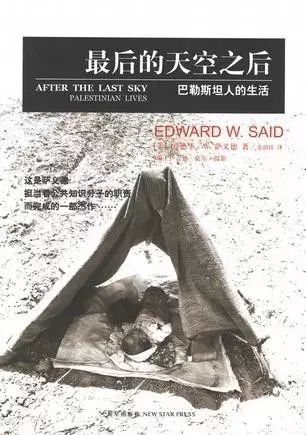
《最后的天空之后》
作者: [美] 爱德华·W·萨义德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副标题: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译者: 金玥珏
出版年: 2006-10
做書原创文章,转载请申请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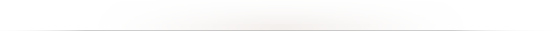
上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