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林庚厚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不平等、金融化、移民和劳动力市场相关议题
梅根·尼利
(Megan Tobias Neely)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工作场所里的性别与种族不平等
金融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助学贷款到购房、经商、规划退休以至其他许多事情,金融时常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决定。这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对社会的不平等有何影响?这是本书的核心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我们探讨了一系列相关问题,包括:金融如何成为高利润产业?它如何改变企业运作?从何时开始,我们的每项决定都像投资决定?而最重要的是,金融如何左右社会的资源分配?
金融的重要性似乎不证自明,我们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金融的世界。但直到1970年代,金融业利润仅占美国经济中所有行业利润的15%。当时金融业所做的,主要是简单的信用中介(credit intermediation)和风险管控:银行接受家庭和公司的存款,将这些资金借给购房者和其他公司。银行也收发支票,方便人们付款。此外,银行也为重要或付费客户提供保险箱,方便他们保存贵重物品。保险公司则是向客户收取保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提供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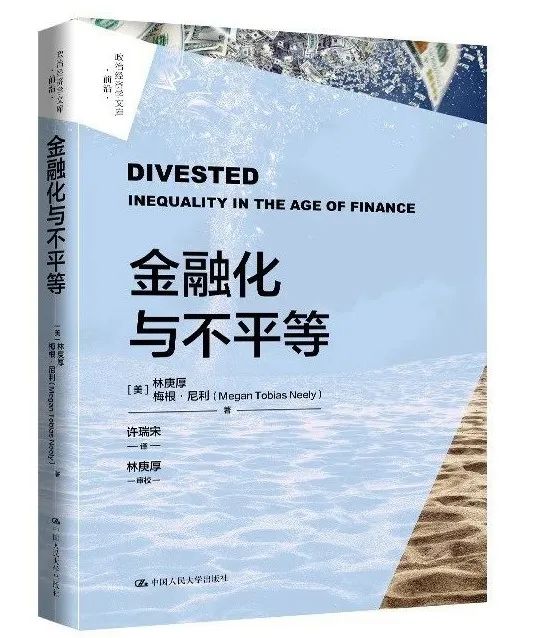
到了2002年,金融业的利润已经大幅增长,占美国经济中所有行业利润的37%。在利润增长的同时,金融业务愈来愈复杂,证券化、衍生商品交易和基金管理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且这些交易多数发生在金融机构之间,而不是个人或企业之间。在金融业对经济的影响日渐深刻的同时,一般民众已经无法理解金融业到底如何运作。家庭、企业和政府所做的决定全都受金融市场左右,但许多金融业务对一般民众却是晦涩难懂。
而在金融业扩张的过程中,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也严重加剧。资本所得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与企业管理层和华尔街人士的薪酬一起上升。同时,反映所得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全职劳工之间上升了26%,大规模裁员成为企业的惯常做法,而非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这些都扩大了贫富差距,造成美国顶层1%家庭拥有全国逾20%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堪比强盗大亨横行的镀金时代。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度缩小了贫富差距,然而,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让金融业迅速度过危机,同时保护了有钱人的资产,但就业却持续疲软,工资停滞不前。
因此,美国社会在过去40年经历了两大相生相息的转变:经济金融化以及严重加剧的社会不平等。本书将说明为什么这两大变化必须一同检视。在当代美国,金融崛起正是不平等加剧的根源。当代金融体系对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一再爆发的金融危机,而是贫富之间的社会鸿沟不断扩大。要了解当代社会不平等,我们必须先了解当代的金融体系。
许多人已经怀疑金融业的发展促成了社会贫富悬殊。在2011年秋天,许多抗议者占领了纽约证券交易所附近的祖科蒂公园,呼吁大家关注华尔街人士与一般百姓之间巨大的财富差距。“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起初要求逮捕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家,收紧对华尔街的规范监管,禁止高频交易,以及调查政治腐败。随着运动的发展,抗议者的要求变得更全面。运动的著名口号“我们是99%”号召美国大众从“另外1%”手上夺回权力和资源;另外1%指的是控制美国绝大多数资本的一小撮金融和政治精英。抗议者将严重的不平等归咎于纽约与华盛顿之间或金融界与政界之间的旋转门,他们认为这种旋转门导致政治权力偏袒企业利益,结果是统治精英大发利市,美国的劳工和中产阶级则陷入困境。
占领华尔街运动起初不受主流媒体重视,但随着参与者着眼于不平等问题和华尔街“1%的人”的巨额财富,这场运动开始在国际上广受关注。始于2011年9月纽约一个公园的小型抗议,短短数周间扩散至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10月15日,运动规模达到顶峰,组织者声称全球逾80个国家共950个城市参与了运动。欧洲的主要都市,例如罗马和马德里,估计有20万~50万人参加抗议活动,美国各地则有超过7万人参加抗议活动。这场运动采用无领袖的运作方式,要求不时改变,因此受到批评,但他们谴责不平等这个核心信息则广为传播。
占领运动最主要的成就,或许是凸显了华尔街如何导致
99%的人与1%的精英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不断扩大。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一般民众与华尔街之间缺乏信任”促使美国在2010年制定《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包括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 rugman)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撰文支持占领运动参与者的观点,要求造成经济大衰退的金融业必须为其贪婪和离谱行为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认识到,经济不平等已成为最重要的议题。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粹主义成功上位。然而,尽管受到严厉批评,并且激起了强大的政治运动,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利润仍继续增长,不平等的程度也继续加剧。
金融“感觉上”的确会加剧不平等。但是,金融究竟如何导致不平等加剧,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金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金融业务非常多样,彼此构成一个互有关联的网络,而且许多金融业务相当复杂,连薪酬丰厚的专家有时也无法提供简洁易懂的解释。金融活动并非仅限于个人利用银行的服务进行付款和投资理财;公司、非营利团体和政府等大型组织,也都利用金融为自身的运作提供资金。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十分多样,包括服务本地客户的社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同时经营商业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全球金融集团,专注于利基市场的精品基金公司,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发薪日放款业者和公司的金融部门。这些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有不同的目标、动机、资源,也都面临不同的限制。此外,因为资金不断易手,当代金融掩盖了资源如何从穷人转移到有钱人手上。
另外,不平等也包含各种分配不均的现象。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赛斯(Emmanuel Saez)指出占比1%的顶层家庭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如何从1970年代末的不到10%暴增至近年的20%以上,让所得集中在金字塔顶端的现象成为讨论不平等时的焦点。这个新镀金时代的重要现象还包括财富不均扩大、劳动所得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下降、工资停滞不前、就业保障受损、工资方面的性别和种族差异持续存在、学生债务暴增,以及长期的悲观与对政府及企业的不信任。
因为这些复杂的情况,相关研究往往仅触及金融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一些零碎面向。本书以此前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更为全面地阐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如何导致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我们提出各样的证据,说明了金融业在华尔街、一般企业和家庭间壮大,如何导致经济不平等恶化。
我们的分析指出金融之所以为恶,不是因为金融专业人士的自负或野心,而是当代金融体系让许多奉公守法的银行业者和基金经理不知不觉地把许多美国家庭推入险境。虽然我们同意华尔街的高薪毫无道理,但金融与不平等的关系不是一句人性贪婪就能带过,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更深广的面向。限制不合理高所得的政策(例如设定所得上限或加强累进税制)是必要的,但是单此不足以解决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问题。此外,我们不认为金融专业人士天生“邪恶”或有其他心理缺陷;就跟其他人一样,金融业者努力追求成功,并且衷心相信因为自己辛勤的付出,领取高薪理所当然。确实有人会为了赢过其他人或逃避失败而作弊,但多数金融专业人士认为自己遵循“规则”,表现优于其他市场参与者,因为自己的技术劳动而得到合理的报酬。
本书认为金融崛起代表的是美国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彻底重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以三种主要方式重塑经济。
第一,金融化创造了过多的中介机构,它们在社会中为金融业榨取资源,但并未贡献相应的经济效益。金融业者发明新的金融产品来满足“潜性”需求,但实际上多数产品仅对金融机构有用。市场影响力愈来愈集中,金融权贵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以及公共政策仰赖私营中介(private intermediation)执行,这三者促进了此过程。金融企业及其精英员工因此掌握了规模空前的资源。
第二,金融崛起削弱了资本与劳动的互相依赖关系,进而削弱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工的议价能力。当一般企业将资源和注意力从它们的核心业务转移到金融部门时,劳工开始被排除在获利过程之外,逐渐失去他们在企业里的价值和影响力。此外,随着愈来愈多资源被用于放贷、投机交易、支付股息或回购股票,就业增长也跟着放缓,对中低级劳工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劳动所得在国民所得中的占比降低,而企业管理层的薪酬却飙升。随着所得差距扩大,雇主与一般雇员的关系普遍恶化。
第三,金融崛起削弱了过去设计用来共同承担风险的社会组织。工会与大型企业集团过去提供就业保障、可靠的医疗和退休福利,有效地为劳工缓冲经济风险。随着这些保障逐渐消失,风险开始从组织转移到家庭身上,导致美国人需要更多金融服务。愈来愈多美国家庭举债度日,并仰赖金融资产保障退休生活。这些金融产品不但将更多资源导向金融业,而且还总是累退的:贫困家庭通常支付最高的利息和费用,富裕家庭则可以动用丰富的资源利用金融市场的波动获利。
通过探讨金融崛起以及其发展如何加剧经济不平等,本书指出高度社会不平等绝非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或不可逆转的趋势。由始至终,我们的分析显示经济发展的轨迹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源自全球层面、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公司层面的一系列政治谈判和制度变革。
有些人可能会说,即使金融崛起导致不平等加剧,金融化仍可能提升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使经济得以加速增长。但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随着美国金融化,整体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企业对厂房、商店、机器、计算机以及最重要的劳工的投资减少,而企业总利润停滞不前。自然,企业对政府税收的贡献也开始减少。写书不只是选择该写什么,也得决定不写什么。本书不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提供详细的讨论。这段历史已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加以探讨。我们采取更宏观的角度,讨论过去40年的结构转变如何助长金融危机并放大其影响。我们着重于美国社会的发展,因为美国在全球金融版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但必须指出的是,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相关变化。我们会稍微谈及这些现象,并在最后一章加以讨论。
虽然金融崛起是不平等程度加剧、顶层所得暴增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认为它是唯一的原因。全球化、科技进步、去工会化(deunionization)、雇佣关系改变、教育差距和政治环境的变化,都与社会不平等息息相关—然而过去的学术研究已经广泛探讨了这些问题。我们认为金融化对理解当代的不平等至关重要,因为它促进并且加强其他各种发展对不平等的影响。
我们必须在此重申,本书受惠于过去和当代的相关学术研究,从社会学到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管理学和历史学。我们冀望在这些学科之间架起桥梁,并将当中的子领域联系起来。我们希望本书能比较完整地说明金融化与不平等的关系,但我们也谦卑地意识到,受限于篇幅,我们略过了许多有重要贡献的研究。因此,任何见解只要听起来有一点点熟悉,读者不需要认为那是我们的原创观点。我们鼓励读者以本书为基础,更深刻探索过去十年出现的丰富文献。
本文选编自
《
金融化与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