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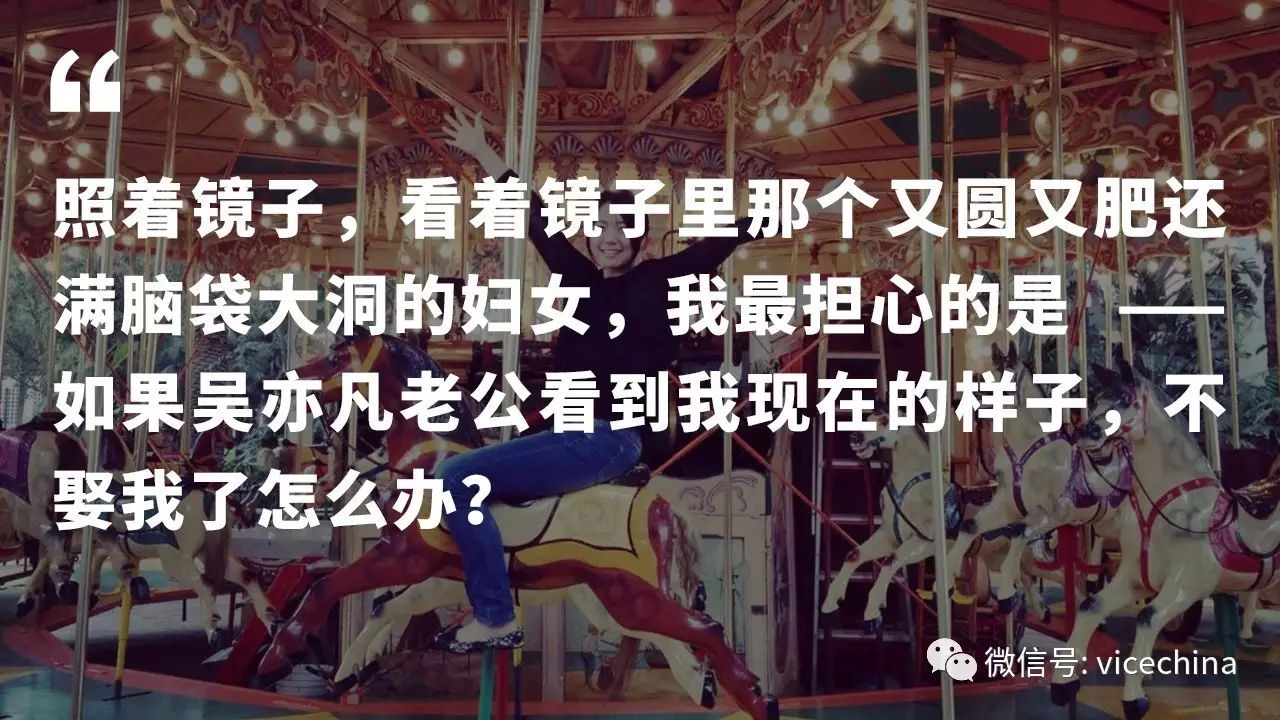

我想呼死那个主任

主任在我光秃秃的脑袋上面画了一个马蹄形的标记,手术时,他会沿着这个标记线像开罐头一样剥掉我的头皮,用头皮夹把我的头皮夹好,然后再用电钻和铣刀切开我的颅骨。很快,我那精密的脑组织就完全暴露出来,医生们就可以操着家伙直捣黄龙,把那枚新鲜的小瘤子采摘出来。
多么完美的切割,多么成功的手术!主任在手术之前也一定是沉浸在自己超屌的技术里无法自拔。他自信满满地对我说,不用担心,也不需要备血,骨头上的手术出血不多,你要相信医院,相信党。然而,在这位行走江湖数十年的主任用咬骨钳咬住我头骨的那一刻,他就后悔了 —— 我的小瘤子真的是血气方刚。你想给它一点颜色看看,它就让你血债血偿。
简而言之就是,还没有等主任直捣黄龙,我在手术台上就大出血了。血出得太猛,把在场的医生都吓尿了。因为手术之前没有备血,他们只好把我才打开的脑袋又给缝上去了。
我就这样被白白开了一次脑壳儿,而那枚血供充足的小瘤子还安然无恙地趴在脑袋里,这意味着我还要再去挨一次刀子。
你们最好不要让我醒过来,我醒了就要去呼死那个主任!
18岁的我就得了癌症,瘤逼吧!

白头发是因为药物作用
18岁,我从本地最好的高中毕业,准备背起行囊闯天下,去澳洲留学。小小年纪的我一直都是遭人恨的类型 :不仅天赋美貌加持,学习好,性格也很好。所以,命运在此处应有破折号 —— 玩死你!
2010年1月的一天,天气晴,原本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天。我的腿上一直有一个大鼓包,因为以前学习太忙,没有在意。妈妈说,就要出国了,还是检查一下好。没有一点点防备,我被拽去了医院。医生在我的腿上掐指一摸,大觉不妙,让我赶快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结果影像资料显示,我的腿上居然有一个大瘤子!以前的我是个牛逼的学霸,现在的我是真 “瘤” 逼了!
很快,我被抬进了手术室,切掉了那枚原发性肿瘤,并接受化疗。

澳洲留学
2月15日,也就是情人节的第二天,我在病床上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我们一家人围着病床唱了生日歌,然后一起许愿。所有人的愿望都只有一个 :希望早日康复,每年都有人给我过生日。
生活又朝着明媚的方向发展了。在一阵阴霾过后,未来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
命运的任意门把我投向南半球,我重新背上行囊,前往悉尼,开始了旁人无异的大学生活。若隐若现的记忆里,悉尼的三年是美好而刺痛的。美好不仅是因为异域刺激,更重要的是我掌控着自己的生活 —— 我搬进了学生公寓,在澳洲有了自己的小窝,结交了一帮好朋友,满悉尼疯跑。不仅如此,我还交了一个不介意我癌症病史的男朋友,他承诺会爱我照顾我一辈子。
我相信一切都好起来了。如果有盗梦的机器,我愿意一直生活在悉尼的梦里,永不醒来。
没有医生敢收我

医生和家长没有告诉我真实的病情,我遇到的是人类斗瘤历史上一个可怕的对手 —— 腺泡状软组织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癌症。
2013年,咳嗽不止的我被发现癌症复发转移到肺。2014年,医生正式宣告癌细胞转移到颅骨。
骨转移意味着我摊上大事了。
2014年夏末,我接受了第一次全麻开颅手术,就是你们在开头看到的那一次。因为主任医师的准备不足,那次手术失败了。
接收我这样的患者,医生都是慎之又慎的。开颅取肿瘤并不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手术,然而这位老资格的主任却做失败了。他失败了不打紧,打紧的是,他失败了就他妈没有医生敢给我做了。一来,医生知道我的病不好对付,做得好我还可以苟活几日,做得不好一命呜呼,他们也会摊上大事;二来,医院内部层级关系复杂,如果其他医生做成了主任都办法做成的手术,主任的老脸往哪儿搁?
只要医生可以继续给我治,我就还有希望。然而,没有医生愿意了。
我和于谦老师的共同点 :喜欢做头

我是吃货行了吧
手术失败后,我做了射波刀放疗。射线可以杀掉我脑袋上的瘤子,但同时也照坏了头皮,伤口不能愈合。加上吃靶向药控制身上其它地方的肿瘤,我的全身皮肤变得溃烂。这一年,我是顶着每天都流着白色脓液、泛着异味的烂脑袋过的,更别说路人的眼神了。
失去尊严和没日没夜的痛苦让我无法忍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常的花季美少女!我要植皮把伤口补上!但是很多医生摆摆手:“你全身这么多转移病灶,再补一块皮也没有意义,不如就让它这样。 ”
在跑了无数家医院被拒之后,我绝望到开始仇视社会想去犯罪了。直到武汉三院给了我新的治疗方案。谢卫国医生 (特别感谢他) 以美观、舒适为前提条件,主刀完成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开颅手术,成功清除了我脑袋里的肿瘤组织,并帮我从大腿上面取下一块皮肤植在头上,把烂掉的伤口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