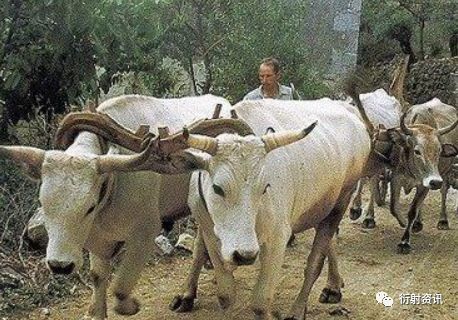两个衍(演)化在中国的古语中都写成衍化,现在衍化的使用不多了,都习惯于演化。古语的衍化特质的是一个过程,带有时间流经意义上的衍化,是随着时间序列结构上改变着的状态。另一种演化强调的是逻辑演化,不见得有时间维度,特别强调逻辑上的承启关系和状态的衔接,强调的是逻辑前提与后承,更多的强调因果性。而衍化更带有时间流经和系统论意义上的衍化,就是一个系统在时间序列中改变的过程。实际上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衍化还没有应用到逻辑因果关系的层面,在当代的理论语境中这样的一种衍化,往往称为唯象性的,这是物理学家经常使用的术语。关于系统的衍化,尤其是近代理论包括哲学理论,都建立在一种数理可构建的一个基础上,对于一个时间意义上的过程系统的衍化,从对他描述的方式来说基本上有它自己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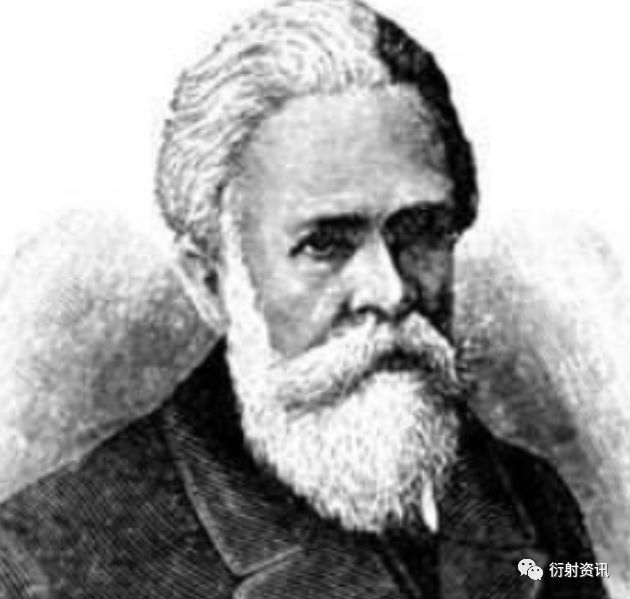
西方人对系统衍化的理论开启,与对牛顿力学的讨论的原始样态相联系,即从流体力学的角度来模拟系统样态的转化。这是物理学系统的一种表述,这当中特别强调的是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一个不连续、不稳定比如湍流的系统,关注自组织理论的同仁都知道,像湍流、自组织现象的发生,这时候形成了临界和相变理论。另一个思路是把这个系统衍化理解为一个概率过程,其实中国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特别的出色,像对马尔科夫的讨论和生灭过程的讨论(如王梓坤和侯振挺),这也属于是衍化过程的讨论。
我们着重强调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冯·诺依曼用概率演化的理论专门写了博弈论,由此开创了博弈的理论体系。不管是从哲学上还是从具体理论上,大体上是从冯诺依曼之后我们建立了博弈的概念。这种博弈往往强调的是零和博弈,就相当于象棋、桥牌这种非胜既负的博弈体系,博弈过程可以用条件概率表现出来,形成了一套瞄向胜利的过程策划的博弈理论。值得强调的是博弈论的新发展,尤其是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出现了之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演化问题,认为社会是在自演化基础上发生着的巨大的系统存态。相应地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趋向,这就是所谓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这样从对弈的博弈到演化的博弈论,虽在数理工具上使用的是同一套概率语言,但形式和使命都发生了比较重要的转变。试图用一种演化博弈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系统当中的一些规律,包括我们的社会如此这般的演化。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这种理论趋向,就是演化博弈论同冯诺依曼建立的对弈的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虽然具有同一性,但是在数学本身的结构和哲学的结构上产生版本上的差异。其哲学意义是想通过这种演化博弈模型的建构让我们能够从一种理想的假设状态、由人们之间自由博弈的逻辑展开,形成一些社会的组织行为和制度行为的理论诠释。实际上哈耶克的理论就是基于这样的东西,因此演化博弈论的逻辑假设,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假设是同一的:即每一个博弈者相当于社会的个体,就是经济人。经济人的个体行为原则都是在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把这个叫做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由于他谋求利益最大化,这就展开了与他周遭的博弈,在这种前提下,演化博弈论被建立起来。

所谓的版本一就是前述的演化博弈论,为大部分经济学家所奉行。国内的经济学家大都把演化博弈论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工具,尤其是受西方经济学影响比较重的所谓高端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奉行这样的研究理路,即通过演化博弈论造模型,通过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进而社会现象。这是我们当下流行的理论版本,它的理论起点是博弈,理论目标是演化。也就是说,这种理论的哲学要点是:它似乎是在理论解剖博弈的浪花,但最终将这些浪花归寂于衍化的海洋。
但这种演化博弈的理论假设有一个致命的理论前提的缺憾:大家可以设想一个赌场,散户当然是博弈者,散户和散户之间的点对点博弈关系是演化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所准确揭示的关系,但如果你要把此点对点的博奕关系的性质置放在庄家和散户之间的点对集的博弈关系上来理解的话,你就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因为我们会发现:庄家的盈利是对整个赌局(集)的盘剥,它是和散户之间(点对点)博弈关系无关的另一个确定的逻辑过程,不管赌徒怎么玩,庄家攒钱是肯定的,就是说庄家盈利的逻辑是被设计出来的:你(点)进了我的赌场(集),我便已然是博弈的天然赢家。
你博弈的对象是点,而我收获的是集。你把庄家与散户赌徒当成地位均等的博弈者——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秘密,演化博弈论通过概念偷换,堂而皇之地隐藏了作为全球经济邪恶控制者的资本集团作为博弈庄家的本质,而在庄家与散户之间大玩起了博弈前提的平等。这才是在平等的逻辑前提下大玩博弈演绎的理论精髓。
我和禹老师一直在做一种理论上的努力,想把类似演化博弈论等西方现代经济社会分析的基本假设中极力隐藏着的理论视域(脉络)还原回来。显然,基本的路途是从正面修正这些理论,即从演化中寻找庄家生成的逻辑路途;我们也曾正面分析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哈肯的协同学及其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期翼寻找到从微观出发达之于宏观的演化论的逻辑路径。但这不仅是在哲学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其实哥德尔逻辑定理的最哲学的本质就在这里。试想,你在散户博弈的理论前提下能推导出庄家的存在样态吗?你从羊群的逐草而徙的基本逻辑起点能推出牧羊者或猎羊者的存在样态吗?一般地,就是微观层面的演化分析获得不了宏观层面的规律结构。其哲学意义就是:一行逻辑无法演绎扩张成两行逻辑。
这就是两行逻辑论提出的现实背景。如果不首先确立两行论(像中国哲学的逻辑前提所指示的那样)的逻辑前提,一个衍化系统的宏微观两个层面之间,是无法用一行论的逻辑演绎相互取代的。

这就是我们在两行逻辑论中指出微观规律之上必有一个与之逻辑独立的宏观逻辑结构(虽然宏微观之间是高度逻辑关联的)的根本原因。表现在几百年来的当今国际经济结构分析时,就是必有一个独立的宏观规律结构,其逻辑的衍化独立于微观演化博弈所能达到的最大分析域之外。具体地,就是说演化博弈论仅只给出了经济系统衍化的一个逻辑版本,即下行的一行逻辑版本;而宏观上,必有一个另一种规则独立发挥作用的逻辑结构,即上行的逻辑结构。我们称之为版本二。这两个版本是华尔街手中阴阳两套不同的版本,其作为培养全球经济学家基本教程的是版本一,目的当然是消灭任何形式的规模经济体或命运共同体,旨在说明任何与自然人“不对等”的博弈者都应该被讨伐出局,唯独隐藏了一个邪恶而巨大的资本庄家;另一个作为狩狝全球经济成果的“庄家通吃全世界”的秘密工作手册则作为版本二,这是绝对秘不示人的。
然而,几百年的“狩狝全球”的具体实践,已经揭示了版本二的逻辑流程和操作细则。这个秘不示人的版本是资本无所不用其极地通过各种资源调配,凌驾于人类共同体之上控制和“规范”全球社会经济行为的逻辑过程。其实这是另一种演化过程,这样的过程从马克思到列宁都不同形式地揭示过,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和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真实地体验过,目前我们讨论的时局,被东方一个逻辑步骤一个逻辑步骤所指出来的,更是这个狩狝全球的逻辑流程。客观上两行逻辑地看,除了中国在成功地同这一逻辑流程在本质上过招之外,几乎整个世界都被这个指挥棒所调动。在这种宏观严密的全球控制体系之下,你会发现微观的经济体间的简单博弈行为微不足道,不对宏观局势产生实质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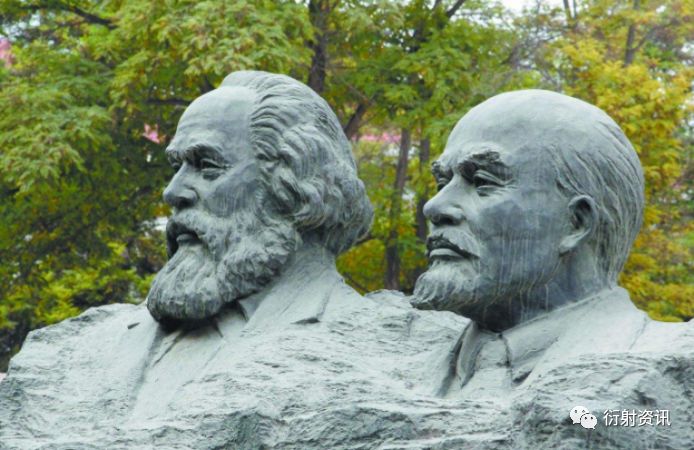
全球的衍化过程被刻意隐藏这个逻辑主线,东方给出了几年的提前量就把逻辑过程指示出来,然后用时间来证明历史的衍化就是如此,这说明其实东方所揭示的背后的理论衍化图景,并不是社会自组织的演化图景,是由所谓顶层设计的、把全球当做控制对象的一套控制程序的自我展开。这个版本除了东方在很本质地把这个过程展示出来之外,我们没有看到理论研究的团体或者学者,按照此方式处理衍化问题。这也客观上揭示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方法,真的被主流的学术界所抛弃了。
那么这两个版本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前面说过,如果你要是以版本1的逻辑视角进行推演,大家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我们把一位或者几位顶尖的演化博弈论高手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进行理论推断,不管他们都多高的想象能力都没有办法推演出来第二个版本的逻辑轨迹。换句话说演化博弈论是一个低层级的博弈论,它是有理论盲区的。它关注于微观,通过微观的演绎,要寻求获得宏观的结论,不管微观的逻辑推论多么的精致、本质,都没有办法透视到宏观的、演化格局背后的那个逻辑。
前面所述的博弈或衍化理论版本间的背离,既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层面现在的原因,又有理论的逻辑结构分割破碎的内在原因。换言之,在目前西方的理论体系下,博弈与演化,乃至于地缘政治与军事理论,这些虽然都应该在同一个理论视域下统筹研究,但其方法的各自逻辑源头的异质性决定了各学科在理论壁垒的制约下各自为战,甚至此理论领域的专家不但是彼领域的外行,更可能是一语难解的彻底科盲。这一点,在学科大爆炸的背景下,更多地表现为专家与专家之间、专家与哲学家之间互设了理论篱藩,均趋于碎片化的专门家。我们说将华尔街版本一稔熟于胸的经济专家甚至感受不到版本二的存在,并多以阴谋论拒斥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研究,也与自身已然被学科藩篱所理论碎片化有关。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以做到如此地“接地气”,对于理论通达之人,何以能做到“不做良相,则当良医”。下面我们以营卫论为例,指出其对衍化与博弈的可理论转化与逻辑会通性。

营卫论的逻辑基础是两行论。两行就是指命运体所在的微观世界与共命运体所示的宏观世界这两行。你不能谋求从微观世界出发逻辑推导出宏观世界;也不能谋求从宏观世界出发彻底逻辑决定微观世界。两行关系是宏微观逻辑共轭的,两行论的自身哲学问题恰恰是两行共轭何以可能实现,怎么实现。营卫论就是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理论回答。
1.一般逻辑表达(两行论)
命运体在自身逻辑展开域内展开自身,所接于对待的一切对象性因素均来自于包含命运体于其中的共命运体。逻辑展开的运行可逻辑描述为命运体与共命运体两行之间的“对进”的“际遇”与“跨际”。这里的“际”是在逻辑展开域中对进点达成处虚拟的两行界面。“跨际”的逻辑实现意味着命运的存续,否则意味着死亡。对命运体和共命运体来说都是如此。
2.逻辑过程实现(性命论)
对于两行对进的任意一方而言,在“际遇”处,对方是以符合自身所赋予的逻辑格式的方式,以“意义流”的形式被自方所对待,“跨际”过程实现时对方“意义流”的注入及其被解读(及利用),构成自身命运存续的前提。命运体在共命运体中的展开,莫不是以此方式。在宋儒太和论的语境下,这是一个“性”达之于“命”的过程。“性”对于“所与”结构的逻辑格式选择性,决定着此命运之“性命”非彼命运之“性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逻辑基础在于此。(这里的格式选择性的凸显,是对宋儒太极论的重要修正)
3.两行共轭的逻辑达成(营卫论)
在一般精致和谐的“命运体-共命运体”共轭结构当中,典型的代表是医家眼中的人体生命体,脏器百骸作为命运体,其与“心”代表的人体共命运体之间,之所以互为依托地各自存续生命,是因为有一个决定性的逻辑环节:对进的两行均以“营”“卫”为对待和指读对方的基本逻辑格式。特别地,如果将“营卫气血”的系统意义进一步哲学化,那么“营”就是标示命运体存续之(获得)资源的测度;“卫”就是标示命运体抵御病害从而免遭夭亡的测度。对于一般“命运体-共命运体”系统来说,“营”是发展的维度;“卫”是安全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