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自公号:KnowYourself,帮每个人学会幸福生活
KY作者 / 预言
编辑 / KY主创们
做大学的选题,起源于一组数据,根据澎湃新闻报道,2018年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再次刷新纪录,
多达800万余人
。而高校应届生本科平均起薪为4500元人民币,硕士研究生平均起薪6100人民币,且有逾5成应届生表示自己就业岗位与此前专业毫无关系。
近些年,和“大学生”这三个字联系最紧密的词,好像变成了“毕业起薪”。“大学生”三个字似乎越来越贬值。
这样的现状,意味着现在的学生,可能已经很难体会到大学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殿堂。
“大学生”在过去几十年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种变化。本次访谈的过程中,我从1977年入学的第一代大学生开始交流,通过他们来思考当下的大学教育和个人成长,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变的议题?又有哪些新的变化?
从几代人的访谈中,我看到,无论年代的变迁,人在大学这个阶段,都有一些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实现的成长,这些成长影响了我们后面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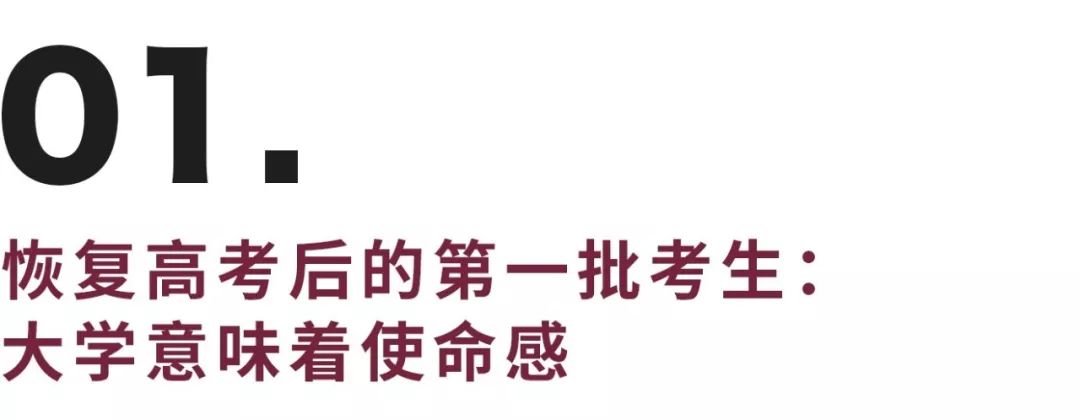
关键词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977年12月10日,那一天是国家首次恢复高考的日子。当天有570万人走进了考场,最终只录取了27.3万人,
录取比率低于5%
(2017年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当年我国高考录取率已经高达75%)
。
第一位访谈对象,张爷爷就是这5%的大学生,时代赋予了这一代人身上特殊的“家国情怀”。
下面是张爷爷的口述:
“对我们那代人来说,大学提供了一个改变人生的起点。没有起点就没有后面的这一切”。
“1977年,我25岁,在家乡的一个小学担任老师。后来我是看报纸才知道国家恢复了高考,当时心里非常激动和高兴,因为那个时候,当老师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但还可以参加高考,就意味着我还有一次机会读大学,今后的路跟当时在家乡的我将会完全不一样。
当年很多人都是临时抱佛脚地开始复习。没有家庭背景的人一边种地一边看书,挣工分。有时候为了逃避家里的活,故意说自己手受伤了、脚受伤了然后回家看书。
我托我母亲想办法搞来一套复习资料,其实很多复习资料的内容我是看不懂的,数理化基本看不懂,我有时间就看看历史地理和语文相关的知识。
我文科分特别高,还是侥幸考入了大学,同学中年龄小的有17、18岁,大的有34、35岁,大家都非常自觉,觉得有书读实在是很幸福。
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交代我们要买书,新华书店第二天才开门,很多同学和我一起,晚上就去了北京市新华书店门口排队——就是因为很兴奋、想要尽快拿到书开始学习。
因为我不懂数理化,进了大学很多都跟不上,学起来很吃力。自己觉得很丢脸。班上有一些取消高考前考过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平均程度比我好一些。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赶上。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不会去想成绩好了能得到什么,只是一种自我要求。
我们学生其实在大学都非常苦。食堂里的饭实在没油水,每天都是大白菜就馒头。但那时的快乐很简单,比如偶尔老师请学生到餐厅好好吃顿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真是美味。还有,因为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我们经常骑着单车去城门儿边玩,就觉得特别快乐。
我毕业后在国家分配的单位里工作,是在一家上海的小学,虽然之前也是做老师,但在大城市落了脚,待遇也截然不同,我在静安区的房也是单位给分的。那个时候,单位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身为第一届大学生当然更加自豪。当然我们进去工作了,也比普通工人更加努力。
那时候大学生不但意味着更好的生存条件,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荣誉。而且我孩子有时跟我说工作无聊、人生没意思,我们那代大学生不会——我们觉得自己对国家有责任,充满使命感。
虽然后来发现,这有时候限制了自己个人的发展,但好处是意义感很强,很容易觉得幸福。
大学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开始,它提供的是改变人生的起点,对我来说,没有这个起点就没有后面的一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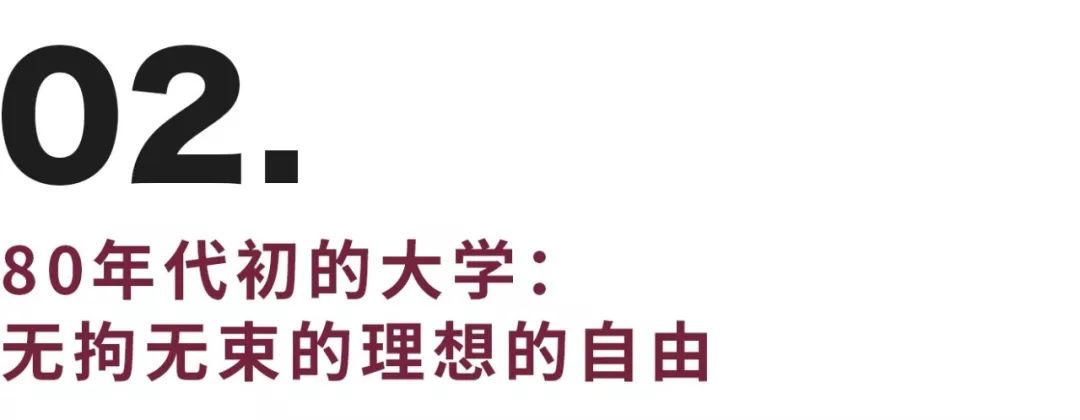
关键词 :在梧桐树下趴着聊天、唱歌
恢复高考几年后,学生们入学的年龄就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尤其是80年代的上海,时代洋溢着向外开放的气息。我们访谈了80年代初在上海读书的,第一批真正意义的大学生们的生活。
以下是张老师的口述:
“在大学四年的集体中,我们寄托了一生中最无拘无束的理想和自由。”
“当时新闻系算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我们周边有很多文笔很好、思想活跃的同学开始自发办校园杂志。
那个年代,老师一直教育我们一个人、一个记者要如何避免世故和势利。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学生身份,但在采访一个董事长、总裁之类的人物,老师总告诉我们不要怯场。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浪漫的理想主义,整个大学夏天的夜晚,在校园的梧桐树下,学生就趴在草坪上聊天、唱歌。我们当时的爱好也比较小资,班上有同学很爱写诗,跳交谊舞、练书法,真是把文人该做的一切都尝试了一遍。
现在想起来真是最美好的回忆。
现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我每次到了开学季,都会试探性的问一问刚进校的同学:‘你们今后谁想做记者?’没有多少学生会举手。你也不能责怪他们,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大学已经不是一个乌托邦。
现在的孩子也挺难的,毕竟曾经的我们还有大学这段可以做梦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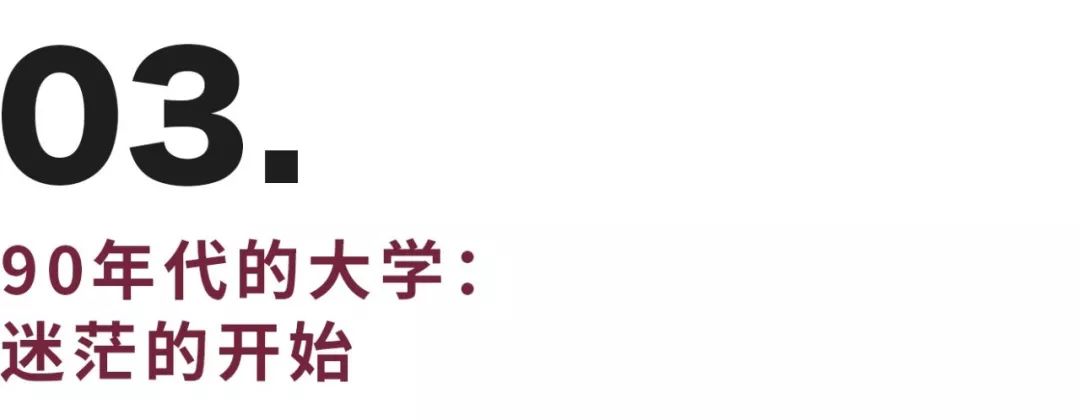
关键词:国家政策的改变
1995年,大学开始施行双向就业政策,96年,大学分配政策正式取消,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第一次进行扩招。整个90年代,“大学”充满了变化。在扩招前,大学教育实行的是精英教育,扩招之后,精英教育开始面向大众教育。
下面是90年代中期读大学的雨林姐的口述:
“我大学的几年中,关于毕业还分不分配,之后很可能会扩招这些信息不断在变动。所以我们的整个大学时期就特别迷茫,也很容易就焦虑。因为本来上大学的目的就是毕业国家会分配,突然有消息说会双向选择就业去向,我们最初上大学的目的就失去了。
现在想想,一方面是害怕被用人单位挑选,
更恐惧的其实是我并没有想过自己想做什么。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生道路就应该是被安排好的,现在忽然说我有了选择,这其实比没有选择更恐惧。
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不知道该怎么做?哪个课程我应该学?为什么有些课很无聊,我也要学?那我真正想做的、想学的又是什么。
后来我因为各种机缘做了一名中学老师。
现在我的女儿也读大一了,我就建议她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不过我发现,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大学、以及未来的人生要怎么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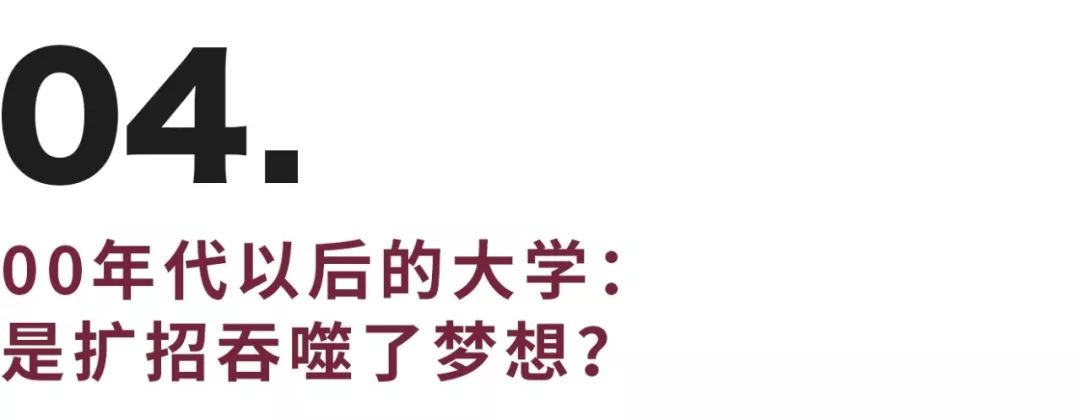
关键词:我为什么要上大学?
扩招以前,我国高考平均录取率是24.13% , 99年扩招后录取率一路上升,始终维持在56%以上,2017年达到了75%
。
大学变得越来越容易上了——这也就意味着,大学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含金量不断降低。
以下是08年入学的李同学的口述:
“不明白为什么上大学,但也不能不上大学。”
“我高考成绩并不是很好,为了去尽可能好的学校,我只能选择不喜欢的专业。可实际上毕业后,我的大学名字也没有给我找工作带来什么便利。
我觉得我们这代大学生的生活很
浪费,虚度人生
。——也许那些北大清华名校里的学生会不一样吧。我们这种二三流的大学,同学们基本不上课,老师们也不知道在上些什么课。反正就是打游戏、出去玩,考试混一混,挂科还可以补考,学校很少真的会让同学不毕业。
理想什么的,不存在的——不过也玩得很开心,起码过了几年开心的日子吧。毕竟从毕业以后开始可能就完全没有这样轻松愉快的日子了。
工作以后其实压力很大,很后悔没有在大学的四年里多学点实实在在的技能,多做点实习。以至于毕业后什么竞争力都没有,很多东西都是现学。
现在变得努力了很多吧,还是会很焦虑——过好日子没这么容易。但这几年收入变高了,发现自己依然不开心,吃吃吃买买买,还是会空虚。很多时候都希望大学能重来一次,好好利用那时的时光,再找个好对象好好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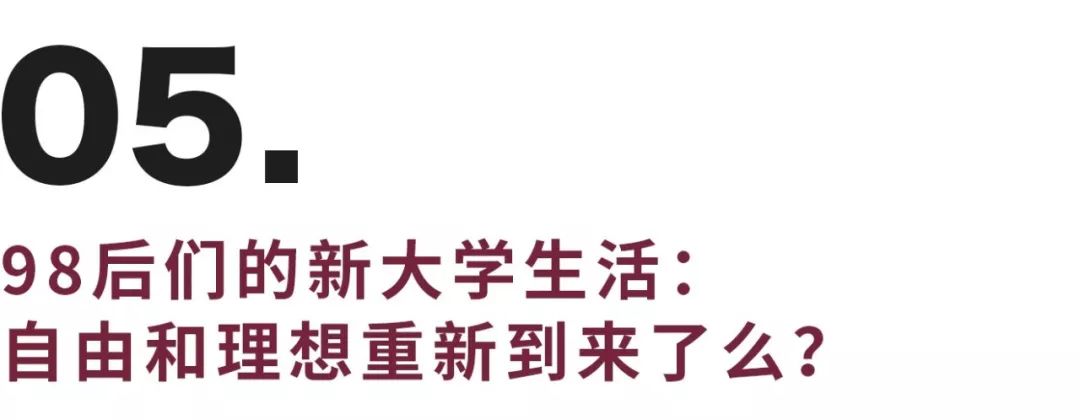
关键词:争取我想要的
最后,我们访谈了一位2017年入学的同学,她是99年出生的,今年19岁。以下是她的口述:
“我是刚刚那位受访者‘雨林姐’的女儿。因为我妈妈当初在大学遇到的问题,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她果断把我送往美国读书。
我们学校在美国是一所著名的女校,非常注重培养女性领导力量。在我们学校,有一类女孩被称为‘Wendy
girl’,她们学习很用功,聪明、努力,并且很有野心,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每门课的学分中,Wendy
girl都会力争做到最好。她们都选择了商科、经管类的专业学习,因为她们认为这类专业,就是标准意义上的‘成功’。
我不属于这类女孩,我喜欢社会学,喜欢用理论去分析当下的社会现象。比如有一次社会学作业,我就分析了我爸妈那一代人,为什么相比其他的兄弟姐妹,为什么是他们最终走入了大学。
分析过后,你会发现,其实最终去读大学的都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在里面,其实我也是,如果不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有大学背景,他们也不会有经济实力把我往美国送。
我们学校学习要求很严格,经常需要在图书馆自习、通宵写论文也是常态。
以前还以为国外的大学就是party很多,大家打扮的美美的逛街,但现实生活是很辛苦的,
就算party也是放弃睡眠时间而不是学习的时间。
现在是大一暑期,我身边的同学都早开始准备申请暑期实习了。因为出身都在环境不错的家庭,所以对于“成功”就更加向往。他们去的地方都是投行、四大、比较能赚钱的地方。
我们这代孩子,无论是从申请学校还是开始申请实习,大家都特别积极,特别早。
现在,我也开始打算校外实习、培养自己的爱好。比如我很喜欢权志龙,追星当然也是爱好的一种啊。追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其实到了国外念大学,你还会发现追星是不分国别的,到哪里去都会有人也喜欢着我的爱豆。我在大学里面学韩语,也是因为我的偶像。”

看完这几个故事,我在思考的问题却比较沉重,是关于特权和精英主义的问题。
第一届恢复高考的访谈者可能是例外。他们那一代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家国深深绑定,这一方面让这代人,没有足够意识到“每个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他们的孩子有一部分受到了这一点的伤害,但其实想跟这些孩子说,的确两代人的生命历史不同,他们试图安排孩子的人生的确是一种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