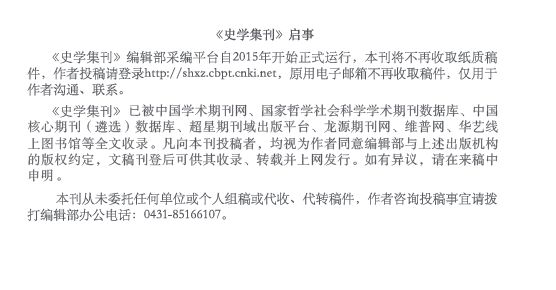原载《史学集刊》2021年第3期。
摘 要:浪漫主义运动发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是一场构建民族精神特质的思想塑造运动。柏林的宗教氛围、普鲁士君主制传统,特别是作为其“血脉”的等级制度在法国革命冲击后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使浪漫主义者得以将普鲁士作为政治实验场开展活动。亚当·米勒和斯泰因是两位改革时期的浪漫派代表,一个从观念出发,将君主制、等级制“浪漫化”,用于指导改革;而另一个则从历史经验出发,在实践中尝试将君主制和等级制做出顺应时代的改变。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普鲁士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普鲁士改革;浪漫主义;亚当·米勒;斯泰因
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并活跃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作为文学概念,它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其与政治的关系,也因为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浪漫派政治立场的关注,而成为一种政治哲学。至于浪漫主义与历史,人们大多关注它对后来历史主义史学产生的影响,作为历史经验的浪漫主义则研究甚少,因为普遍认为“浪漫”是个超历史的概念。[1]但实际上,浪漫主义深深嵌入了德国的历史进程,或者说它的思想和行动构成了德国历史本身。[2]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浪漫主义与发生在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相结合,通过描述两位与改革相关的政治人物——亚当·米勒(Adam Mueller,1779—1829)和斯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的思想和主张,分析他们的“浪漫”思想和活动轨迹,展现这一时期德意志历史的丰富性。在《政治的浪漫派》再版前言中,施米特承认,“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把浪漫派与上个世纪宏大的历史结构联系在一起,批判才能达到更有意义的深度”。[3]
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浪漫主义运动后期[4]醉心于国家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政治浪漫主义者与普鲁士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诺瓦利斯(Novalis,原名Georg Philipp Friedrich Freiherr von Hardenberg)、施莱格尔(Friedrich August Schlegel)、米勒,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或思考的对象正是普鲁士。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施莱埃尔马赫尔(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虽不属于前者那个小圈子,但与浪漫主义人士也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同样主要活跃在普鲁士。
柏林的宗教氛围是浪漫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历史学家比洛(Georg von Below)说,“浪漫派虽然不是新教精神的产物,但确实是新教土壤及其国家即普鲁士的产物”。[5]普鲁士是新教国家,但崇尚宗教宽容。早在勃兰登堡马克时期,选侯约阿希姆二世(Joachim Ⅱ,1535—1571年在位)改宗新教,于1540年颁布《教会法规》,确立了路德教的领导地位。约翰·西吉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 1608—1819年在位)则改宗加尔文教。不过,勃兰登堡—普鲁士一直保留着宗教宽容的传统,一般而言,各教派可以保留自己的信仰,邦君也避免使用“强迫信仰”的特权,以防止教派争端和政治分裂。这个传统在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1740—1786年在位)时期发挥到了极致。在《论政府形式和君主责任》中,国王坦言,“统治者没有权力指导臣民信仰什么。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人们平静安康,而有宗教迫害的地方,则会引发血腥的、长久的、毁灭性的内战”。[6]因此在普鲁士,官方宗教总是充满各种思想和情感,激进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兼具神秘色彩的虔信主义,如“摩拉维亚兄弟会”等,在这里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
一个事实是,浪漫派文学的重要代表都出自新教家庭,他们使用的德语在宗教改革后才发展起来并进入文学殿堂。普鲁士是新教的大本营,而新教天生具有革命性。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将天主教世界捅出了一个大窟窿,引发了普遍而持续的反叛精神。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一开始就吸引了一批具有革命情怀的浪漫主义者,他们是革命精神的拥趸,对雅各宾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强烈诉求,对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充满期望,虽然他们所追随的可能只是革命的话语和形式。革命赋予了浪漫主义者另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念。
不能否认,浪漫主义运动是从新教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也在信奉宗教宽容的普鲁士大放光彩。改革时期,两个与宗教有关联的俱乐部即“基督教德国圣餐会”(Christlich deutschen Tischgesellschaft)和“麦凯弗雷”[7]为政治浪漫派提供了活动场所。在一段时期内,它们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当然,在普鲁士,宗教行为必须从属于国家利益,它只能作为信仰和文化,而不能成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因此,当浪漫主义诗人、作家以各种手段和形式表达不安分的反叛精神,提出治国理政的思想观念时,他们是被允许的,但当他们皈依天主教,并以此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时,作为浪漫主义的政治运动也就宣告终结。[8]
对于政治浪漫主义者而言,普鲁士真正吸引他们的还是政治。普鲁士国家在两个层面上为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石:它是开明的军事—官僚—王权绝对主义国家,同时强烈关注个人权利和全民福祉。弗里德利希二世的普鲁士是欧洲“开明专制”的典范,国王本人也是“开明君主”的楷模,他接受了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君王指南”,后者那本《关于人的社会学的理性思考》(Rational Thoughts o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Human Being,and in Particular on the Commenwealth)的意图便是指导普鲁士君主建立一个完全的福利国家。弗里德利希二世于1784年着手修订《普鲁士国家通法》(1794年生效),对这部法典,托克维尔的评价是:“它模仿了法国1791年宪法中的《人权宣言》,但本质上又完好保存了传统社会的等级特权。”[9]该法典为解释普鲁士体制提供了完美注脚,它有理由使那些对政治具有强烈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以为,普鲁士不仅是德国传统邦国中最有潜力的国家,也是最有可能通过改造现存权力结构,发展出新型政治形态的国家。浪漫主义者围绕普鲁士所展开的斗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时代的基本目标,他们渴望普鲁士成为他们理想中的浪漫国家。
1797年,普鲁士王位再度更迭,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Ⅱ,1786—1797年在位)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97—1840年在位)登基,政治浪漫主义者萌生了在普鲁士进行内部变革的强烈愿望。1798年,诺瓦利斯在《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uecher)上发表了格言式篇章《信仰和爱》(Glaube und Liebe),赞美路易斯王后,推崇模范家庭,塑造道德楷模,以普鲁士王室为榜样畅想理想的君主制国家的本质——爱和忠诚。在次年发表的《基督世界或欧洲》(Christendom or Europe)中,他更是从普鲁士出发,提出了规划欧洲秩序的新蓝图。具有诗人气质的诺瓦利斯想以普鲁士为舞台,描绘其生命、诗歌与思想的浪漫图景,但不幸早殇。他的离世虽然使之免受因对普鲁士“浪漫化”期望的落空而招致的痛苦,但并未阻止他的战友们之后继续活跃于普鲁士,以普鲁士为“试验田”。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兵败耶拿,王室逃亡到梅梅尔河畔。祖国山河破碎,却在客观上为浪漫主义者施展抱负创造了条件。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改革,随处可见浪漫主义者活动的身影,浪漫的政治思想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在普鲁士历史的危急时刻,带有浪漫色彩的政治人物投身到了复兴普鲁士的运动之中。然而,像革命者和诗人、文学家、出版人这样的早期浪漫主义者对普鲁士注定是要失望的。当一切都要赋之以信仰和爱,哲学、诗歌、科学和艺术,甚至国家理论和政策实践都要被赋予浪漫色彩时,一定会遭到冷遇和误解,浪漫主义者是带着怨恨离开普鲁士。对于他们的离去,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说,本来就“没人拿他们当真”。[10]
但是,还是有一类浪漫主义者在普鲁士获得了成功,至少有可能按照他们的理想推动普鲁士走上浪漫主义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从梦幻转向了真实世界,不是简单的想象过去,记忆历史,以过去否定现在,而是从普鲁士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发现可以推动改造的元素,形成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而能够将他们与真实世界紧紧勾连在一起的,则是梅尼克所说的具有“确定社会特征的氛围”,即作为普鲁士血脉之一的传统的贵族等级制度。
普鲁士的等级制度并非特例,它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一种经济—社会—政治模式。进入17世纪、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时代,贵族等级虽然受到抑制,但君主与贵族等级的“二元社会和权力结构”并没有被破坏,反而以新的形式巩固下来,形成“等级导向的君主制”。[11]按照常规,新君继位后都要召集地方等级的“效忠会议”,重新明确君主与地方的关系。在易北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勃兰登堡马克、波莫瑞、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在内,等级制度构成了普鲁士君主制度牢固的政权基础。
代表地方权力的等级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土地贵族、市民和自由农民,农奴并无等级权力,其意见由“主人”——地主来代表。市民阶层和有地的自由农民虽然勉强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但并不强大。真正掌握等级权力、控制等级政治的是土地贵族。因此,地方等级机构本质上是封建贵族利益的重要代表,它与中央政权间形成平衡关系,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不过,普鲁士的等级制度并不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在革命到来之前它已经开始了缓慢变革。开明的君主以及地方贵族意识到人身自由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在领地农庄中,赋予部分农奴以一定的身份自由。同时,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在扩大,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将易北河以东的土地贵族与城市、农民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日趋紧密的、新型的“利益共同体”。
法国革命是由第三等级领导的,对第一和第二等级形成巨大冲击,它不仅剥夺了贵族等级的财产,也废除了他们包括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在内的一切特权。公民权的确立破除了社会中所有传统等级的壁垒,让人人在法律面前实现了身份平等。
但是在普鲁士,法国革命的剧目没有上演。与法国革命爆发之前的社会不同,在普鲁士发生的改革并非源于等级制度的落后和腐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拿破仑战争中也没有受到冲击。耶拿溃败、宫廷东逃以及1807年6月14日《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虽然使普鲁士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所有土地,但东部四个省份——勃兰登堡、波莫瑞、西里西亚和普鲁士却安然无恙。不仅如此,国家的溃败、中央政府的瘫痪还进一步激励了由贵族所把持的地方等级政治,无论是支付法国的战争赔偿还是复兴战后地方经济,等级团体发挥作用的空间迅速扩大,这也为贵族抵制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制度基础。
偏安东隅使国家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机会,社会各方得以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压力之下国家可能的未来。普鲁士改革汇聚了一批时代精英,他们来自不同邦国,其中也包括一些浪漫主义者。这些人集中在战败的普鲁士,思考如何避免类似法国的革命在德国发生,改革的方向是否应该与法国革命的原则一致,未来的普鲁士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上应是怎样一种形态,普鲁士的历史和传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经验和要素。借助等级制的历史和现状,浪漫主义者在普鲁士似乎大有可为。
作为运动的浪漫主义就这样嵌入了特殊时代的普鲁士历史。亚当·米勒和斯泰因,一个是浪漫派政治思想的设计者,一个是普鲁士改革的领导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改革增添了“浪漫”色彩,在普鲁士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亚当·米勒出身新教家庭,是柏林财政部一名小官僚之子。1798—1801年,米勒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和历史,受到了法学家雨果(Gustav Hugo)和历史学家施洛策尔(August Ludwig von Schloezer)及黑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的影响。此后,他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马克委员会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候补法官,又到波森受聘为哈扎(HazaRadlitz)家的家庭教师,并在此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哲学著作《对立学说》(或称《矛盾学说》,DieLehre vom Gegensatz)。随后,他游历了丹麦和瑞典。1805年,他跟随精神导师根茨(Friedrich Gentz)去维也纳,于4月30日秘密改宗天主教。
1805—1809年,米勒住在德累斯顿期间,做了关于诗歌、艺术的讲座,影响不大。但1808—1809年冬季他开始讲授国家学理论,最后以《论国家艺术的要素》(另译《治国术》,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为题,于1811年集结出版。这些活动为他聚拢了人气,赚得了名声,吸引了不少政治家的关注。1809年,在法国人开进德累斯顿前,他回到普鲁士,并思考如何活跃柏林“真正而又严肃的”公共舆论。8月29日,他向当时普鲁士财政参事斯泰格曼(Christian Friedrich August Staegmann)递交了一份《关于在普鲁士出版官方报纸的备忘录》(Denkschrift ueber Anteil der Nation am Nationalen und Oeffentlichendurch Pressfreiheit und oeffentliche Meinung)。1811年,他与克莱斯特创办《柏林晚报》(Abendblaetter),后又经营《德意志国家通讯》(Deutsche Staatsanzeige)。1809—1811年,米勒在柏林做了一系列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个性和普鲁士君主制的演讲,后编辑成册,以《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普鲁士君主制的特点》(Ueber Koenig Ⅱ und die Natur,Wuerde und Bestimmung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为题,成为颇有影响的政治读本。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开始时,米勒离开普鲁士去往奥地利,并于1829年逝于维也纳。虽然米勒未曾在普鲁士担任过一官半职,报刊主编的正式职位也与他失之交臂,这多少令他失望。但在维也纳,他被任命为帝国参事,直接为首相梅特涅服务,并受封骑士称号。
米勒是以浪漫的造反派起家的,他曾自嘲其青年时代是“病态的,吹毛求疵的”。但不同于其他浪漫派人士,米勒不仅没有受到“1789年思想”的影响,而且表现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他最初接触的是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思想。在这方面,他受到了“哥廷根学派”的影响,这些学者们始终与法国革命的热情保持距离,对当时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采取审慎的批判态度。米勒的思想渊源非常复杂,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与根茨、柏克、克莱斯特,甚至费希特的密切关系,在思想上他们彼此影响。从根茨那里,米勒了解了现实的物质世界,理解了国际贸易和国家的意义;从柏克那里,则懂得了传统、风俗、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对于有生命的国家的价值。在米勒眼里,柏克立足当下,尊重过去,放眼未来,其精神已烙入他的灵魂,但却无法简单模仿。[12]
米勒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对立学说》一书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这本书的出版受到根茨、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和费希特等人的鼓励。后人称之为“浪漫主义世界观的纲领性论著”,但施米特却认为,《对立学说》是部万花筒,国民经济学、自然哲学、医学、文学和占星术都碰一碰,却不得要领。[13]米勒提出该学说的宗旨是要在大革命后,向启蒙思想所编织的机械藩篱发起冲击,把思想的玄思植入现实的土壤。
米勒竭力反对启蒙理性主义的“线性演绎”,正是为了克服它可能带来的僵死性,米勒特别引入了“对立”理论。他指出:一切生活都建立在自然和精神、社会和政治的彼此矛盾和紧张之上,比如爱与恨、战争与和平等。不过,为了避免对立思想也出现“僵死”,米勒又进一步提出了“动态”概念,即把思考的对象置于运动和变化之中,强调过程而非静止的概念本身。当然,“动态”的概念也是理性的,它不像人们通常批评浪漫主义思想那样,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动态”的优点在于突破了启蒙思想的局限性。浪漫的理性和启蒙的理性,“一个是无边际的思想图景,另一个是僵化而封闭的现实;一个坚决厌恶所有限制,另一个坚决反感所有自由”。[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曼海姆认为,米勒的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完成了启蒙主义凭借自己永远可能完不成的任务。[15]
通过“动态”概念,对立的事物“交互生存”,或竞争或冲突,并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一个整体。因此,事物的当前状态往往是变化中的当前共存因素的综合,但不会就此停止,它还会在不断的运动中,形成下一个更高级的综合体。这样一来,固定的社会契约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形成。米勒相信的是“观念”而不是“概念”,他由此否定了机械的“社会契约论”。
米勒强调“整体性”(Totalitaet),这是他从诺瓦利斯那里挪用的浪漫主义术语,以“整体性”来包容和超越所有的矛盾和冲突,因为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比二元更复杂。德国宪政史家胡伯(Ernst Huber)就认为,米勒对立思想的核心是“寓于多样性中的整体性”(Einheit in der Vielheit),整体性体现为多样性,而多样性也是整体性的表达。[16]这就是米勒的“生命哲学”。
《对立学说》为米勒最为关切的国家理论奠定了哲学基调,而《治国术》正是他思考政治学的杰作,也是政治浪漫派的经典。在米勒看来,根据对立学说,国家形态不能只是形式和秩序,这是“僵死性”国家的表现,而应该是动态、鲜活、流动的,像生活本身一样变动不居:
国家以及一切伟大的人类事务都具有这一特性,即它们的本质绝对不会被包裹在或被压缩进词语或定义之中。我们把僵硬的、一成不变的那类形式——如有关国家、生命、人类等的一般科学——称为概念。我们的先辈认为国家是一种强制机构,但是,在新的时代,最好、最重要的国家形式不再是强制的,我们构建出了其他概念,但尚不能立足,因为这种概念不是动态的,而国家,就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却是持续运动的。[17]
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个个机械存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机构。对国家的认识也不只是简单地了解其资源、物产、土地、人口、财富以及流通、法律和慈善状况。如果仅限于此,米勒用浪漫派惯有的生动语言表述道,就如同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客厅里号脉、称量食物那样,得到的是少得可怜的知识”。[18]至于政治家,他们的工作当然也不是像清理衣橱那么简单,把穿旧的衣服换下即可;或像高级裁缝那样,为国家宪法和法律事务剪裁出合身的衣服;或像医生那样,为生病的国家开出单一的、精心配置的药方,似乎药到即能病除。米勒主张,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必须理解国家的本质,“要到国家的核心,也即其运动的中心去”。[19]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运动的中心呢?米勒以为要经历险境,“海上的风浪越大,舵手的冷静就越值得称赞”。“政治家不能将战争状态排除在其国家理论之外,视其为不相容和非自然之事,而应使战争思想渗透和启发其整个理论。他所阐述的理论中不能只有和平没有战争,不能只有静态没有运动。只有这样,政治家的素质才能充分展现”。[20]
当然,并不是说米勒崇尚对立最极端的结果——战争,他崇尚的是无所不在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冲突的种子只有在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中才能发现并存活。米勒强调政治实践而不是政治理论。掌握治国艺术的政治家不应该固守理论,而应该投身实践:
与理论家相比,实践者们总是更注重情感,他们的学问也更加鲜活,因此我们能够从实践者身上学到更多,他们总是和万能的现实及其永无止境的需求站在一起,并使其保持生命力;实践者们与国家的运动更多地纠缠在一起,并与其他一切存在相联系;实践者处于市民社会之中,而理论家则总是置身其外。[21]
作为政治理论家的米勒同样也想做个政治实践家,把自己放到“运动的中心”去。他开始与普鲁士政治“亲密”接触,观察它、思考它。讲座集《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普鲁士君主制的特点》的面世表明,米勒已经从泛泛的国家学理论阐释转向对具体的普鲁士国家的个案分析,他要赋予整体性国家以直观和鲜明的特点,并且希望对症下药,用治国术的药方来解决普鲁士的问题。
米勒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国家及其生活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普鲁士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工厂,它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分裂的。“公共生活的代表是统治者或国家工厂的管理者,而象征私人生活的则是财富和虚荣”。[22]但是,普鲁士似乎又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个君主制统治下的军事—官僚国家,在弗里德里希的国家秩序下,君主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所有者,是庞大的思想和企业生产以及商业机构的管理者:
君主从旧有的复杂权力关系中挣脱出来,成了权力的唯一所有者。这个人现在开始关心开销、燃料、照明和治安了,给每个劳动者分配日常工作。他以货币和贷款为工具,轻松地做着清晰明确的计算。而劳动者的生活除了大工厂生产之外与统治者之间没有了其他关系。臣民的自由就在于完成每日机械性的工作,按照君主所满意的那样去行动,去思考,去生活。[23]
对此,米勒难以忍受。“如果这个天才——指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没有综观整体,而只有普通人的世俗眼光,那么这个天才以及他所发挥的作用又如何能被民族所理解呢”?[24]更有甚者,政府的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它甚至可以“通过捆绑、强迫、驱使,简言之是以各种机械手段进行统治”,“为人造的作品编织铁衣”。[25]这样的国家根本不是米勒所要的“整体国家”。因为所谓统治都是外在的,或者根本就没有统治。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是截然分离的,归属“两个主人”,对国家的责任和追求个人利益的私心难以协调。更重要的是民众感受不到上帝、宗教、自由、法律、忠诚以及所有富有力量的思想的结合。因此米勒提出,必须解释和解决这个时代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有第三种更高的善,一种理念,一种神性的思想,让责任和私利得到和解,把爱变成责任,把责任变成爱。只有这样,内在的自由和民族性才能真正焕发出来,毕竟,私人生活是自下而上的民族性的反映,而公共生活反映的则是自上而下的民族性”。[26]
于是,米勒开始深入普鲁士政治的核心,培养等级政治。在米勒看来,等级应该包括贵族地主、商人、企业主以及广大市民。而在旧时代,商人和市民等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米勒相信,等级政治不仅是历史的丰富遗产,对未来也是行之有效的。他期望把人按等级组织起来,因为单靠个人是没有前途的,只有通过某种政治形式,归属某个等级,个人才能发挥作用。并且,各等级只有与政府联合才能成为有决定意义的整体。国家内部应始终保持动态的政治结构,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不同等级形成不同政治派别,彼此对立与竞争,实现等级秩序的统一;二是政府和各等级制度之间形成对立与融合,构成国家整体。胡伯认为,德国最早的政党学说是从浪漫派中产生的,而米勒正是它的创始人。
在米勒的等级政治中,贵族政治是首要的。但是他也注意到,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贵族等级受国家政权和经济利己主义的侵蚀,正在逐渐解体,走向没落。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呐喊:
“要像英国一样通过继承法,一方面维持其强烈的荣誉观念与纯洁无瑕,另一方面也要维持其身份的珍贵,此外,要对来源于贵族观念的血统的纯洁性(尤其是男性成员)和家族关系的纯洁性进行严格监督。同时,仅有非常突出的功勋才可以晋身贵族阶层。”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不能抹去贵族从其出身中获得的优越感”,要“通过各种法律规定和荣誉奖励,来尽可能地捍卫贵族无形的本质”。[27]
保护贵族的财产私有权是米勒最为关切的。“要保留所有保护贵族家族的特殊制度,如信用委员会、长子继承权,以及一切对不可转让的财产和权利的规定”。米勒最担心的是一旦土地贵族和农民没落了,最后只剩下商人、企业家和犹太人。为此,他坚决反对农民解放,反对地产转让。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治下,王室领地的依附农的解放也成为风尚。
与此同时,米勒也没有忽略市民等级的意义。虽然贵族是国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必要的宪政等级”,[28]但为使君主了解民意和民众利益诉求,市民等级能够充当连接国家边缘和中心,并对君主产生影响的桥梁。市民议会通过人为选举产生,与靠自然出生形成的贵族议会组成二元对立,是国家理想的政治形态。因为真正的权力只能在无限的束缚中产生,同时,在这种权力与束缚之间无限的冲突中,才能产生普遍自由、权利意识和国家法。
为约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官僚国家,焕发真正的内在自由和民族精神,米勒赞同成立一个“民族代表大会”,这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因为英国的议会和法国的国民议会早就受到赞美和追随。但米勒的代表制有所不同,不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和相互制衡,而是把选举产生的、具有不同等级特征的且能承担责任的代表制度与君主统治结合起来,既尊重和保留传统君主制,又避免绝对君主制的弊端,而且可以充分调动国民参与民族性和公开性的建设,真正实现民族的自由。他认为:“只有把民众组织起来参与公共生活,国家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党派,才会产生伟大的二元性,充满活力的二元性,才会有真正的等级制度。只有这样,意志的永恒统一和坚强的行政才是可能的。这样,我们就不需要依赖天才,在任何环境下,政府自身就可以胜任。”[29]
其实,米勒不反对具有最高决策权的君主制,恰恰相反,在他内心深处,期待着在这个“特殊的国家”发生“一件振奋人心的事”,那位特别的统治者能为“百年王业推向巅峰”做出贡献。[30]只是,米勒所要的是在等级政治基础上的君主制。不过,作为典型的浪漫派,当对改革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探寻以何种方式、由哪些成员来组成国民代表大会以及赋予其何种职能时,米勒却小心地回避了。
1809年,当米勒再次回到普鲁士时,决计要把《治国术》理论付诸实践。而实际上,该书的出版也正反映了当时普鲁士现实政治中所表现出的普遍对立的情绪。1810年,哈登堡执掌政权,高居“首相”之职,领导改革,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推动普鲁士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以勃兰登堡贵族为首的地方等级则担心传统特权的丧失,反对中央行政集权化,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办法建立政权,强化等级制,成为政府的反对派。米勒卷入其中,第一个行动便是计划在柏林办两份政治报纸:官方的和民间的,作为政府操控新闻机构的有效武器。在8月20日一封给斯泰格曼的私人信件里,米勒这样写道:“我敢在国家参事院的授权下公开出版一份官方报纸,在参事院默许下出版一份匿名的民间报刊。换言之,既给大臣们也给反对派写文章。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普鲁士公共舆论的复活。”[31]
创办两份报纸的意图与他提倡的“对立学说”相符,米勒要开启一个新闻“对立”的时代,不仅要发出市民社会的自由声音,还要担当政府的喉舌。他相信,只有这样公共舆论才是鲜活和健康的。而哈登堡政府在宣传改革的问题上与米勒不谋而合。政府也希望通过新闻媒体影响公共舆论,对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阐述观点,深入讨论,消除异见,达成共识。不过,在普鲁士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米勒身上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代表政府,要么代表反对派。前者要改革,后者要复辟。在当时,米勒的思想是波动的,很难确定他的方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要创造公共生活的空间,认为只有让民众参与到公共生活中,通过矛盾和冲突,国家才会有活力。
1810年6月,普鲁士改革进入新阶段。哈登堡采取雷霆手段,与他的办公厅主任斯泰格曼频频出手,推出《税法草案》,废除一切封建残余,取消各省、各等级之间的差异,实现税收平等化,并将地方财权、债权以及行政权等重要事务移交中央政府。总之,哈登堡想通过税制改革统合普鲁士行政国家,将等级势力最终纳入中央集权制的行政体制。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而此时的米勒却与反对派领袖马尔韦茨(Friedrichvon der Marwitz)站在了一起。米勒和马尔韦茨,究竟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代替后者发声,学界存在着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力图捍卫君主与贵族间订立的神圣契约,承认君主主权得到贵族认可,政权则在君主与贵族间分配。米勒提醒马尔韦茨,哈登堡要摧毁传统等级政治,在普鲁士建立法国式议会。他写道:“没有旧等级就没有国家,没有传统贵族,国家也将不复存在。”[32]贵族所拥有的自然历史权利丝毫不容侵犯。对立斗争的舞台是《柏林晚报》。反对派不断撰文,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和目标。双方以报刊为中心,舆论战打得不亦乐乎。
这个时期,米勒还与阿尔尼姆(Achimvon Arnim)一起,成立了“基督教德国圣餐会”,集中了一批普鲁士重要的贵族反对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以《柏林晚报》为“布道台”,批评自由贸易、官僚制度以及资本的影响。1811年2月11日,由米勒起草抗议书,呈递国王,矛头直指哈登堡。文中罗列了哈登堡的种种罪状,说他要在普鲁士搞革命,挑起无产者对有产者、工业对农业、资本对地产、物质主义对神圣原则的战争。更进一步地,哈登堡还鼓励利己主义,压制利他主义,追求当下,漠视过去,以个体凌驾于家庭,鼓励投机,打击商人和农民,否定民族历史,以能力和知识取代美德和个性等等。[33]
哈登堡怒不可遏,他以行政手段将马尔韦茨、芬肯斯泰因(Finckenstein)送进了斯潘道监狱,关了六周。《柏林晚报》停刊,反对派阵营被瓦解。虽然文件是由马尔韦茨签署的,但米勒本人也被哈登堡打发到了维也纳,安排了一份可有可无的工作——外交记者,离开了权力中心。1813年,解放战争爆发,“基督教德国圣餐会”解散。
骑墙终归是没有出路的。施米特说,哈登堡不愿意再与米勒玩“对立”游戏。在首相眼里,重用米勒存在风险。为他安排公职,如果是朋友,可以发挥作用,而一旦成为敌人,则十分危险。这个出身市民家庭的浪漫派,最后彻底倒向了等级贵族。之后,米勒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他申请普鲁士公职遭到了拒绝,去维也纳成为他唯一的出路。1813年,奥地利参加反法同盟,米勒找到了在奥地利任职的机会,在蒂罗尔的奥地利军队中担任地方专员和政府参事,同时负责《蒂罗尔信报》的出版和发行。1815—1826年,米勒任奥地利驻北德总领事,常驻莱比锡。期间,他于1817年公开了政治浪漫派的天主教身份,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形势急速右转,哈登堡改革受到了阻碍,一批保守派官僚聚集在国王周围,逐渐把持了政局。1819年,诗人科采布(August Kotzebue)遭青年学生卡尔·桑德(Karl Sand)刺杀身亡。为压制德意志邦联内部日益兴起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在梅特涅主导下,邦联推出了《卡尔斯巴德决议》,而米勒正是决议的起草人之一,他成了彻彻底底的“反动分子”梅特涅的代理人。
对这个结果,曼海姆的分析是中肯的。米勒与贵族等级的结合不能长久,因为后者不能长期得势,因为未来不属于它,所以米勒跟早期的浪漫派知识分子一样,会成为没有社会属性,没有利益归属的人。不过,米勒的生命离不开政府,他的思想是要与权力结盟的,虽然他痛恨专制政体,但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寻找权力靠山,“把自己的文笔出租给当时的政府”。[34]而更重要的是米勒的政治思想,他要在世俗世界取得平衡的对立思想,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绝对君主制被否定了,但又找不到能够替代它实现平衡的政府体制,最后也只能寄希望于超俗的第三方即“高贵、崇高和神性的东西”。这也决定了米勒思想的最终归属,他只能属于浪漫派。
浪漫主义的“对立学说”作为普鲁士的显学是短暂的,甚至还没有梅特涅的政治生涯长命。米勒死于1829年,终年50岁。第二年,即1830年,巴黎发生“七月革命”,复辟时代结束。
斯泰因是拿骚帝国骑士的后裔,其家族和普鲁士关系密切。斯泰因16岁时就读于哥廷根大学,攻读法律,但对中世纪帝国史和普鲁士历史有浓厚兴趣。1780年,斯泰因就职于威斯特伐利亚矿产部门,负责矿场改造。此后,又先后出任克勒弗马克矿业局长和威斯特伐利亚战争与王室领地管理委员会主任。1804年赴柏林,荣升普鲁士财政和经济事务部大臣。1806年,普鲁士战败,斯泰因随宫廷一路向东逃亡,先经科尼斯堡后赴梅梅尔,并在此出任普鲁士国家资产部大臣。期间因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发生龃龉,斯泰因被解职,但旋即又于1807年夏复出,开始主持普鲁士改革。
与米勒不同,斯泰因不是思想家,他反对抽象理论,轻视政治哲学家,称之为“玩弄辞藻的人”,并嘲笑“治国术”就是一门“抖机灵”的学问。他的改革更多是吸收了时代同仁们的思想精髓。但即使如此,后人在研究斯泰因时,还是想要追溯其思想渊源,尽管其很难厘清,甚至还会引发不同派别的争论。其中,关于斯泰因是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问题便是见仁见智。至于他与米勒之间是否有直接接触和交往,也无更多史料佐证。
青年时代,斯泰因显然是受到了他的同窗好友雷贝格(August Wilhelm Reghberg)和布兰德斯(Ernst Brandes)的影响,作为“汉诺威学派”的重要成员,他们将柏克的思想传递给了斯泰因。斯泰因与柏克都看重基层社会的重建,赞同具有差异性的等级社会,尊崇土地贵族,支持改善依附农地位,焕发乡镇生活的生机。应该说,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帝国骑士的出身对斯泰因影响更大,因为这些是他血脉里的东西。兰克说,“斯泰因身上所特有的精神植根于他成长的土壤”。[35]
斯泰因与尤斯图斯·默泽(Justus Moeser)的关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默泽将古老的等级制度、贵族特权做了顺应时代的改造,使中世纪的宗团主义与启蒙的政治理论达成了和解。在他的“国家股份制”理论中,等级是国家建构的核心支柱,土地贵族和农民、市民及手工业者各得其所,构成了古朴和其乐融融的德意志乡村和城市景象。斯泰因应该是接受了这一教诲,1817年12月18日,在给胡费尔男爵(Freiherrn von Hoevel)的信中,以及后来对卢梭的批评中,斯泰因都表达了对国家契约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和民族不是一件艺术作品,不像新开垦的殖民地那样可以人为创造。它是有机生长起来的,国家的健康发展只有与它的历史相连才是可能的。[36]与出身于奥斯纳布吕克贵族世家的默泽一样,在拿骚成长并在威斯特伐利亚从政的斯泰因,试图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充满社团仪式的、有德意志同盟精神的有机体”。[37]
斯泰因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家、实践家。他在工作中思考和行动,拒绝一切不切实际的东西。普鲁士改革开启于耶拿战败之后,同那个时期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对法国革命原则的欢呼和迷恋是一种正常现象。在斯泰因及其改革派的圈子里无法排除自由主义的观念,启蒙理性、个体权利等都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正如曼海姆所说,“这种反应从根本上说究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应,实际历史因素的随后发展几乎将此颠倒过来”。[38]
这个历史因素指的就是现存的国家和等级制度。斯泰因是从旧制度过来的,对旧制度的状况十分清楚,对他所服务的那个普鲁士国家有切肤之感。他不喜欢弗里德里希国家的政治基础,虽然他认可君主的勤勉和德行,但在所谓的开明专制下,人就像机器零件一样被操控,变得麻木、堕落;而整个官僚机器以及精神状态则日趋僵化,缺乏弹性。1821年8月24日,在给加格恩(Gagern)的信中,斯泰因对官僚制度有过一段辛辣评价:
官员们领取报酬,只追求工资的获得和增加;他们受过教育,却停留在照本宣科的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中;他们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因而与市民阶层没有接触;他们自己就是一个特权阶层,只会打字的特权阶层;他们没有财产,所以财产的一切变动都与他们无关。无论下雨晴天,无论捐税增加还是减少,无论是摧毁旧权力还是任之存留,这一切他们都毫不关心。[39]
但是,即便如此,斯泰因也并不主张推翻现存国家机器,而希望对旧制度进行顺应时代的调整,赋予它新的精神内涵。
同样不能推翻的还有等级制度,这也是斯泰因所尊重的自然—历史权利。但他真正熟悉的是他生长的西部乡村和贵族世界,称它“自主、富有力量”。对普鲁士君主制的核心地带东部地区,他所知甚少且印象极差。在他眼里,那里的农村单调、死寂、缺少活力、令人沮丧。贵族的庄园像野兽的巢穴,周边被墓地包围,肃杀荒凉。不仅如此,东部的贵族等级思想僵化、品行低劣、极端自私。对此他痛心疾首。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斯泰因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是焕发民族精神,推动公民参政。在那份著名的《拿骚备忘录》中,斯泰因改革的核心意图得到了充分表述:“要活跃共同精神和公民意识,利用沉睡或被误导的力量以及分散的知识,恢复对祖国、独立和民族荣誉的情感。”“如果财产所有者被排除在所有省的行政管理之外,那么将他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失去了意义,他那些关于财产和公民身份的知识就产生不了作用,他追求完善、缓解不幸的渴望就会减少,他的业余时光和才能就会付诸娱乐和蹉跎,而这些本来是应该在另一种环境下心甘情愿奉献给国家的”。[40]
为此,首先要解放人,把农奴从国家和封建制度的约束中释放出来,通过废除封建领地义务,保障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等,让他们经济自立,成为有产者;而后让他们参与行政,并逐渐“习惯”于自我管理。1807年政府颁布的《十月敕令》是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而1808年10月13日的《乡镇自治条例》和1808年11月19日的《城市自治条例》则是为了满足第二个意图。
当然,等级政治的意义从来没有离开过斯泰因的视野,这是他体制改革的核心。但是斯泰因对新时期等级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它不再限于贵族地主和地产所有者,还包括其他所有的有产者阶层,也就是说它建立在私有财产和知识能力基础上,而不再只是依靠出身和世袭。斯泰因写道:“那些贵族是国家的负担,数量庞大,大部分很穷,向国家要补贴、特权和各种优惠待遇。他们的穷困是缺少教育引起的……也因此无力提高自己的地位。”[41]未来,代表贵族等级的应该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有见识、有财富的那些人。终其一生,斯泰因都相信,“健康的”贵族等级是国家必不可少的,即使他不断地呼吁农民和市民的解放。
1808年11月19日,政府发布《告普鲁士君主国全体居民书》,其中宣称:“自由人所拥有的权利,从今以后农民和城市市民可以享有。通过参与政务你们可以实现自我管理,并由此推广和完善等级制度。你们当中最诚实和最能干的人应该代表各级政府,各类学者和专家要成为各个行政部门中的顾问。市民们用自己的双手创建自己的政治集体,废除当局政府的监管。”[42]
按照斯泰因的设计,公民不是以个体身份,而是以某等级代表的身份参与行政。代表产生的办法依靠等级,由各地各等级推选产生。这是他所设想的代表制的基础和框架。不过,斯泰因也是务实的,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看到了农民解放和公民参政可能带来的好处。
在斯泰因主持政局前,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面临困境。对农村土地的投资已无利可图,贵族用以抵押土地的债券实际价值跌落至面值的1/3。城市被饥饿和瘟疫包围,贫困带来了高死亡率。1807—1808年间,在柏林出生的婴儿有5846人,死亡者却达到4300人。自杀率快速攀升,柏林每周自杀人数从6人上升至10人。从勃兰登堡省长萨克(Johann August Sack)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官员的情况也很惨,一些下层官员变卖家具,最后只剩下一张床。解放农民,活跃市场经济,提高生产力,改善民生,似乎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43]
法国占领期间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战争赔偿,也像一座大山,压得普鲁士政府喘不过气来。公民参政既可以节省行政开支,还能削弱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并克服官僚身上的“雇佣精神”和“教条心理”。行政体系的开源节流明显受到了英国自治的启发,在《拿骚备忘录》中,斯泰因引用了英国公共行政的例子,认为英国自治由地方乡绅主导,有较高声誉,不领政府薪俸,而是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承担自愿参加地方治理所产生的费用,他们不属于“职业官员”。这样做不失为政府节流的好办法。
斯泰因执政时期,公民参与的等级政治开始全面推广。在基层乡镇,要实现最大程度的有产者的治理;省一级要由等级代表参与管理;而在中央层面,则设立某种委员会,比如立法委员会,成员包括等级代表,为政府决策提供专业信息,为政府立法提供法律咨询。当然,最高目标是成立“民族代表会议”。公民,无论是拥有一千公顷土地(相当于100胡符)的地主,还是农业、工业或贸易的从业者,无论其拥有资本还是知识,都有资格成为“民族的代表”。
但是,这套方案在具体实施时遭遇了挫折。乡镇自治最先受到抵制,大多数东部的农民和市民根本无法进入各县的代表机构,所有代表席位都落入传统贵族手里。省代表会议中,只有东普鲁士省的实践是成功的,1808年2月,在斯泰因的亲自主持下,会议在“战时首都”科尼斯堡顺利召开,代表中除了贵族,还有自由农民及市民,有的代表甚至不再接受推选人的授意,而是独立投票,这是历史性的突破。增加税收等重大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都获得了通过。但其他省份如西里西亚、波莫瑞和勃兰登堡由于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在税率问题上,讨论的结果居然是贵族的应纳税率低于农民。
“民族代表制”方案是斯泰因委托雷迪格(Karl von Rehdiger)设计的,但它的困难不仅仅在于究竟实行“两院制”还是“三院制”,[44]还在于斯泰因想减少贵族家族的代表权,选拔那些有才干的富裕贵族进入议会,并腾出位置给更多其他阶层的代表。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代表权依旧由传统贵族掌握。
改革不尽人意,现实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是原因之一。首先,经济改革处于起始阶段,在依附农还没有得到解放之前,有产者阶层只能是那些曾经的地产拥有者——贵族地主。且不说有关经济解放的法令朝令夕改,等级贵族的强烈抵制使任何一项措施都步履维艰。其次,斯泰因在内心深处对等级制度是青睐的。尽管他不否定甚至鼓励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这种权利和自由是有社会性的,划分等级的。有历史学家认为,斯泰因的改革就是为等级贵族利益服务。比如,《十月敕令》的出台是为了使贵族摆脱庄园里多余的农奴,农民们因此丧失了保护,不仅如此,该法令也为地主有恃无恐地公开吞并那些没有继承权的农民的小块土地提供了方便。而所谓的地方自治实际上也是为了增加而非削弱容克的政治权力。[45]事实上,直到1810年哈登堡上台,贵族们一直在利用敕令提供的机会,牺牲农民的利益,扩大地产,改变领地的财政状况。1808年夏西里西亚的农民暴动反映了这一问题。因此,结合斯泰因对贵族等级的各种言论,波岑哈特将斯泰因改革直接称为“贵族改革”[46]就不足为奇。
在贵族领地司法权问题上,斯泰因也是模棱两可。1808年,一位法官曾给斯泰因去信,为领主法庭辩护。他提出的理由是,依附关系是一切国家的根基。教育人们从年轻时开始学会服从是贵族的责任,如果领地丧失了警察和司法权,那么服从也就荡然无存。另有一封呈给国王的请愿书,其中也写道:保留现存制度是国王应允的,其中领主法庭最重要,它是纽带,通过忠诚和情感,把地主和依附民紧紧联系在一起。[47]斯泰因对此表示接受,因为直至他于1808年11月离职前,领地司法改革始终没有提上日程。
尽管作为改革的领导者,斯泰因必须讲求实际,解决现实问题,但他也有个人情感、等级烙印。仍然可以看到斯泰因身上有浪漫主义色彩。1821年11月8日,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国家,绝不是初级产品生产和加工的联合会,不是农业经济和工场产品的协作机构。国家的目的是促进宗教、道德、精神和物质的发展。”1820年3月28日,在与斯皮格尔(Spiegel)伯爵通信时,他再度表达了对国家的看法,国家的主要功能不是做民众的衣食父母,“在我看来,它是宗教—道德、知识和政治的完美体现”。[48]在这个问题上,斯泰因与米勒观点一致。关于国家,米勒有这样一段经典表述:“国家不是简单的制造商和管理机器,也不是机械的社会。它把社会中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紧紧连在一起,它是社会生活的化身,伟大、精力充沛,代表着整体有生命力的发展。”[49]
既然是整体的“有机国家”,行政与立法当然合二为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在普鲁士既无理论市场也无实践场所。在1806年4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斯泰因称:“普鲁士没有国家宪法,最高权力不是在国家首脑和国民代表之间分配的。”[50]虽然“自治”(Selbstverwaltung)是斯泰因一生的志业,但不同于英国建立在议会政治基础上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完全分离的地方自治,斯泰因所提倡的是在行政领域进行的分权管理,参与行政事务的公民既有行政权也有立法权。让民族中最优秀的人参与公共事务,为各个等级中拥有杰出才能者提供机会,实现国家的最大幸福,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全体人自由、责任和共同参与权,这是斯泰因最大的政治理想。
斯泰因执政生涯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个性中的漫不经心、人际关系中不善于转圜给他带来了厄运。在一封信中,他不加掩饰地谈及要以西班牙为榜样,实现德意志的崛起,但不慎落到法国人手里。于是,在拿破仑的压力下,加上内部政敌的攻击,1808年11月24日,斯泰因被免去所有职务,彻底离开了普鲁士。之后他曾前往波希米亚。1812年,当他再度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已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座上客。他寄希望于依靠俄国来拯救欧洲的自由,拯救德意志的“尊严和独立”。
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斯泰因小心维护着他作为欧洲“世界公民”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声誉。对此,梅尼克的评价是:“邦国与民族的纯粹政治使命恰好与统一并解放欧洲的普世使命相合,在政治浪漫主义的意义上,健康的国家利己主义与普世主义也是相通的。”[51]历史学家哈通(Fritz Hartung)也竭力为斯泰因辩护,说他即使作为沙皇的谋士,也没有丢掉德意志人的品性,他还是德国人,还在为德国做事。如1813年1月,他亲赴东普鲁士领导解放战争,当然是作为沙皇的顾问。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为解决德国问题而左右调停。[52]
但是,在如何构建未来德意志国家的问题上,斯泰因逐渐对逝去的“德意志帝国”产生了某种幻想。在1812年9月17日的《彼得堡备忘录》中,斯泰因首次提出了战后德国的政体问题。在他看来,10—13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强大、富于智慧,法律也是昌明和自由的。[53]在翌年8月的《布拉格备忘录》中,他再次提出,应该建立一个由奥地利皇帝来治理的帝国,皇帝在帝国法院的监督下行使行政权,负责军事、外交和财政;加强帝国议会的立法权,宣战权则由等级贵族转交皇帝。[54]
斯泰因对帝国的“记忆”源于对现实的失望,对梅特涅的奥地利和哈登堡的普鲁士,他都不满意。1815年后的德意志邦联不是他所期待的那个能够代表德意志人民的国家。不过,斯泰因赋予“浪漫”的历史时代不应该是10—13世纪,而是15世纪,“最后的骑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执政期间(Maximilian I,1459—1519在位),曾推行政治改革,旨在加强中央集权、遏制政治分裂;建立法律体制,在帝国范围内实现“恒久法律和秩序”;建立等级代表制,维护和保障各等级权利。
不过,吊诡的是,这个时期斯泰因几乎所有的《备忘录》都是呈给欧洲最大的“反动派”亚历山大一世的,而且《备忘录》中所描述的德意志历史也并不准确。斯泰因传记作家施密德特(W.A.Schmidt)曾批评说,斯泰因对帝国的想象充满着“错误、矛盾和天真”,他“根本不理解1815年的欧洲局势”。[55]诗人、女历史学家胡赫(Richard Huch)更是指责斯泰因美化中世纪帝国的荣光,反对贵族绝对主义,鼓吹社会公正,具有“帝国思想”。她甚至认为斯泰因是潜在的革命帝国的制造者,1814年还做过当皇帝的游戏。[56]当然,后面的指摘没有被证实。
曼海姆在批评米勒思想的“浪漫”气质时,强调其将“历史”浪漫化,将等级制意识形态化。其实,在斯泰因身上,这种痕迹也十分明显,尤其在后期,在他脱离政治岗位、离开政治实践场之后。不过,在未来的等级政治问题上,斯泰因的理想却不是“浪漫”的。1815年国王的宪法许诺,鼓舞了斯泰因继续推动省等级代表制度的热情。1823年6月5日,普鲁士颁布《省等级会议法》。主要内容如下:建立省等级会议;地产是拥有等级代表身份的条件;省等级会议是各省各等级组成的法定机构;所有涉及具体省份的国家立法草案,均交由省等级会议讨论;本省乡村基层事务,由省等级会议出具决议,国王保留批准和监督权。[57]
应该说,该法案部分实现了斯泰因的设想。传统等级界限被突破,有产者以土地贵族—农民—市民为选举单位开始参政议政。1826年,西威斯特伐利亚等级会议首次召开,讨论批准《省等级会议法》。三等级代表比例大致为1∶1∶1。相对于东部各省贵族代表均超过半数,西部省份的等级制改革显然成效很大。斯泰因是等级会议的当然领袖,但法律赋予会议的权限在他看来实在有限,等级会议只有商议权,而无决策权,更无行政权。君主—官僚制度依然是普鲁士的根本。斯泰因所开启的改革,特别是“公民参政”代替官僚政治的目标与现实越来越远。
1819年,斯泰因出资新建了德意志文献集成研究所,希望通过编辑德意志早期历史文献史料,激发人们对早期德意志历史的理解和同情。1826年,在斯泰因推动下,研究所出版了第一卷《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简称MGH)。对德意志中世纪历史的迷恋并未使斯泰因丧失对现代的信念。虽然对时代不满,复辟的政治以及解放了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无产者化,都让他感到失望,但斯泰因并不想以牺牲现代来赞美过去或中世纪。在时代的喧嚣中,他没有放弃引导人们向善。直到最后,他还希望通过对“不成熟”民众的政治教育,就像他为普鲁士改革所设定的方向那样,来最终实现自治理想。1831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的第二年,斯泰因逝世。
普鲁士改革时期的浪漫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思考,也是一种政治行动。作为理论思考,它不成系统,施米特说它仅是一些思想的“断篇”,只是把它所看到的“对立”转化成一种具有审美平衡性的和谐。这一特征在米勒身上表现明显。但梅尼克却认为,浪漫主义其实是有哲学思考的。他评价道:“假如米勒能够将其所具有的关于国家的整体观建立在一系列具体经验之上,假如米勒不仅能够将其称之为‘观念’的事物,也能将其称之为‘概念’的事物各得其所,并不再缺失思想的尖锐性与清晰性,那么他本人便有可能由于上述努力而成为一位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58]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h)也指出,存在一种理论与思辨含义上的浪漫主义,是对在启蒙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学院主义和哲学唯理智论的论战和评判。它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是思想激荡的过程,具有批判性,富有诗性,强调激情、个性和自发性,有时甚至会出现极端和冒失,但最终走向理性。[59]克罗齐对浪漫主义的评价用之于米勒,似乎也并不为过。
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米勒是有意为之,但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归根到底他只是一介文人,是从“浪漫”的理论出发来指导行动。与其他浪漫派一样,他天生具有高度敏感性,能抓住或占有历史中存在的事物,如等级制、君主制等,对它们加以“浪漫化”或者再发现,并借助思想的“技巧”把它们提升到更高的解释层面。普鲁士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经验“构想”出了米勒的思想观念,并进一步被试图用于指导普鲁士的历史实践。只是,在米勒身上出现了悖论,他“介于不着尘世的理想主义和只专注眼前事务的官吏之间”,“既不是抽象的热心家,也不是狭隘的实践者”,他是天生的历史哲学家。[60]
而作为政治家的斯泰因则不同,他从具体实践出发,来思考现实中的理论问题,但最后却走向了政治浪漫主义。作为改革家,他与米勒一样,也善于抓住普鲁士历史中的等级制和君主制,并将它们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改变。但有别于米勒,斯泰因并不以“浪漫化”来理解普鲁士历史,而是实实在在地生活于日积月累的历史传统中,并在其中为它说话,为它行动。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员,斯泰因试图利用等级政治,使之发挥作用,而不是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斯泰因可以被视为保守主义者。只是,在他退出政治核心圈之后,将历史作为“反思”和“记忆”似乎成为斯泰因追求的价值取向。梅尼克评价说:“斯泰因男爵在为德意志民族努力奋斗与思考的岁月中,同时也成为政治浪漫主义思想体系发展的承接者——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思想体系后来被称之为神圣同盟。”[61]从这个角度说,斯泰因最终还是落入了米勒之流的浪漫派行列。
在普鲁士改革中出现的浪漫主义,不是什么“反动”的意识形态。施米特解释说,“反动”是由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赋予给它的。1819年,为了应对拿破仑战争引发的全欧范围的宪政民主热潮,梅特涅颁布《卡尔斯巴德决议》,革命时期广为传播的自由精神陷入低谷,直至19世纪30年代。而这个阶段恰恰也是浪漫主义最活跃的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直到1848年革命发生,欧洲的革命者一直将浪漫主义视为政治对手,把它定性为“反动的绝对王权主义的意识形态”,[62]说它害怕革命,是“限制真正自由的敌人”。当然,说它“反动”,还因为另一个事实,即很多浪漫主义者最终皈依了天主教。
1815年解放战争结束,普鲁士逐渐转向理性的、新教的保守主义路线,与旧制度亲和,走上“复辟”的道路。但此时,无论是米勒还是斯泰因均已退出普鲁士的政治舞台,他们身上带有“复辟”色彩的思想也因为与政治运动完全脱节,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浪漫”思想。普鲁士改革时代结束了,浪漫主义的政治行动就此落幕。
作者简介:徐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近代史。
[1] [德]威廉·亨利希·瓦肯罗德著,谷裕译:《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
[2]作为文学的浪漫主义以及浪漫派哲学是德语文学界和哲学界的经典话题,而国内史学界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则并不多见,且大多聚焦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后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本文将普鲁士改革与浪漫主义运动结合起来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将斯泰因作为浪漫主义者加以研究更是第一次。本文受到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以及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浪漫派》(Political Romanticism)的影响。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对亚当·米勒(第七章“1808—1813年间的亚当·米勒”)和斯泰因(第八章“1812—1815年的斯泰因、格奈森瑙与威廉·洪堡”)思想的分析,曼海姆对德国早期保守主义的精辟论述,以及施米特对政治浪漫派的深刻批判,对笔者有重要启迪。
[3] [德]卡尔·施米特著,冯克利译:《政治的浪漫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4]学界常以1806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为界,将浪漫派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情感的迸发,表现得灿烂而活跃;后期则转为深沉的思考,尤其是对与民族精神相关的政治问题的思考。
[5]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22页。
[6] Friedrick Ⅱ, “Forms of Goverment and the Duties of Rulers”.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3549(2021-03-25).
[7] “Maikaeferei”,因其成员聚会地点位于柏林五月酒馆附近的“自由宫”而得名。
[8] “基督教德国圣餐会”的主旨是建立强大的普鲁士,驱除外国影响,拯救历史传统。它主要呈现的是浪漫派的文学运动,与宗教并无实质关联。而“麦凯弗雷”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浪漫—保守派俱乐部,由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倡议成立,初衷也是以合法性与基督性对抗法国革命。该组织成员除了浪漫派人物,还包括许多重要的贵族保守派政治家,如福斯-布赫(Karl von VossBuch)、斯托尔贝格(Cajus Stolberg)、比洛(Friedrich von Buelow)等。不过,它存在明显缺陷,布伦塔诺是天主教徒,盖拉赫(Gerlach)兄弟也试图把政治和宗教混合,与“摩拉维亚兄弟会”特别是其成员塔登(Adolfvon Thadden)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819年,“麦凯弗雷”被关停。
[9] Matthew Levinger, Enlightened Nation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1806-1848,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6.
[10]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36页。
[11] Guenter Birtsch, Derpreussische Hochabsolutismus und die Staende, in Peter Baumgart(hrsg.), Staendetum und Staatsbildung in Brandenburg Preussen,Berlin: de Gruyter, 1983, S.403.
[12]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Berlin:J.D.Sander, 1809, S.25.
[13]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43页。
[14]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23.
[15] [德]卡尔·曼海姆著,李朝晖译:《保守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16] Ernst R.Huber, Nationalstaat und Verfassungsstaat: Studien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Staatsidee, Stuttgart: W.Kohlhammer, 1965,S.52.
[17]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27.
[18]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15.
[19]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7.
[20]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16.
[21]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21.
[22] Adam Mueller, Ueber Koenig Friedrich Ⅱ und die Natur, Wuerde und Bestimmung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 Berlin: J.D.Sander, 1810,S.31-32.
[23] Adam Mueller, Ueber Koenig Friedrich Ⅱ und die Natur, Wuerde und Bestimmung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S.29.
[24] Albrecht Langner, Adam Mueller 1779-1829, Paderborn: Ferdinand Schoeningh 1988, S.95.
[25] Adam Mueller, Ueber Koenig Friedrich Ⅱ und die Natur, Wuerde und Bestimmung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S.28.
[26] Adam Mueller, Ueber Koenig Friedrich Ⅱ und die Natur, Wuerde und Bestimmung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S.45.
[27]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260.
[28] Adam Mueller,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S.266.
[29] Albrecht Langner, Adam Mueller 1779-1829, S.96.
[30] Adam Mueller, Ueber Koenig Friedrich Ⅱ und die Natur, Wuerde und Bestimmung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S.59.
[31] Ernst R.Huber, Nationalstaat und Verfassungsstaat: Studien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Staatsidee, S.56.
[32] Robert M.Berdahl,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2.
[33] Wilhelm Mommsen(hrsg.), 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Eine Auswahl vomVormaerz bis zur Gegenwart, Muenchen: C.H.Beck, 1951, S.9-12.
[34]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127页。
[35] Fritz Hartung, Freiherrvon Stein, in Zeitschrift fuer die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Bd.91, H.1.(1931), S.4.
[36] G.H.Pertz, Das Leben des Ministers Freiherr vom Stein, 1849-55, Bd.5, Berlin:G.Reimer, 1850, S.166.
[37] Fritz Hartun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 Verwalt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Otto Buersch(Hrsg.), Modern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1648-1947, Berlin: de Gruyter,1981, S.686.
[38]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118页。
[39] Hans 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d.2, Muenchen: C.H.Beck, 2008, S.304.
[40] “Nassauer Denkschriftzur Staatsreform im Preussen”.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document.cfm?docu_id=3552(2021-03-25).
[41] Herbert Obenaus, Anfaenge des Parlamentarismus in Preussenbis 1848, Due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84, S.38-39.
[42] “Ordnung fuersaemtliche Staedt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document.cfm?docu_id=3553(2021-03-25).
[43] Robert M. Berdahl,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 p.108.
[44]由贵族和高级教士代表“显贵”组成上院,由有产者和受教育阶层组成第二院,由国家参事院充当第三院。但斯泰因有不同意见,他反对文官和军官代表(第三院的主要成员)参与,因为他们没有独立人格,职责是服从,无法表达民意。
[45] Klaus Epstein, “Stein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andTheory, Vol.5, No.3(1966), p.254.
[46] Erich Botzenhart, Adelsideal und Adelsreform beim Freiherrn vom Stein, Westfaelische Adelsblatt, Bd.5, 1928,S.210-241.
[47] Robert M.Berdahl,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Nobilit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Ideology, 1770-1848, p.122.
[48] Fritz Hartung, Freiherrvon Stein, Zeitschrift fue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S.14. Anhang 2.
[49] Ernst R.Huber, Nationalstaat und Verfassungsstaat: Studienzur Geschichte der modernen Staatsidee, S.54.
[50] Ernst R.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Stuttgart:Kohlhammer, Bd.1, 1957, S.291.
[51]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119-120页。
[52] Fritz Hartung, Freiherrvon Stein, Zeitschrift fue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S.18.
[53] “Petersburger Denkschrift”.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3597(2021-03-25).
[54] “Prager Denkschrift”. 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3598(2021-03-25).
[55] Klaus Epstein, “Stein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p.246.
[56] Klaus Epstein, “Stein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p.258.
[57] Allgemeines Gesetzwegen Anordnung der Provinzialstaende. https://reader.digitalesammlungen.de/de/fs1/object/display/bsb10509524_00139.html(2021-03-25).
[58]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97页。
[59] [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十九世纪欧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60]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第127页。
[61]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120页。
[62]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第19页。
敬告读者
近期,有部分网站和个人假借《史学集刊》编辑部的名义,通过虚假投稿渠道向投稿者收取所谓“审稿费”,损害了本刊及广大作者的合法权益。《史学集刊》郑重声明:
http://shxz.cbpt.cnki.net是本刊唯一官方投稿平台,本刊从未委托其他任何单位、个人和网站组稿或代收、代转稿件。请广大读者及投稿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