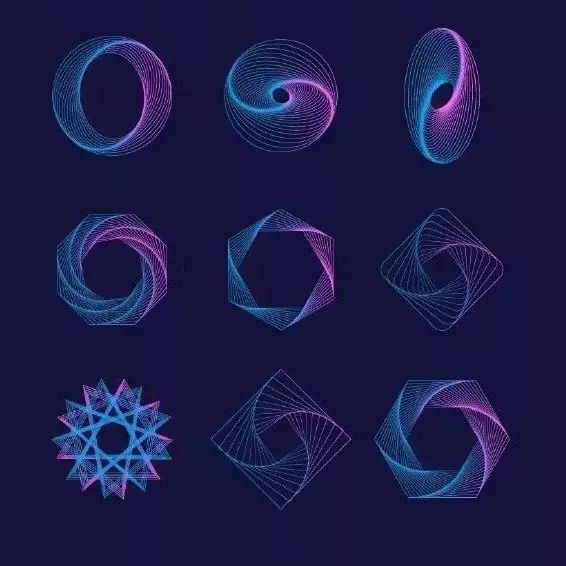不管是礼、宗教、道德、习惯,还是巫术,都离不开中国社会本身的特色。在一个工商业社会,在一个科技相当发达的社会,很多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比如大多数人在今天都不会在乎是否死后会上天堂,“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才是常态。现代性的除魅,核心的不是思想上的变化,它们只是物质变化的附随结果,礼法传统之所以能够标识中国社会,乃是因为传统社会本身的特色。那么,中国传统社会是什么样的?当然有着很多的理解思路,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
中对中国的描述很有解释力,礼法传统在社会治理中,实现了国家可以调动的资源与静止社会所需要的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平衡。
费老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其实,任何社会在最早期的时候,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就自然要依赖于土地,且强调延续性进而导致保守。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关键不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乡土社会,而是为什么中国的农业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持续那么久,搞得还那么红火,能够保证这个文明的延续。这个关键在费老的书中没有说,当然这并不代表费老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江村经济》已经触及到了后农业之后的问题,黄宗智先生将这本书置于更高的地位,而《乡土重建》则已经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乡土社会的重要特色在于“差序格局”。
虽然苏力老师在《较真差序格局》一文中认为费老概括的“差序格局”不能作为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说任何社会都是差序格局的,所以这个概念的解释力不强。实际上,苏力想要指出的是,差序格局不是中国的特色,而是落后社会的通病,这是原则而非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费老所说的差序格局与其说是中西之异,不如说是古今之别。
苏力的说法不错,这也与苏力本人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但是我们可以问的是,为什么差序格局在中国可以持续这么久,而同时代的西方社会里,差序格局早就被平等的公民秩序所代替了。当然有很多的解释进路,最流行的是《论法的精神》的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中国人也如此理解,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解,法律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法律的精神其实就是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传统中国的那个样子可以从地理、气候、人种、产业等等的角度去理解,我这里不对中国的法律精神理解。我们主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分析,福山说古代中国是政治早熟的国家,在国家能力的多个方面都比较先进了——缺少的是法治以及民主的维度,福山的批评我们先不管,先看看这个国家能力的问题,古代中国有什么样的国家能力?
《乡土中国》中说的是乡村的情况,是一种近乎微观的写法,乡土中国和差序格局下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呢?“皇权不下县”是典型描述,县以下就是费老所描述的那样乡绅的治理,那么中央政权如何能够管控这些自治的乡村?古代的中央政府的管理很少的,但是古代比较强大的一点是,对意识形态上管得非常厉害,而且有着非常强的宣传工具,那就是皇帝对儒家经典的掌控。所有读书人都渴望成为天子门生,而少数科举成功的读书人更是儒家礼教的最好的宣传者,古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几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科举做官。古代农村中的那些有钱人,一般都是因为可以通过读书成功而避税,因为士绅不纳税、不纳粮,所以才能慢慢积累财富,在生产效率低下的情况下这是最便捷的道路。差序格局靠的就是熟人社会下的“关系”来维持层级和亲疏,维持秩序的成本被限定在社会维度,国家不需要付出治理的成本,这也符合当时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