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 61 坎坷的离职创
业路聊起,向未
来看的思维、side project 的习惯和追求自由的态度贯穿始终。
曾拜访过谜底科技的办公室,十分羡慕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态——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花样
文
字或许是
运气
,
OffScree
n 源于
一拍
即合的理念
,
谜
底时钟则是始于数
据分析
。但共同点
是沉寂一年之久才突然火起来
,过程虽然煎熬,但没
有停止过打磨产
品
。
以下内容来自于 2022 年 1 月录制的三五环第 61 期播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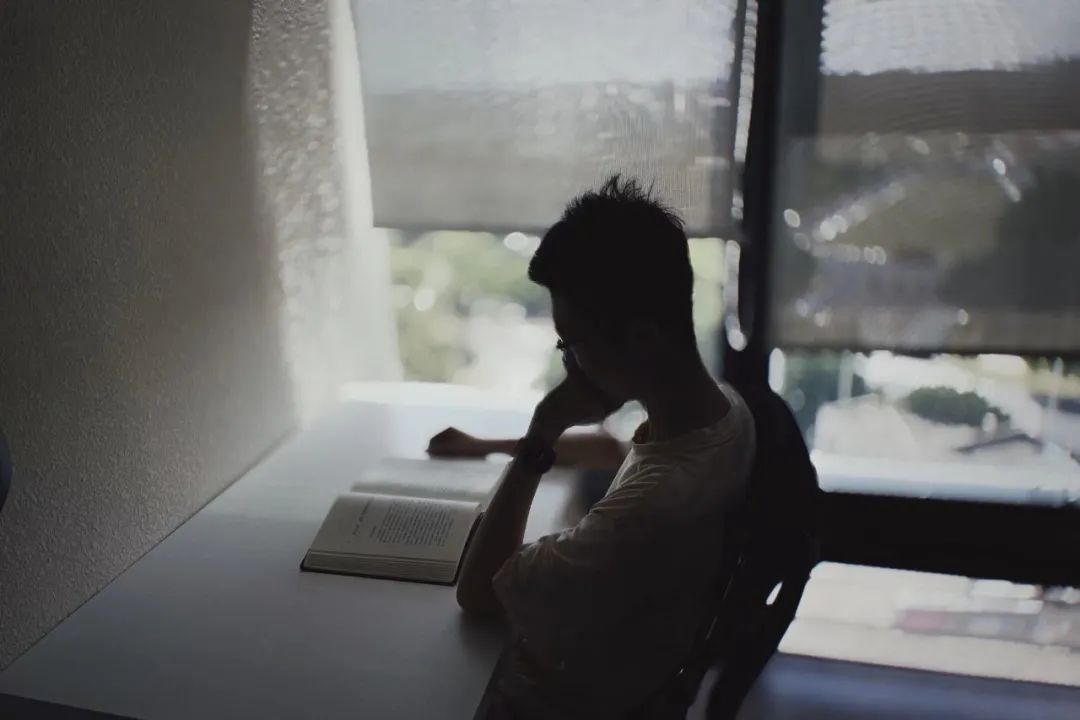
01 毕业初期的职业选择
02 不再去追求大干一场
03 公司的第一个产品诞生于「副业」
04 没有因为数据不好就停止打磨
05 酒香也怕巷子深
06 关于我们要做什么——不同阶段的思考
07 OffScreen 本质上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01 毕业初期的职业选择
61:
我是 2012 年毕业,2011 年秋招的时候拿到阿里云的 offer,但没有去,那时选择了杭州的一家创业公司,也是做工具类 APP 的叫 Doit.im。从 2011 年到 2012 年我正式毕业期间,我一直在 Doit.im。毕业后八个月跳槽去了阿里,在阿里待了两年多时间。
刘飞:
当时做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61:
在学校的时候对阿里是比较憧憬的,后来我去面试过一次,格子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
象
,当时觉得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一种办公状态。
后来我在微博上看到了 Doit.im 的招聘信息,他们发了一些图片,当时被那种硅谷风格吸引——人
少和
那种创业的氛围,非常吸引我,我就拒了阿里去了Doit.im。
后面选择去阿里,因为工作到了一个阶段,认为还是要去大厂去看一看。当时我们是做网盘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天天研究 Dropbox,有一个对标的优秀产品,你也想做得跟它一样好。
* Dropbox
:
云存储软件,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盘。
刘飞:
你现在做产品或开发的一些方法是从那个时候积累和输入的吗?
61:
是的。从那个阶段开始,养成了研究产品的习惯,
知
道哪
样的产品是好的
。比如,不断地去看它有哪些新的 feature 或体验。
这个过程就像在打基础,可能不是技术上的基础,而是兴趣和整体上如何做一件事情的基础。
刘飞:
当时离开阿里是为什么呢?
61: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些格格不入。我对产品的细节和体验非常看重的,但大家都说阿里是做生意的,所以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给你去打磨,你就会感觉整个环境是比较粗、比较急躁的。
02 不再去追求「大干一场」
61:
我一直是那种往未来看的心态,过去的经历就过去了,没有任何的留恋。我 2015 年 6 月从阿里离职,在远程的时候是做外包,几个月时间就开始了创业,做了一年零两个月解散。
刘飞:
那时候你会迷茫吗?可能以前的同事都在阿里升职加薪。
61:
确实很迷茫。不过那个过程其实蛮刺激的,觉得要干一件大事了。结束的时候,觉得
不太可能回去上班了
,因为已经
享受过那种自由的状态
。这种自由的状态不是闲,反而每天都是一种很拼命的状态。享受过这种做产品的状态之后,回公司做一件我不太喜欢的事就不是我的首选。
这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能做什么。
我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习惯,在任何阶段我都有 side project
。比如说我在实习的时候,就开始想我自己能做什么 APP。
我
在阿里的时候,业余其实做了好几个 APP,晋升的时候还写了我业余做了哪几个 APP,然后我晋升挂了(哈哈)。那时候我
觉
得还
是会有人欣赏的。
刘飞:
理解,但可能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比较奇怪。
61:
我在做表格的过程中,
业余
也有在做 APP。其实
相
对
来说
,我们做 APP 成本很低,有一个 idea 和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始做了,雏形出来都很快。这个过程中我有做一个叫 Price Tag 的 APP,用来监测 APP 的限免降价,它是一个爬虫,提供一个列表告诉你今天有哪些 APP 在限免降价。
我们把公司关掉的那一天,就那一天,我就在思考我要做什么。前面讲到不可能去上班,也没有其他选择,于是就把这个 APP 拿出来做。本来是很随意地做,现在我很正式地打开电脑,下午就开始写代码了。
大家对这个东西还
挺感兴趣的,慢慢地就开始积累用户了。
那个阶段我
了解
到国外所谓的独立开发者,一个
设计师和
一
个开发
搭档。
很多 MAC 和 iOS 上优秀 APP 其实都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作品。
那时候我心里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这样的团队,
不再去追求大干一场
。
我就追求做一个这样的工具,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去接受用户的反馈,很快地把它实现并上线,就这样。
03 公司的第一个产品诞生于副业
61:
Price Tag 下架后,我几乎没有尝试过重新上架,跟平台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
还是那句话“往未来看”,我们很快就开始调整去思考要做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些设计的方法 Design Sprint,怎么去找新的 idea,比如邀请用户在原型阶段就来体验。我们甚至还想做一个中国的 Product Hunt。事实上,我们已经上线了这个产品,但是我一直没有宣传,然后就暂停了。
* Product Hunt:
国外的好产品发现平台。
刘飞:
这个会跟少数派很像吗?
61:
不一样,少数派偏重以文章内容为主体,我们会更结构化。
我们
在做 Price Tag 的时候,会把少数派和 AppSo 的文章抓过来归纳在某一个 APP 下面。
刘飞:
有点像豆瓣,
你们自己不做内容,但是会做一个内容的集合,
可能是网友上传或官方的内容。
61:
对。我去研究了一下,当时 Product Hunt 的创始人为什么要做这个,整个运营从 0 到 1 是怎么启动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它有哪些缺点,我们再去改进。这个东西我们轰轰烈烈地做了有三个月,第一个版本已经上线了。但上线了之后,一直没有达到我们觉得满意的状态。
不得不再次提到我做 side project 的习惯,整个公司在很忙碌的时候,我就是闲不住自己写代码。我就是那种——今天有个 idea 就要通宵把它给做出来的人。我的 side project(花样文字)上线一段时间后我就发现,我啥都没做,数据就开始增长。
我又停下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不集中精力做这个东西呢?这个阶段,我跟我的投资人吃了一次饭,我印象也很深刻。我跟 Ta 说,我现在没有 big idea 了,这(花样文字)就是我做的东西。我觉得 Ta 很能理解,Ta 其实也跟我讲过自己的创业经历,一发炮弹打出去并不会直接命中,一般都是在空中飘来飘去,最后才有可能击中。那次吃完饭之后,感觉心里有一颗石头落地了。回来以后,我们公司的方向就开始调整了。
04 没有因为数据不好就停止打磨
61:
我们第一个产品(花样文字)的成功,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它给了我们信心和资金,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再去做第二、第三、第四个产品。
然后我们又开始做 OffScreen, OffScreen 是大家了解得比较多的一个产品,但 OffScreen 其实也是做了整整一年之后才开始被人知道的。
这一年的过程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煎熬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磨和迭代。
说实话我们这样的小团队,最不擅长的就是增长。我觉得我的东西很好,但没有人知道,同时我也不愿意花钱找 KOL 推广。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OffScreen 的数据都不怎么样,直到 iOS14 发布之后。
刘飞:
被推荐了,是吗?
61:
对,我们被 Apple 推荐了,感觉是人生的一个亮点。新系统发布那天我们的下载量大概有几十万。
因为 Apple 这次
推
荐,接
下来的一个月,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水平。
知道你的人多了,收到的反馈也多了,你的正向的反馈也多了,就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觉得你的东西做得不错,并且你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去拓展,比如说我们大部分下载都是在中国区,我们仍然有海外的市场可以去努力。你就会意识到这个东西好像潜力还很大。
被 Apple 推荐到一个高峰
并不是意味着
结束,还有 N 个人、N 个市场,N 个国家的人,等着你去触达。
整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的一个优点就是比较耐得住性子,能够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后来做谜底时钟也是做了整整一年之后,还是没有起色。
这回没有那么走运了,它的数据始终是我们的 APP 里面垫底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因为它的数据不行就停止迭代,
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和 road map,把脑子里的 idea、创意和设计放进去,想做一个大家看了会喜欢的东西。
等 iOS15 发布后,我们又火了,但不是在中国区火了
,是在东南亚和美国。
我发现原来我们在海外的潜力那么大,所以就主动去 Instagram 上找一些 KOL 的推广,效果非常好,沟通起来也很顺利。
我
们观察好几个
月了,一开始以为会跟以前一样,偶尔一个波峰,然后下来。但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模式,现在在增长道路上。
我自己来看我们做这几个产品的共性,撇开运气的成分,就是我们都花了一年时间去打磨。
这其实很重要,运气来的时候,你要能抓得住。并且知道什么时候是运气,什么时候是实力。
刘飞:
而且现在你们心里已经有底了,比如说现在的团队能支撑做多少产品?能做哪些事情?这个产品成功逻辑在哪?下一个产品你的确定性就很强了。
05 酒香也怕巷子深
刘飞:
其实从你的描述里面能感知到,早期创业的时候,会有那种只要我产品做得好,不用在乎怎么推广或怎么增长。之前我跟少楠也聊过,他说很多人
第一次创业关心的就是体验,第二次创业开始关注增长。
61:
没错,我觉得特别是做技术的人出来创业会有心理门槛,
会认为我给用户提供一个优质的东西,就等着用户自己去发现了。
但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酒香也怕巷子深
。
其实我们之前在做 Price Tag 的时候,积累了自己的渠道和流量。所以后面做新产品时,初始阶段不担心,能通过自己的渠道和流量获得一批种子用户。但第二阶段,
就成了一个瓶
颈
。
我不太喜欢跟人去沟通交流,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招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自从我不写代码后,就开始享受做这件事情了。慢慢的,我们也引入一些跟数据相关的衡量方式,通过第三方工具去看。以前推广是凭感觉的,现在至少能够有数据去对比和衡量效果。这些事情逐渐变成我每天的全部。
06 关于我们要做什么——
不同阶段的思考
刘飞:
接下来聊到对「小工具」这件事的认知,比如说你们为什么决定做这几个产品,你们当时的观察是怎么得到的?是觉得现在自己缺东西还是怎么样?
61:
我们不同的产品确实有不同的思考
,有好几个阶段,比如说像前面提到做花样文字,完全是个人兴趣。后面 OffScreen 其实不是我的 idea,是我们之前合作的设计师的 idea。正是因为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于是认识了这样一群在杭州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Ta 其实都把整个产品思考的差不多了,包括视觉也做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这样开始合作,把它慢慢地做了出来。
Ta 设计的这个东西让人眼前一亮,从视觉设计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一定会有人欣赏。另外
,从功能上来说其实有很多创新点,它是一个能够在数字时代帮助你减少手机使用的工具,好像跟大家做的事情不太一样。
大家做的事情是让你更多地用手机,去抢占你的时间。
Ta 的设计满足我的需求,这样我们就一拍即合。
后面我们做谜底时钟,又是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从数据切入
。我们在做 OffScreen 时,积累了大量的学生用户,OffScreen 里面有个专注的功能,提供了一个「白名单」功能——用户需要填一个表单,告诉我们将哪个 APP 加入白名单。我统计了一下白名单里的 APP——各种时钟。所以,我们判断这些学生在专注状态时需要一个时钟。这个时钟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可能是阻止自己玩手机,这也是一种仪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