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只需置身其中,就像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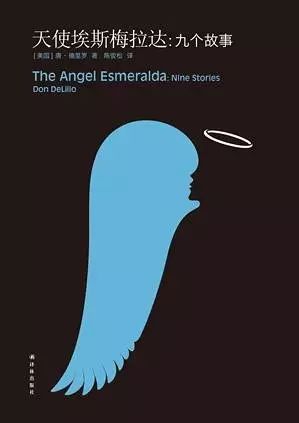
▼ 本文由豆瓣用户@渡边。 授权发布 ▼
我发现我最近被德里罗迷住了,尤其是昨天读到的这个短篇,《天使埃斯梅拉达》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要让我解释这篇小说的妙处,我就只能复述整个故事。虽然我不喜欢用这种形式去评论作品,但德里罗的故事比较特殊,它不怕剧透,因为它不以情节取胜,而是靠一些好玩的概念和美妙的语言。德里罗的小说充满着衍生义、附加义、隐喻和象征,这些言外之意不仅依附于人物情节,还会附着在字句本身,他独特的文风奇特的想法形成一团云雾,让你不必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只需置身其中,就像音乐。
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个冬天里的忧郁男孩,“我”和托德。他们是大学生,正被困在精神世界的伊甸园,他们年轻,无聊,无所事事,喜欢在散步时空想,并就空想出的内容展开无休止的争论,他们看见什么就想什么,什么无聊就争论什么。比如他们看见一个穿着大衣在雪地中踽踽独行的老人,这老人不仅被厚厚的大衣帽子包裹着,也被我们不知情的凄苦包裹着,活像刚从契诃夫的小说里走出来的。可能是老人身上的文学性,让这两个男孩开始了他们的空想游戏。
他们先是争论老人穿的什么大衣戴的什么帽子,因为托德延伸出因纽特人这个新鲜词儿,我便开始抓着不放,用因纽特人的特性来反击他说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会为了享受新鲜而不惜卖出自己的破绽,比如TBBT里有一集谢耳朵发明了新的Spock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于是他和莱纳德就都会一直出Spock,不惜输掉游戏。)然后他们开始给老人脑补身份和角色,想象他是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或者俄罗斯人,想象老人的妻子、女儿,以及他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细节。老人成了他们空想的玩具,他们不断甩出从嘴边滑落的语言抽打着想象的陀螺,玩得不亦乐乎。
小说中还出现一个大学教授的角色,教逻辑学,名字叫伊尔戈斯卡斯,这名字一听就是德里罗者为了自己取乐的而起的,德里罗对语言、名字这两个概念很有执念,我读的他的上一本小说就叫《名字》,在那本书里,他抛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不同文化对于现实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概念,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规定性结构;语言规定本能的表现,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它不仅表达思想,也建构现实。而在这个短篇里,在男孩发散出“驯鹿、海豹和浮冰”这三个词汇之后,他以作者的身份向读者半总结半解释道:“有时任由冲动行事,把意义抛开。让语言成为事实。这就是我们散步的本质——表达外界已存在的事物,所有事实和事件分散的律动,将其重构为人类的声音。”
大学教授的角色在这里可以代表着语言,代表事实,代表事先确定的意义。他让“我们”不想喜欢他,只想相信他,他挑战了“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对事物真假的判断。事实就是想象世界的断崖。
后来“我”和一位女同学有了一段对话,主要是谈论教授,并从她口中得到了一个信息,女同学说她和教授曾在某个小饭馆里面对面谈过一次,还问了他在读什么书,“读什么书?”“我”问。女孩说,教授的原话是“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太棒了。这个信息不仅新鲜,而且它还(可能)是事实,这让“我”激动不已,在下次对契诃夫老人脑补的竞赛中,“我”先是把契诃夫老人说成是教授的爸爸,并接着抛出这个重磅炸弹——“对于伊尔戈斯卡斯,你有些事情不知道。”“什么?”托德问。“他昼夜不停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代表着什么?一是对于代表既定事实的教授而言,知道了他在读什么书,这几乎相当于事实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人性时刻”的缺口,而且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世上还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人性的存在吗?二是在和托德的的空想竞赛中,“我”来了个小高潮,“我”把一个迷人的事实妥帖地嵌入两人的想象之中,如同往泥潭里扔进了一颗钻石。“我”对此得意非常,这种得意的情绪溢出来,感染了无聊的读者我。
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们”没有再看见契诃夫老人,开始担心他是不是死了,一旦老人死去,“我们”这场想象游戏也就意味着惨淡收场。而在一个夜晚,当老人再次出现时,我和托德高兴坏了,“我们”用手指着彼此,并保持这个互相赞许的滑稽姿势,感到无比满足。“我们”兴奋地跑起来,去等在老人的必经之路,我们近距离看清了他那张沮丧的脸,看清了他穿的大衣,甚至被痛苦的手紧紧握住的纽扣,“我们”的想象得到了部分验证,游戏胜利了。但托德还不满足,他想要更多,他想要去跟老人交谈——在想象的世界,事实的吸引力就如同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黑色方碑。托德或许只是被事实吸引了,或许只是想在游戏中扳回一局。但我强烈反对,因为想象一旦接触事实,就随时可能破灭。“我”不想让想象破灭。想象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