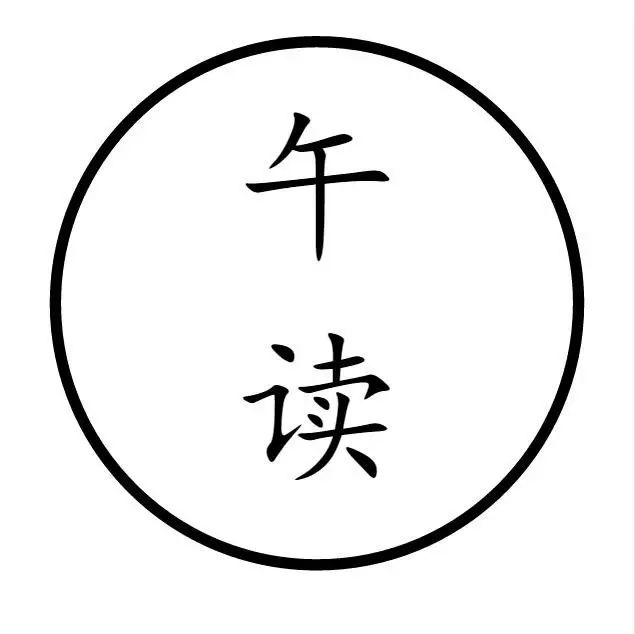编者按
致力于科学原理发现的基础研究是一项公共产品,失败风险也很高。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应该由政府资助的科学。但国外一些领先企业,却愿意花钱“养”基础研究。

卡罗瑟斯(W.H.Carothers,1896~1937)是美国杜邦公司的化学家,他在杜邦公司做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合成纤维尼龙。而且他对高分子化学这门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8年,杜邦公司实施一项"开创杜邦技术"的基础研究计划,经费是每年25万美元。当时还在哈佛大学的卡罗瑟斯向杜邦公司化学实验室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建造新的实验室和配备助手;第二,研究课题不受限制,继续从事基础研究课题;第三,提高工资,哈佛的年薪是3500美元,到杜邦后,至少要提高到5000美元,以补偿他离开哈佛而失去的自由和稳定。这三个条件杜邦全部答应了。这样卡罗瑟斯来到了杜邦公司,从此开始了他形容为“像煤矿工人那样的工业奴役生活”。早上8点到实验室,忙于思考、抽烟、阅读、谈话、做实验,直到下午5点下班。但是卡罗瑟斯仍然感到很愉快,他说:“没有人过问我如何安排时间,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一切都由我自己决定。”最令卡罗瑟斯高兴的是,“研究资金,简直没有限制,我愿花多少,就花多少”。
卡罗瑟斯就这样在杜邦公司做研究。虽然他进行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但是,他却做出了两项后来震惊世界的发明,那就是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他发明的合成橡胶是氯丁橡胶,杜邦公司立即使之工业化了。
1935年春,卡罗瑟斯确定戊二胺和癸二酸是合成纤维的最优秀的原料,合成的多聚酰胺,他称之为尼龙5—10。由于尼龙5—10的熔点太低,而且原料昂贵,工业上没有应用价值,杜邦就让卡罗瑟斯用己二胺(含有6个碳原子)和己二酸(也含有6个碳原子)来合成尼龙66。1937年春,卡罗瑟斯完成了对尼龙66的研究,同年注册了尼龙66的专利。
在尼龙66发明出来以后,杜邦公司决定以“最短的时间,把试管和柜台之间的距离连接起来”。从公司的各个部门调集了230个化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投入巨大的资金,开始有组织地从事"追捕猎物"的行动。1938年建成中间试验装置。这年还发动广告攻势,宣传语是“用煤 、空气和水制成的纤维,跟钢丝一样结实,像蜘蛛丝一样纤细,那就是光泽美丽的尼龙丝”。1939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尼龙。1940年,杜邦公司共销售了6400万双尼龙袜,获得巨大回报。
二战期间,尼龙用于制造降落伞,飞机轮胎的帘子线、滑翔机托绳等战略物质,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至1953年,杜邦公司一直垄断美国的尼龙生产。1953年一些美国化工企业获得杜邦公司的许可证,开始生产尼龙。现在尼龙产品有成千上万种。
1932年,通用电气公司的欧文
•朗谬尔(Irv
ing Langmuir,1881~1957)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是美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的工业科学家。
1906年,朗谬尔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1909年,朗谬尔进入通用电气公司的研究实验室。从此,朗谬尔与通用电气公司结下了终身的缘分。他那多产的一生,计有200篇论文,63个专利,
数不清的荣誉和奖励,包括荣膺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都是在通用电气公司度过的。
通用电气公司鼓励和支持理论研究,他们相信,基础研究终究会“致用”。正如1920年通用电气实验室的年度报告中说:“实验室里某些最优秀的研究者从事着纯粹的科学研究工作,其果实尚未成熟,不能计入年度报告之中,但是,他们的工作却为实验室将要进行的大量研发工作打下了基础,而且,最终可能会变成我们最有用的产品。”
朗谬尔对表面化学感兴趣,可以追溯到一战前,那时他正在研究白炽灯。他发现氢和氧在灯丝上形成了薄薄的一层,大约只有一个原子的直径那么厚。经过多年的研究,朗谬尔对单分子表面层的本质有了深入的了解。1916年,朗谬尔发表了“固体与液体的结构和基本性质”的论文,首先提出固体吸附分子的单分子吸附层理论。朗谬尔认为,固体表面原子对气体分子的吸引力的本质,是固体表面原子的剩余价力。如果固体表面已经吸附了一层气体分子,剩余价就被完全用掉了,不能再吸附第二层分子了。剩余价力的大小,决定固体吸附剂对气体分子的吸附强弱。吸附作用是气体分子在吸附剂表面上凝聚和蒸发两个相反过程的平衡。朗谬尔由此推导出了著名的朗谬尔等温吸附方程式。
朗谬尔的工作奠定了现代表面化学的基础,对催化、液体或固体表面分子的导向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朗谬尔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在表面化学领域内的杰出贡献。
1973年,通用电气公司又出现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通用电气公司的贾埃弗(Ivar Giaever,1929-)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因对“隧道现象”的研究而共同荣获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无论是从公共物品的经济学看,还是从演化经济学看,基础研究必须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企业不会资助基础研究。以上案例说明,以盈利赚钱为目标的企业,也舍得投入和从事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很高的、不能独占效益的基础研究。换言之,
市场机制在基础研究资源分配中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据资料,美国产业界在1940-1990年的50多年的时间里,其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平均约在6%。当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其R&D 经费的比例一般处于5%~ 10%
。相比之下,据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2017年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所言,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其R&D 经费的比例仅为0. 1%。这固然跟我
国整体工业化发展阶段落后于创新型国家有关,也跟我国企业技术水平整体上还处于模仿跟踪、跟跑追赶有关,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确实存在着“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的问题。
我国领军企业尤其是央企和国企,当充分认识基础研究(尤其是应用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对降低企业的技术学习成本、对提高外部科技的“吸收能力”、对发挥“第一行动者优势”等是有利的。归根结底,要成为创新“引擎型”企业,必须有科学原理和科学规律发现的“深厚家底”。因此,
我国产业界应该在继续做大R&D投入的同时,从开发和应用研究的投入中挤出一部分来,逐步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责任编辑:刘小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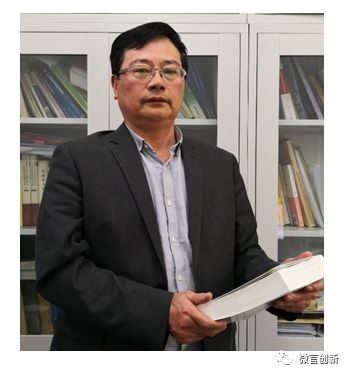
刘立,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研究员。
刘立专栏 | 中国科技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
增加基础研究经费需平衡好短期负效应和长期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