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路撒冷"四个字,会让你联想到什么?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是建筑,三千年积淀,一层埋着一层,从古巴比伦、阿拉伯帝国、十字军、奥斯曼帝国到英国托管时代,从英伦三岛、欧洲大陆,再到地中海沿岸和中东,无穷无尽的传统建筑艺术在耶路撒冷汇聚、挤压、质变,最终凝结成了今天的样子。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耶路撒冷--金色与纯白、黛青与湛蓝调色的耶路撒冷,包括旧城与新城的面貌,却是在距今不到百年的20世纪30年代敲定的。
建起一座伟大之城,要归功一群伟大的建筑师,和他们背后的政府官员、赞助商、医疗机构、教育家和其他有识之士,还要归功于数不清的无名建筑工、采石工、绘图工、雕刻家、陶艺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信仰,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紧张的中东空气里,从废墟中努力缔造了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在这背后,有一段怎样曲折迷人的历史?这几位建筑师究竟是谁?他们如何克服巨大的压力和阻碍,完成自己的规划,完成自己的艺术人格?他们心中又曾经构想过一座怎样的耶路撒冷?
今天,故事君就选取获得三项欧美文学奖的美国历史作家阿迪娜·霍夫曼的全新历史大作《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与你共同领略中东与犹太人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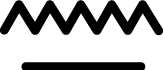
在1923年的旅行中,露易丝一路陪着丈夫,几十年后她承认,她当时一样"完全没料到"巴勒斯坦将带给她的影响。事实上,她被东方和东方人--不仅是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吸引--"几乎是惊到了"。--向优雅、娇贵的欧洲大提琴手露易丝,了解到自己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不过她承认,作为一个女孩,过去并没有意识到身为犹太人的处境。少女时代,她在"黑森林"长大,度过一个个夏天,被大理石壁炉、水晶枝形吊灯、身着低领口丝绸裙的女性先祖们的画像所围绕。如今,"某种突如其来涌上心头的归属感",成了一种"不易接受的东西,因为这于我而言,是一种种族层面的归属"。门德尔松夫妇将自己看作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而这种种族上的影响力,似乎一度使他们兴奋而又不安。
然而,直到他们回到柏林,门德尔松依然无法摆脱那种身为犹太人和建筑师,马上要与巴勒斯坦建立纽带关系的迫切情感。他给自己的校友、同为建筑师的理查德·考夫曼写了封信,后者已经在耶路撒冷安顿下来,获得了稳固的地位,成为犹太复国的奠基者中最著名的规划师之一。"虽然我看到自己的作品在这里"--在德国--"被那些身份显耀的人认可、需要和欣赏,它却并不是我从血液和天性里真正渴望着的土壤……"门德尔松表达了他的愿望:只要能保证他的佣金,并且能与考夫曼的圈子保持良好关系,"最终我将踏上以色列的国土"。门德尔松直白地说:"其他一切,将会随着我的工作自然而然到来。"这是承诺还是胁迫呢?"如果能满足这些,我会即刻前往巴勒斯坦,而且到达之前会通知你。"
正如他所设计的那些发电厂、商业中心和花园城市,所有计划都停留在图纸上,被折好,塞进了抽屉里。即便门德尔松一直没有认真考虑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我深思着",他在1925年给露易丝的信中写道,"美国-欧洲-巴勒斯坦"-有某件事情阻碍着他,阻止他投身于东方。这里指的又是什么事呢?是什么在困扰他?
事实上,纵观整个20世纪20年代,门德尔松在全欧洲都奢侈地拥有稳定、高端的业务,并享有国际名流的声誉和地位。他不必迫切地四处寻求工作机会。事实上,自1928年起,他甚至在柏林郊区一处树木繁茂的地方建造修建了一座低调而壮观的滨水别墅,作为送给妻子露易丝的精美礼物。
当"在鲁本霍恩的别墅"于1930年夏季完工时,它所拥有的在当时最先进的音乐室、精心设计的景观花园、可收缩的玻璃墙壁、自动控制的壁炉、体操室、酒窖,以及特殊的无线电控制嵌入式橱柜,使这对夫妻在柏林的上流社会中既令人歆羡推崇,又遭到抱怨与妒忌。这位建筑师似乎还主动地加剧了这种现象,经他本人监制,一本登载大量照片、以三种语言书写的书正式出版了,向全世界炫耀着在鲁本霍恩的别墅--包括露易丝的全套美甲工具,女儿埃丝特的小折叠书桌,还有一个设计师的伞架。
在一篇文章中,勒·柯布西耶的那位崇尚纯粹主义的伙伴阿梅德·奥占方极尽溢美之词地捍卫了这座"小小殿堂",他解释道:"我非常想弄清并感到惊奇的是这座建筑中互不排斥的功能性与美观。"据他本人在这里生活、工作的经历,他享受到的除了完美的比例之外,还有精心配置的革新科技。奥占方目瞪口呆地说,"它就像有十位机械天使,让我的生活更加便利。"他没有引用柯布西耶关于理想现代住宅的"作为居住机器"的著名表述,但隐含的就是这个意思。奥占方说,在鲁本霍恩的别墅是"一位三十年代的歌德所建造的房屋"。也许并不意外,有些人认为这全套的展示(无论建筑还是书)并不是很得体,它产生自极端堕落与炫耀式的自我放纵。
无论它是否配得上世人给予的大量夸张奉承或尖刻批判,在鲁本霍恩的别墅无疑是一座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文化名人录里的时尚鸟笼。在专门请奥占方制作的壁画、一幅马克斯·佩希斯泰因创作的头戴深色斜帽的、年轻出众的露易丝的肖像,还有那个时期其他一些流行的艺术作品环绕下--包括莱昂内尔·法宁格和艾瓦德·马塔雷在内的顶尖前卫艺术家的画作和铜浮雕作品--作家与各国大使、出版商与王公贵族们都会出席门德尔松一家定期举办的奢华晚宴和音乐会;午后,露易丝会从包豪斯建筑师马塞尔·布劳耶设计的茶点车里端出摩卡和花式小蛋糕。他们那位住在哈弗尔湖畔的邻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常常坐着小帆船到达他们的后院,他把小提琴掖在胳膊下面,以便与露易丝和广受赞誉的匈牙利钢琴家莉莉·克劳斯(LiliKraus)一同表演三重奏。(据露易丝所说,在这些即兴小型演奏会上,埃里希起初会仔细聆听音乐,随后便充耳不闻,自顾自画起草图来。)
然而,他们的奢华别墅,墙垣正在日益孤悬,他为之忧患的祖国也在逐渐闭锁。当最后设计别墅中印着字母图案的餐巾的细节时,门德尔松开始对这所别墅的奢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感到忧虑。他感到,或许应该在简单的生活方式里寻找替代方案,在南方,在东方,他感受到自己对于那个东方原始国度迸发出的冲动。1931年,在一次去雅典的醍醐灌顶的航行之后,他急切地前往意大利和法国蓝色海岸旅行,惊艳于光线、水流、树木、天空,以及遍布整个地区的自山坡散落而下、在山谷中汇聚一处的"粉刷过的长方形小陶土块和砖块"。他痴迷地描述着这些景观,如同在一种眩晕的茫然之中绘制的语言水彩:"天堂,水流,远处的小岛和映射的光线沉入碧海,沉入在永恒的安逸中摇曳着的深蓝。"地中海凭借"它的丰富,它的宁静"引诱着他,然后,他沉思道:"地中海深思而创造,北方却烦扰和劳作。地中海在生活,而北方则保卫着自己。
门德尔松在明媚阳光、温暖气候中感受到的那股奔流着的"永恒的创造力",与德国当时的冷峭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十分讽刺的是,正是这几年,建筑学界爆发了一次臭名昭著的、由种族主义引的争议,建筑师密斯·凡·德·罗在斯图加特策划的一场永久性展览,展出了一些建造技艺最先进的盒式建筑的最新进展。这场展览被德国民族主义者攻击说"像一个阿拉伯村庄",或者根本就是"耶路撒冷的某个郊区"。这些房屋没有典型的德国式坡屋顶,被魏森霍夫的建筑评论家打成了创作者"毫无根基的天性"的反面典型--而这些创作者堪称现代主义的全明星阵容--包括包豪斯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荷兰先锋建筑师奥德、德国建筑师领导者彼得·贝伦斯、布鲁诺·陶特、马克斯·陶特、汉斯·夏隆,以及另外九位才华横溢的欧洲建筑师,包括密斯本人。
即便这群人如此杰出,依然有人谴责他们是"大都会里的游牧者",毫不熟悉父辈们的观念,更遑论祖先们的家园。有人发出嘘声,说建筑师们的平屋顶"让我们不再待在德国的天空下,也不再脚踏德国的土地,而是被错放到东方的沙漠边缘"。在一张臭名昭著的纳粹明信片上,有人在施瓦本(Schwaben)的真实街景中画上了一些骆驼和皮肤黝黑、包着头巾的"当地人"。
虽然魏森霍夫的建筑师中没有犹太人,但"堕落"的污名还是从被鄙夷的平屋顶中传染或渗透了进来。门德尔松本人并没有为斯图加特的展览提交设计。(虽然他也收到邀请并参与了项目,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不参展。)但是可以这么说:展览引起的普遍的反犹太人的情绪,会变成对他的一种刺激--一种不友善的灵感--由此他思索了自己与东方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将会在建筑上带来的可能性。显然,他早就洞察到在德国,有些东西已经腐烂透顶。从科西嘉岛的愉快旅行回来后,门德尔松对露易丝说道,"在柏林的三天再一次暴露了这个注定要破碎的国家和这座虚饰的、强颜欢笑的、毫无希望的城市那种沉重的负担。"他警告说,他周围所有发生的计划和冒险,都是"一群狂热、病态的人的集体骚乱。他们还不知道以后可能会遭受更多更严重的伤害,就去跟他们的疾病作斗争了"。他提到了一种"无法填补的空虚,我在我的办公室里能感受到这种空虚。在办公室里这种空虚没有任何存在的基础;而在家里,空虚却密密麻麻地存在,束缚着、压迫着我"。这种被扼住喉咙的感觉,使他眼前的路更加清晰。即使在门德尔松对妻子表达这种"我自己,我们,要摆脱这里"的需要之后,他仍然思索着多种选择,在巴勒斯坦、(很可能会去的)科莫湖和"谁知道去哪儿"这几种选择之间的一丝缝隙里徘徊。
但是德国的情况逐渐变得难以忍受--在1933年之前,这种威胁终于找上门来。在柏林的一个和煦的春天早晨,露易丝从床上起来,从窗外看到一面纳粹旗子在街道上挥舞,听到上学的孩童唱着:"德国觉醒,觉醒,觉醒!让犹太人腐烂,腐烂,腐烂!"没过多久,埃里希的一位好朋友在他最信任的助手们为他办的一个巴赫主题的聚会上迟到了。(埃里希和他最爱的作曲家巴赫是同一天生日,每年他都会和露易丝与朋友们一起用赋格曲庆祝生日。)这位朋友神采奕奕地宣布,他迟到是因为刚刚觐见了元首。这位朋友对希特勒的着迷,据露易丝后来所说,是对他们的一次"毁灭性打击",也加速了他们离开这个国家--巴赫的国家的决心。
然而,几天后,在3月末,当他们真的逃走时,在一趟夜班火车上,只带了几个行李箱和一本珍贵集邮册的夫妇俩,仍旧没有立即奔赴耶路撒冷。
相反他们先去了荷兰,随后来到了法国南部,在那里,门德尔松与荷兰建筑师亨德里库斯·韦德维尔德、奥占方联手为一座野心勃勃的"欧洲地中海学院"打下了基础,这所学院-若真能建成-会以一种包豪斯的风格耸立在里维埃拉(Riviera)。它所拥有的师资将成为这座学院的基石,包括一群卓有成就的国际艺术家,比如作曲家保罗·亨德米特、生于格罗兹尼的设计师塞吉·希玛耶夫和英国印刷匠、石匠怪才埃里克·吉尔;学院的咨询委员会依仗着一些赫赫有名的成员--爱因斯坦、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保罗·瓦莱里、马克斯·莱因哈特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学院的课程同时具备丰富的动手实践和更有理论性的调查研究。正如学院手册中关于门德尔松的部分所许诺的--在关注"塑造未来"的同时,"将传统和表达我们自己时代的渴望携起手来",这一课程是为"培养年轻建筑师成为一位全面的建造者"而设计的。
但是,在理论性的教学大纲上计划未来,远比现实生活中的纠缠要简单得多。遍布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投来了阴影,学院创始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在滋长--门德尔松一家突然搬去了伦敦。尽管英国的建筑思潮远比德国保守,然而他那种强烈颠覆传统的审美,时常令恼羞成怒的英国文化组织觉得缺乏品位。但当埃里希前往那里为学院筹备资金时,依旧得到了当地一群思想更超前的建筑师的拥戴,他们为他安排了在伦敦的生活和工作。
1933年11月,在利物浦建筑协会的一次社交舞会上,他做了一次关于建筑的讲座。一篇登载在《曼彻斯特卫报》的文章充满溢美之词:"这位著名德国建筑师的发言被热情的欢呼频频地打断。"英国建筑师C.H.赖利(其中一位接待人)向在场的嘉宾宣布,门德尔松近期将会在英格兰开展建筑实践。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对于门德尔松个人而言,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忧虑,定居英国的决定意味着他必须彻底放弃在德国的大量积蓄,连其中的一小部分都保不住。而且他还必须适应这里--或者说尝试去适应--在一个没有精神张力的国度里呼吸。我无法在一个将创新的斗志视为'挑战常识'的地方工作。"出于某些官僚主义的原因,身为外国人的他,被迫与英国人切尔马耶夫一起工作。尽管这位比门德尔松更年轻且缺乏经验的设计师本身性格随和,但两人的合作仍然由于门德尔松自负的独裁倾向产生了很大摩擦。
即使有这些困难与不适,他依然没有收拾行装,带着妻子和他的实践成果离开,前往那个同时代的欧洲犹太人眼中最为明朗的目的地。当他的朋友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质疑这趟兵荒马乱且动机可疑的旅行时,他解释道:"为何不直接去巴勒斯坦?你切中了要害。这些年来,我一直设想着经自己之手建造巴勒斯坦,经过我的行动让它所有的建筑实现统一的形式,以我的组织才干梳理它的智识结构,并向着目标迈进。"他高谈血统、空间、种族以及它们与他职业之间存在的某种微妙的联系,但尽管如此,"巴勒斯坦并没有召唤我。"他需要的似乎仅仅是别人的传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