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立柏是一位研究古典语言学的奥地利学者,任教于人民大学,至今已在北京居住 20 年之久。他称北京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我的灵都》便是他献给“家”的随笔集。在书中,雷立柏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讲述了京城鲜为人知的历史,并细数出 101 条外国人爱上北京的理由。
雷立柏一直自称为“世界公民”。他认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并不妨碍彼此倾听和融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曾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自十八世纪以来,北京逐渐摆脱孤立的局面,小心翼翼地同外部世界接触,发生摩擦和碰撞,留学生和传教士曾作为北京连接西方的桥梁,西方世界也亟需了解这座蕴含潜力的神秘之城。但过程总非一帆风顺,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曾使中国一度陷入固执、怀疑和抗拒的泥沼,那些不受欢迎的历史也渐渐被国人所遗忘......

外国人爱上北京的 101 条理由
(奥) 雷立柏
北京第一批留欧的学生
今天很多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会到国外学习,中国人去国外留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清朝直到 1894 年都禁止中国的学校使用传播“西学”的教材,就可见这种变化之大。在 1894 年之前,出国留学的青年都需要悄悄地离开这“封闭的”大清帝国。
早期出去的人包括山西人樊守义,他于 1707 年至 1718 年间在意大利学习,1720 年还请康熙看他的《身见录》。康熙如果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他应该会派遣一些中国青年到欧洲学习。然而不仅仅康熙没有这个想法,就连在他的皇宫服务的外国传教士好像也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在康熙朝廷工作的外国人中有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他是意大利人,1710 年至 1723 年在北京朝廷担任画家和刻板家。他有一个新的想法,即在意大利的那布勒斯建立一家培养中国神父的学院,因为他感觉到,在中国无法培养出很好的神学家和传教士。
因此,1723 年,他与四名中国修道生和一位语言老师一起启程,先到澳门,而后航海到意大利。1724 年 11 月他们六人到达意大利的那布勒斯,这是马国贤的家乡。他们的旅途还比较顺利,因为虽然花了一年的时间,四名学生总算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这四名学生中有三个来自北京地区:一个是顺天府人,两个来自直隶固安(北京以南 40 公里),一个来自江苏金山。
这四个人算是从北京派到欧洲的第一批中国(北京)留学生,所以1723 年应该是值得北京人纪念的一年。彼时开始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因为从 1723 年以来,在意大利的那布勒斯学院中一直有一些中国人学习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同时也有一些欧洲人向他们学习汉语。马国贤的那布勒斯学院可以算是欧洲最古老的汉语教学机构!

早期中国留洋学生合影
谁是北京的第一批留学生呢?第一个人是谷若翰(外文名称: Joannes Baptista Ku ),1701 年出生在顺天府,1714 年在北京进入修道院,1717 年宣发圣愿,1723 年到 1724 年到意大利,1734 年 1 月 17 日被祝圣司铎,同年回中国,被派遣到四川和直隶传教。他回来后为中国教会服务近三十年,1763 年 1 月 25 日在北京去世。很遗憾,无论是车公庄外的天主教墓园(利玛窦墓)还是原来正福寺的墓园(现在在五塔寺)都没有“谷若翰”的墓碑——我们不知道北京第一名去欧洲留学的人葬在哪里。
第二个人殷若望(外文名称: Joannes Evangelista In )来自直隶固安,也可以算为北京地区的人,虽然固安县今天属河北廊坊市。殷若望于 1705 年出生,1714 年在北京进入修道院,1723 年与马国贤一起离开北京,在那布勒斯学习十年之久,1734 年被祝圣司铎,同年 9 月被派到中国。一年后( 1735 年 11 月 15 日)他不幸在湖南湘潭去世。
与他一起离开北京的还有黄巴桐(外文名字: Philippus Hoam ),他 1712 年出生于直隶固安,1719 年接触修道院生活,1724 年到那布勒斯学院,1739 年宣发圣愿,1741 年被祝圣司铎,但 1760 年 8 月才返回中国,被派到直隶。他于 1776 年 4 月 26 日去世,但学生名单上没有显示出他在哪里去世。
第四位从北京出发的中国留学生没有回国:吴露爵( Lucius Vu , 1713 — 1763 )是江苏金山人,1724 年在那布勒斯开始学习,而且学习的时间很长,他于 1741 年才被祝圣司铎,后来去罗马服务,1763 年 8 月在罗马去世。
今天,每年都有很多留学生从北京出发去欧美学习,但其中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最早的留学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到达目的地并完成学业呢?
北京的“魔鬼”:无知
从历史上来看,长期与“开明”“改革”“教育”作对的力量是官场的“无知”和“愚民政策”。官员们和政治领导当然不愿意听到社会上的问题、缺点和不足,因为这些问题都可以理解为对其政治的批评。因此,“报喜不报忧”是政治家的天性,背后其实是一种“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黑白分明”思想。
这种“黑白分明”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和“恶魔”。如果没有“世界主义”的胸怀,没有“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人都是罪人”的信仰,那么真正的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是会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
当利玛窦、汤若望、雷孝思、马国贤、马夏尔尼、丁韪良、李提摩太和樊国梁来到北京时,他们都想推广新知识,都想帮助中国,但当时他们被怀疑,不受重视,无法自由活动,无法创办新型的教育机构。一直到今天,他们在历史书中也很少得到同情性的理解,比如“传教士”这个词经常和“帝国主义”和“外国侵略”联到一起,所以“传教士”在现代汉语中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在我的心目中,这些人都是伟人,他们的牺牲和投入为中国带来了好处。

雷立柏
最近几年北京也出了一些关于外国传教士的传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看了这样的话:“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
看这些话时,我觉得特别宝贵,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话!如果在 1950 年代、1960 年代或 1970 年代公开发表这样的话,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大部分在中国服务过的外国人不被纪念?这种思想仍旧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黑即白的思想。
由于这种思想,中国人无法承认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为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一些好处,也不能承认日本文明在 1895 年到 1915 年间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那么多好的资源。历史需要很客观地研究——虽然只有上帝是完全客观的——但“尽可能客观”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原则。
明清时期,北京的“恶势力”(欧洲人称之“魔鬼”)可能就是对于外界的“无知”。因为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怀疑外来的文化、知识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天性”,所以一种建设性的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皇帝没有学习俄罗斯语,没有学习拉丁语,也没有学习英语,这样也无法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国际化。
在 19 世纪末,对于外界的“无知”演化为极端的排外情绪,并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同时也继续阻碍着新知识和新学的传播。李提摩太于 1886 年写下的《七国新学备要》面对的,是清廷的蔑视。用形象化的语言可以说,李是在“与魔鬼搏斗”,“与无知拼命”。
这种搏斗在 1900 年后、1920 年后,甚至在 2000 年后仍然继续。中国人有历史感,但这种“历史意识”更多是针对唐、宋、明三代,而对 19 与 20 世纪的历史,“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知恩图报”。于是,英敛之被遗忘了,而樊国梁也被遗忘了。

“五四运动”资料图片
第二个“恶魔”是情绪化地夸大事实。比如情绪化地夸大事实导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不理性地用暴力去焚烧腐败官员的住宅。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经常感谢上天,因为我来北京是在 1995 年,而不是 1965 年或 1975 年!在和平的时代为什么还要用暴力呢?
“夸大”有很多表现。在 1900 年前,有人散播谣言说,外国传教士办孤儿院是为了制药,要挖出小孩子的心、眼睛,等等。造谣的人和喜欢听谣言的人都有罪,因为这些谣言会阻碍双方的沟通与合作。今天有谁会把“对方”的缺点“夸大”呢?哪些“谣言”或夸大的说法会阻碍长期的合作与和平往来?孔子所说的“君子成人之美”让我深思。在今天的世界中,哪里有一些人被“妖魔化”呢?
北京的外国人回来了
从蒙古时代开始,北京一直都有外国人。然而,到了康熙末年和乾隆时代,对外国人的管理和限制越来越严格。康熙和乾隆的政策是为皇宫吸引优秀的外国专家,但又不让外国传教士很自由地接触乡间的中国百姓。因此他们都不太支持中国天主教的发展,最多就是容忍它的存在。
到了 18 世纪末,教会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1784 年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地掀起了仇教的风潮。当时一共有 18 名在乡间秘密活动的外国传教士被逮捕,并被押送到北京,乾隆下令将他们囚禁。
到 1785 年春天,已经有三名传教士病死狱中。1785 年 7 月,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吴斯德望( Etienne Devaut )和贲若瑟( Joseph Delpon )在北京的监狱中去世,而几个月后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毕亚基尼( Atto Biagini )也在狱中去世。
1785 年 11 月 9 日,乾隆皇帝终于回应了那些在朝廷供职的传教士的联名恳求,决定释放仍然活着的 12 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留在北京。不过因为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都没有继续聘请新的外国专家来朝廷工作,所以在北京的外国人人数逐渐下降,到1810 年时就很少了,1820 年只留下四名葡萄牙遣使会会士,其中一位就是毕学源(Pires-Pereira)主教。
1838 年 11 月 2 日,毕学源主教在北京逝世,他是在北京工作的最后的天主教传教士。直到 20 世纪初,他的墓碑仍然保存在车公庄外的栅栏墓园,墓碑的拓片也还在,上面还用拉丁语写着: A Russis sepultus (由俄罗斯人埋藏)。这说明当时为他举行葬礼的是驻北京的俄罗斯教士团的人,因为北京的天主教中国司铎都离开了北京,他们已经于 1828 年迁到了张家口地区的西湾子。

中国古代的传教士
这里的俄罗斯人指的是康熙时代以来驻北京东直门内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士团。在 19 世纪初,北京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教士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好的,因为毕学源在 1838 年11 月去世之前,将宣武门南堂藏书楼和栅栏墓地产权转交给了俄罗斯东正教教士团的大司祭魏若明( Beniamin Morachevich ),请他保管天主教的教产。
毕学源一去世,南堂教产被中国官方没收了,住房被拆除,教堂也被查封。在此之前,皇帝已经下令查封或拆除了很多教产。1826 年 10 月,毕学源已经成了唯一一位留在北京的外国天主教教士。在 1826 年到1838年间,他目睹了北京教堂一座座被毁:1826 年北堂的住房被迫出售,1827 年北堂被毁;留下的是南堂、栅栏和正福寺。
1840 年代和 1950 年代的北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北京没有西欧人士,只有一些俄罗斯人。1840 年的俄罗斯人属于东直门内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士团,而 1950 年代驻北京的俄罗斯人是一些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随着 1958 年前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恶化,所以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有一个人和“外国人回北京”的事件有特别的关系,就是孟振生主教( Joseph-Martial Mouly , 1807 — 1868 )。他是一位法国遣使会会士,年轻时就想去中国传教。他学习神学,被祝圣司铎,并于 1834 年达到澳门。
19 世纪初的澳门是准备中国传教工作的重要地点,比如葡萄牙的江沙维( Affonso Gonsalvez )就在 1813 年到 1841 年间在澳门的神学院培养了一些中国修道生并编写了好几本双语词典,比如拉汉词典和葡汉词典(那个时候的“拉丁语”称“辣丁文”)。
1835 年 2 月 12 日,澳门的法国遣使会会士决定秘密派遣孟振生神父到北京,希望他可以去西湾子。这位 28 岁的法国神父每天晚上用茶水洗脸,希望把自己的肤色染黑一点儿,不要让人发现他是“白人”!他在马车上和小船上都会装扮成一个行动不便的病人,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他知道,如果被发现他是不被允许进入内地的“外国人”或“泰西”来的人,就会被押送到广州或澳门。
那时外国人都不被允许去北京,所以孟振生去北京是件很冒险的事。他于 1835 年 6 月到达北京,在那里偷偷地和中国遣使会会士韩若瑟神父见了面。孟振生曾在北京的正福寺停留过三天,此后他去了西湾子,但他也很关心北京的教产。
孟振生 1835 年在北京的日子肯定是忐忑不安的:他害怕自己外国人的身份被发现。在偏僻地区的西湾子,他可能会感到安全,因为那里是教友村,但在北京时他绝对不能公开露面。可能他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中还能有机会在白天公开地行走在北京的街头。
1860 年,局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对北京的天主教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英法联军在 1860 年 10 月 24 、25 日强迫清廷分别和英国、法国签订《北京条约》,而根据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应该归还此前没收的教会财产。
英法军队很快从北京撤离,但清廷根据所签的条约恢复了北京天主教原来的教产。北京的天主教教友可以重新看守和管理那些古老的教堂和文物了,比如正福寺和栅栏的老墓碑。南堂、东堂、西堂和北堂都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
1867 年孟振生为北堂的落成主持了祝圣礼,但两年后他便不在人世了,61 岁的他于 1868 年 12 月 4 日在北京去世。他的接班人,苏主教( Guierry )为他举行了葬礼,参加葬礼的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美国大使和使团人员,以及海关总署的罗伯特·哈特( Robert Hart )和东正教大司祭巴拉第( Palladius Kafarow , 1817 — 1878 ,1850 年来北京)。
这就意味着,1867 年在北京活动的外国人已经不少了,他们也都是桥梁人物,他们一步步地学习汉语,教授外语,向本地人传播外国文化,介绍国际上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进行汉学研究,做翻译,建造西式楼房,拍摄照片,等等。
今天的北京人几乎都不知道孟振生( Mouly )主教是谁。他原来在正福寺所立的墓碑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混乱中失踪了。如果没有孟振生的勇气和努力,今天北京天主教的教产可能有一部分就没有了。北京的天主教应该纪念这位在特殊时期完成特殊任务的法国人。


作者: 【美】雷立柏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7-6

编辑 | 朱玥
单读出品,转载请至后台询问
无条件欢迎分享转发至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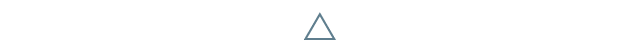

识别图中二维码,购买《单读 14 ·世界的水手》

▼▼点击【阅读原文】链接,购买最新一期《单读》,成为与我们同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