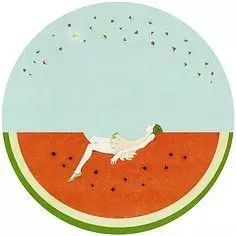文 | 何帆
北大汇丰经济学教授
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在总复习的时候,读一读大家的留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有一些读者一如既往地不喜欢我,但更多的读者留下了他们的鼓励和表扬。有些鼓励和表扬表达得是正好相反的意见:比如,有的读者比我自己还关心订阅数,出各种主意,希望第二季我的《得到》专栏订阅数会增加;也有的读者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众的专栏,留给一小部分读者静静地欣赏最好;有的读者希望我继续讲经济学,有的则更想听经济学以外的东西;有的说,最好开出来一门课;有的说,千万别开课,就这么跟拉家常一样地讲,效果最好。所有的这些批评、鼓励和表扬,我都照单全收,谢谢大家。
有一位读者的问题我最欣赏。他说,既然是教学相长,想听听我在这一年从《得到》学到了什么。以下是我的回答。
▼
这一年的专栏,我是一边写一边修改的。写到最后,已经和最开始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最开始写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写一个漂亮的专栏,到最后,已经变成天天琢磨如何打造一个好用的产品。这两种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我之前固定的写作园地是FT中文网。那里有我的专栏,叫《一知半解》,我每周发一篇书评。在FT中文网写专栏的时候,我的风格基本上是“炫技派”。我追求的风格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有冷幽默、有一语双关,在看似平淡的行文中埋一些“梗”,等待着读者能够发现文中看似不经意的深意,然后会心一笑。到了《得到》,发现这样的风格很不适合读者。读者没有心情去细细品味,他们都是在开车或是做饭的时候听我的文章的,“梗”埋得深,读者会感到茫然。
《得到》的读者经济学基础也参差不齐,有些读者没有学过经济学,所以我不能直接上来就亮明自己的观点,要给大家讲清楚来龙去脉。怎么把握这个火候,是个技术活。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非常累,好像再怎么努力讲得直白浅显,还是有读者听不懂。他们着急,我也着急。有一次我跟罗胖抱怨,他笑嘻嘻地说,这就看你的觉悟了,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你有没有这样的境界?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从那之后,我开始转变思路,不再“炫技”,只是老老实实地打磨自己的产品。
大家可能注意到,写作的过程中我在不断地调整。一开始有关键词、每天的内容总结,后来改为更强调和大家互动的“大局观预热”、“大局观修炼”。每周都请一位嘉宾助阵,周末有“大局观复盘”。文章的主题和风格也在不断调整。从一开始侧重经济学,到后来无所不讲,再到后来集中于几个重大的主题,我在寻找一个更清晰的框架和脉络。从一开始比较硬朗的文风,到后来口语化的风格,我在寻找一个让讲者和听者都更舒服的姿势。我已经喜欢上了这种不断磨合、精益求精、放下自我、服务读者的“产品意识”。从“炫技”到做“产品”,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加谦逊、更加务实、更加专注、更像一个手工艺人——这样很好。
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第一季的“大局观”是一个成功的产品。它的定位不够明确、内容缺乏规划、线索过于凌乱。到第二季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把产品打磨得更加圆润,更加对用户友好。我希望能够保持自己大开大合的风格,跳出学科藩篱,拟合读者的人生场景,把知识拆零之后重新组装。“六经注我”,让大师和高手们的思想为读者服务,让你们掌握终身学习的重要技能,成为跨界高手,能够在“得到”真正“得道”。
在美国有个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叫哈金。他1956年出生于辽宁一个偏僻小镇,21岁考上大学,30岁才出国读书。他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国家读书奖的华人作家。我读了哈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落地》,讲的是在纽约“中国城”法拉盛的一些底层华人移民的故事。
在序言中,哈金谈到,这本小说是他先用英文写,又自己翻译成中文的。他说,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只占他用英文写作所花时间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他用中文写作更为顺手,但却一定坚持用英文写作。为什么呢?他说,用英文写作,让他感到更加独立和坚强。
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倒不是说我想学他用英文写作的方式。尽管我也用英文写一些论文和评论文章,但并没有考虑过放弃中文写作,中文是我的一生所爱。但哈金的意思我懂。在《得到》写专栏,我用的是一种自己并不在行的写作风格,就像哈金要用更困难的英文写作一样。为什么要自己折磨自己呢?我也是希望能够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
人要想生存,就必须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有一种生存能力是在体制内生存,还有一种生存能力是在江湖上生存。两种生存能力,哪一种更难获得?我也说不上来。不过,很多人重视的都是在体制内的生存能力,无形中忽视了在江湖上的生存能力。要是想在体制内的科研机构或大学活得舒服,发发论文、做做课题、上上课,日子就过得很滋润了,何必再去《得到》开专栏呢?在《得到》的文章写得再好,也没有办法拿去评职称,甚至更糟糕的是,会有不少学术圈里的人说这是不务正业。
在我看来,《得到》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能够磨练和检验自己在江湖中生存的能力。如果说在江湖上的生存能力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自由。你可以不依附于体制或机构,直接和读者对话与交流。你自己就是一支队伍、一个品牌、一种力量。你有多大的能力,就有多大的舞台,你有多大的耐力,就能行走多远。
所有的自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敢于特立独行的人,往往活得更累。你要忍受更多的孤独、更多的冷遇、更多的挫折,看破热闹的红尘、喧嚣的名利、心中的执念。要是想过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你的内心里必须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而且要不断地调整和迭代。
为了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最近看了许知远采访马东的视频。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许知远的文风,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完全理解他的悲凉心情。我的精神启蒙是在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当时,没有人关心赚钱,关心赚钱的都是“倒爷”,是大家最不齿的一批社会渣子。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中国的改革和历史的命运。我们那个时代出来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过当诗人的梦想。
那个时代突然不见了。没有人关心诗,没有人讨论哲学,也没有多少人争论民主了。这个世界似乎变得非常肤浅和浮躁,金钱变得越来越傲慢,而文化变得越来越猥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时代才是畸形的。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热爱诗歌,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倾心哲学。你不能再高高地站在讲台上,等待着台下一双双仰慕的眼睛。作为所谓的文化人,你不可能指望大众去供养你。相反,你要学会自己去养活自己,不给社会增添麻烦。这是一个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开放之后的结果。
时代已经变了,原来的变量变成了常数。你看许知远讲的话,和他十多年前讲的话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像官方讲的话,也和十多年前讲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你们有没有觉得,许知远是一个典型的“刺猬”,而马东更像一只“狐狸”?据说,凯恩斯曾经问丘吉尔:“如果事实发生了改变,我的观点也会改变,那么,您呢,先生?”要想理解历史的趋势,我们必须去寻找真正的变量。真正的变量在哪里?真正的变量在被我们忽视的地方。
这是《得到》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宝贵的机会。如果没有《得到》,我永远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广泛的读者群。我的读者里有部级干部,也有小镇青年,有大学教授,也有农民工。有的在北上广深,有的在三线四线城市和农村,也有的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有时,在读大家的留言时,我时常会想,在每一条留言的后面,都有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
时代的洪流奔腾不息,泥沙俱下。《得到》从时代的洪流中舀了一瓢水,在这一瓢水里,你能检测出河流的成分。我在《得到》的读者,跟我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时面对的听众不一样,跟我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台下的学生不一样,甚至跟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面对的观众不一样。但是,我隐约觉得,如果想要寻找那种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关闭的大趋势,如果想要让视野越过这一轮经济周期,看到辽远的未来,那么,《得到》读者这个群体可能是我目前能够接触到的最好的样本。
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变量,剩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更好的去理解它的含义:对我的含义,以及对中国的含义。
(完)